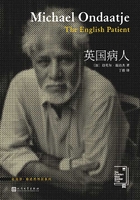1
国民党的监狱是苦痛的刑场,是病菌的酵室,也是黑暗的深渊,是“死之家”,是“石造的柩”,它是建筑在被统治阶级的赤血与白骨之上的。黑暗、污秽、潮湿、熏臭、饿渴、寒冷、酷热、疾病、鞭挞、死亡……永远像黑影般地在监狱里到处游荡。
首先看看伙食吧!行政院规定,监狱里的伙食标准是一角五,可是往下实发却只有一角二。狱方以前每人每日扣三分,自赵天明他们进狱后又增扣二分,总共扣了五分,管伙食的人实际领到七分。七分钱的伙食是够低的了。照一般想象实在是没有油水可捞了。但是神通广大的国民党官吏们,钱经过他们手里过,怎么会不揩点油呢?所以,他们神机一算,就在这七分钱上面揩下了一二分,甚至二三分。他们把菜场里的烂菜皮、烂绿豆芽和牛皮菜等喂猪的东西,以一分钱十余斤,甚至二三十斤的价格收买下来,像煮猪食似的连菜带水在大锅里煮一滚,洒几滴油花,就作为犯人的菜。这几滴油花,有时还被那些看守用勺子先舀去吃了。所以,难友们吃到的只是一碗没油少盐的臭菜洗锅水一样的汤罢了。他们吃的米,都是米商、地主仓房里由于保管不善而霉烂虫蛀的下脚米,价格极其低廉。这样,还不能中饱他们的私囊,他们还要在这种米里面掺上黄沙、石子压压斤两。他们还把每天三餐改为两餐,实际上难友们所能吃到的,有时只有三四分,有时四五分的伙食而已。每次开饭时候,难友们就是饿得再厉害,只要一闻到这股热烘烘的霉臭味,自己的胃就发出了抗议,嘴巴也很难张得开来。尽管这样,每次开饭以前总还是存在着一股希望,直等到这种连猪食都比不上的饭菜挑来时,他们的希望才转变成一股抗拒情绪。不吃怎么办呢?内心又斗争起来了,结果只好像病人不得不吃药似的,勉强咽下一点去。因此,要把每天两餐霉米、沙石饭和那碗烂菜汤吃下去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然后才能慢慢地进食。这样的伙食,人们只要吃上几个月,身体就很快瘦弱下来。
政治犯在这里比军事犯苦多了。军事犯一般外面都有接济,他们本身也有些钱。他们的伙食有的是家中送来,有的在馆子里包饭,有的身上带着钱可以经常买些好吃的……当然,也有不少士兵,他们都是贫苦农民,也和政治犯一样苦。政治犯绝大部分是家庭贫寒的工农干部,他们的家大多在苏区,苏区又正处于主力红军撤退以后的最艰难时期,敌人疯狂烧杀抢掠,大部分家庭都被烧杀得家破人亡;有的流落在外,有的也被捕了,根本说不上还有什么通信联系,还能进行什么接济。就是还有些亲友,他们也不愿意去连累这些亲友,有的也的确怕被他们连累。因此,一般身体都很瘦弱,各种病菌也就乘机侵入。
栊子里的难友经常患各种各样的疾病:有的生肺病,经常在栊子里咯血;有人生胃病,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最普遍的是软脚病,他们半身瘫痪无力,连大小便都要请人帮助;至于疥疮等根本不算病;还有许多人只觉得难受有病,究竟是什么病,连医生也说不出来……病员常占90%以上,死亡率很高,平均每天要死一两个人,疫病流行时每日死亡一二十个人都是常有的事。难友们为着生存,常常就要与狱方进行斗争。有些同志甚至为了保存多数而挺身出来,站在斗争的前列而流血牺牲。经过大家坚决斗争以后,狱方也作些适当的改善,但不久就又坏了。这样循环反复,直至把这些人折磨至死。在红军撤出苏区以后,蒋介石就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说什么放宽了量刑尺度,过去该杀的现在不杀了。实际上不过是把枪毙改为以疾病、饥饿折磨至死而已,而这样的死却比枪毙痛苦万分。
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生活,赵天明他们已过了一个多月了。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大约是四月中旬,人们赞美的春天已来到了人间。这是赵天明人生中第二十六个春天。囚徒的春天,比严冬更难熬!因为这温和湿润的气候,加上监狱里的肮脏,正是各种病菌滋生的时机。所以,每年在这个季节,死亡率特别高。赵天明在栊子里调查了解这个情况后,心里也非常着急。他知道疫病是很危险的,在他的心目中疫病比作战牺牲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的哥哥、弟弟、妹妹和外婆都是得了疫病死去的。参加革命后,据说他的父母也被病魔吞噬了。“怎样对付这个敌人呢?”这是他近来关心的事。
甬道里响起了脚步声,杨疯子酒气冲天地到各栊子通知打防疫针。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认为今年的疫病大概可以比往年减轻了。所以,到了时间,都按规定排着队到铁门外去打针。今天打针是距离远的栊子先打,靠近铁门的栊子后打。二号栊子排在最后面,因为一号栊子没有住人。
铁门外一张方桌罩着一块白竹布,上面放着药水瓶、针筒、消毒器皿等类的东西,有两个穿洁白工作服的人正在为大家打防疫针。
赵天明、田九等打过后,就轮到贺平才了。被叫到名字后他从铁门里走出来,走到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医生面前,这家伙头发梳得油光贼亮的,脸上擦着一层厚厚的雪花膏,白色工作服里面豆沙色花哔叽西装穿得笔挺。一手抓过贺平才的手臂,拿着针筒就来给贺平才打针。贺平才注意一看,针筒里的药水有2CC多,他想打防疫针第一次无论如何不该打这么多呀!于是把刚伸出来的手往后一缩,看守所的医生捉了个空。“第一次打这样多,人吃得消吗?”贺平才有医学常识,看打这么多药水就产生了怀疑,向医生提出疑问。可是那青年医生却死硬着脸发怒道:“你懂得什么?”他捉住了贺平才的膀子就要打。贺平才又扭了一下,他打了个空,药水漏了一半,只好勉强捉住,把剩下的一半打下去了事。赵天明、田九看了贺平才的动作,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药水已全部打进他们身体里了。
回栊子不久,赵天明他们的膀子就红肿酸疼,人也一阵热似一阵,体温在一步步升高,就像被扔在烈火里似的,煎熬得十分难受。贺平才打得少,虽然也同样发烧,但不厉害。张先也学着贺平才的样子没全部打进去,所以也只有轻微的反应。
赵天明要贺平才到其他栊子里去看看。其他栊子里的难友都是一样的浑身酸疼得厉害,在发烧,膀子肿胀得动也不能动。赵天明皱着眉头,脸色十分沉重地说:“老贺!这不是防疫,这是阴谋!我们要设法抢救,粉碎他们恶毒的诡计!”
“对,我正在考虑。老赵!你安心休息吧,一切由我负责。”贺平才安慰了赵天明以后,就为赵天明、田九各倒一杯开水。
甬道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张先走到栊门口一看,只见几个和他们一道入狱的乡苏维埃主席,已因打防疫针后抵不住急速上升的高热停止了呼吸。看守们正指挥差役们拖出他们的尸体……张先心里十分沉重,他想要是报不了这个仇,那才冤枉呢?他不敢把这消息告诉赵天明,只是催促着正在苦思焦虑的贺平才:“快拿出办法来呀!否则……”他沉痛地指着甬道里一具又一具被抬过去的难友的遗体。
“唉!”贺平才紧皱着眉头。
“跟着冲出去!”张先推着贺平才,“去责问他们,为什么杀人?”张先要贺平才跟着抬过的遗体一道冲到铁门外面去找监狱长。
贺平才拉住他说道:“老张!这不是好办法,搞起来反会耽误了时间,害了老赵他们的。”
“那你快动呀!”张先急得满脸冒着黄豆大的汗珠,头上热气腾腾,两手不停地抓腮摸脑。
“等一等,等周看守来。我们要他请老医生想办法,给点药来解救解救就行了。”
“老医生这个人要是好人,今天也不会让这些人来害人了。”张先认为医务所是老医生负责的,今天注射超剂量防疫针的暗害阴谋不通过老医生是不行的。老医生为什么同意呢?这说明老医生也不是好人。
贺平才不以为然,他说:“看问题不能这样简单。”
“那如何复杂地看呢?你倒说说。”张先一面跳脚,一面说。
赵天明、田九烧得更加厉害了,好像就要失去知觉似的。所以,赵天明趁脑子还能活动的时候,说道:“老贺!老张!我还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希望你们担负起来吧!斗争!一定要和那些骑在我们头上任意施虐的敌人进行斗争!”
赵天明的话,田九模模糊糊地听到一点,就接着说:“对准!对,你们一定要对准那些狗头,一下就送他们上西天!”继而,他又愤愤地说道:“老天,要是我有劲的话,我也决不让你安安静静地罩在我的头顶上了!你不公平,你太不公平啊!你让坏人当道,让好人受苦,你,你凭什么做老天!你凭什么做老天!你,你凭什么做老天……”田九越说声音越低,呼吸也越来越急促,最后只看见他的嘴巴在嚅动。
贺平才和张先又回头看看赵天明,只见他两颊烧得通红,紧闭着眼睛在喘气。
“办法!办法!快点想办法!”张先急得用双手摇着贺平才。贺平才顺手抓了几颗盐冲了两碗盐水,交一碗给张先:“先喂点盐水吧!”张先没法只得端起碗来和贺平才两人分头喂水。
栊子里忽然扔进来一包药,跟着周求进来到了栊子里。
“贺平才,烧得怎样?”周求进脸红红地冒着热气,说话有些喘,说明他来时走得很快。
“我倒没什么,你看他们!”贺平才指着赵天明和田九,只见他们两颊通红,微微有些呻吟,人已昏昏沉沉不省事了。贺平才接过药包解开一看是石决明和石膏,就奇怪地问道:“这个药方是谁告诉你的?”
周求进看贺平才的神色,知道他对这个方子很感兴趣,笑眯眯地说道:“我在外面听说今天上午打超剂量防疫苗针的事,就去找姑爹想办法,姑爹只说问题严重,可办法一点没有。后来我就去请教我们家隔壁的中医老头。他问:打超剂量防疫水不知是什么症状?我说:就是高烧。他说:退烧我们中医是有办法的呀!我说:那你就开个方子给我去试试。他就开了这个方子,我到药房里去买了带来给你们试试,不知有用没用?”
“有用,有用。”贺平才赞许地点点头,“谢谢你,我代表他们谢谢你,虽然这是一包花钱不多的普通中药,但是它却能救人性命,能说明你对我们的关爱,只要你努力一定会成为我们朋友的。”贺平才拍着周求进的肩膀,对他的行动大加赞扬。
年青的周求进十分庆幸自己竟做了一件与人有益的事情,纯洁的心灵随着贺平才的鼓励,愈加飞向那善良的世界,追随着真理前进!
“你到各栊子去看看,帮他们想想办法。”贺平才考虑到其他栊子许多难友,也只有通过周求进想办法解决,要他去看看,体会体会国民党的残酷毒辣,促使他更加积极地为难友们解决问题。
“我知道。”周求进有点难受的样子说,“刚才我碰到了几副担架,没想到竟这样快。”
周求进怀着愤慨而沉重的心情到各栊子去了解情况,他一个一个栊子走过去,每个难友都像一块烧红的炭块,人走进去就一阵烘热。他,周求进,青年人的热血沸腾了。青年人的正义感正在召唤他行动起来,他心情沉重,满腔愤怒,又走到了二号栊子。
“怎么样?”贺平才含蓄的眼睛,已失去了往常的宁静,焦灼期待,炯炯有神地逼视着他。
“唉!很严重!”周求进好像不胜重负似的回答。
“有办法吗?找找老医生!”贺平才估计这样的问题老医生一定肯出力的。
“他吗?他要辞职了。”周求进说。
“辞职?”贺平才好像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下似的,突然震惊起来,“为什么?”
“就是为了打防疫针呀!”周求进很难受的样子。
“噢!”贺平才惊奇地问,“为什么打防疫针他要辞职呢?”
周求进叹息着说道:“你听我详细说吧!昨天,卫生局来了一个通知,规定今年每个人都要打防疫针。因为南昌这地方中外要人都要来参观‘委员长剿匪’的伟绩,所以,今年规定得特别严格,指定每个人都至少要打3CC防疫药水,分三次打完。可是这张通知给橄榄头看到了,他就手一抓带回家去了。他每年的老规矩:是要借疫病之手杀一批,摧残一批,来贯彻上面消灭共产党的主张;同时捞进一笔医药费和棺材费。今年这个通知一下,疫病是要减少些了,这就不能虐杀一批政治犯,又会减少收入。所以,他躺在鸦片灯旁想出了这个办法来,打超剂量的防疫药水,这样来按历年的规矩办事。特别是现在关的这批人身体都还好,橄榄头想起了去年的事情,要不是那些人已被摧残得手无缚鸡之力,他哪里还能有命!所以,他下了命令让医务所这么干。但是,老医生不赞成。他说: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不能干。橄榄头一定要逼他干,他就要求辞职!橄榄头就叫小医生来当刽子手了。”周求进讲到这里,他忽然俯身摸一摸赵天明和田九的额头,问道,“药给他们吃了没有?”
“吃了!”张先说。
“我说怎么他们俩烧得比人家轻些呢?”周求进望着正在睡着的赵天明和田九露出了一丝笑意。
贺平才接着又问道:“橄榄头同意老医生辞职了?”
“橄榄头哪里会同意呀!他同意,四姨太还通不过呢?我刚才送个亲戚到老医生那里当护士,看见四姨太正在劝他呢!”周求进做着鬼脸强笑着,但忽又沉重起来,“不过老医生——我那姑夫也是个牛脾气,他是不容易回心转意的,吃这口饭他也常常埋怨,不是看在四姨太的情面上,他早就不干了。”周求进讲得津津有味,还想讲下去,贺平才止住了他说:“嗯!现在你应该为其他人想想办法啊!是不是请你姑夫支援一点药品?”
“全部靠他是困难的。少量的可以,大量的他还不敢。我想还是走军事犯的门路,要他们把钱给我帮他们买药。这样揩下点来救政治犯,我看也就差不多了。”周求进眼睛转了几个圈子,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好办法。
“对!就这样!”贺平才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定要努力办到啊!”
周求进没有回答,挥挥手就到其他栊子找军事犯去了。
赵天明渐渐醒来,听到了一些他们的谈话。他的心慢慢舒展开来,人也觉得清爽点了。
半夜,甬道里又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赵天明、张先都被这可怕的声音惊醒了。赵天明不放心,他摇摇晃晃站起来,脚像走在云雾里似的踩不踏实。张先忙过来扶着他站在门口看,不想杨疯子挥手一拳把他们打倒在地,说道:“半夜三更乱跑干什么?”他们抬头一看,原来黄浪正斜着狼眼在看他们呢!黄浪走到笼门口,扳转他们的后背,看了看号码,说:“401!402!你们已犯了狱规,知道吗?”
“不知道!”赵天明身体十分虚弱,坐在地上起不来。
“我们是起来小便的。”张先站起来,挡着赵天明对黄浪说,“难道在栊子里也不能行动吗?”
“啧啧啧,你们的脚不明明已越出了栊门的界线了吗?”黄浪说着就命令杨疯子,“好!你神气!神气就请你吃顿笋烤肉。杨五!十大板!”杨疯子用力地一下一下打下去。张先一声也不吭,仍然歪着头向甬道里望。只见抬过去的又是和他们一道来的几个游击队长和区苏维埃的负责人,就更加痛心,挣扎着骂道:“人死了这么多,我们还没跟你们算账,你们倒反和我们算起账来了。”他两眼圆睁,突然把手一缩大声喊道:“我就不给你打!”杨疯子没有准备,吓得板子跌落在地上。这样一来栊子里的人都叫醒了。黄浪怕再惊醒其他监里的人,他对准杨疯子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骂道:“没用的东西!”又歪过腿来踢了张先一脚,骂道:“你要找死,你就神气吧!”接着黄浪就匆匆忙忙向外去了。杨疯子在后面跟着,忽然又转回来,摸着屁股弯着腰对张先说:“今天的事,请包涵点!”杨疯子有一个怪脾气,碰到硬的、凶的、职位高的,他就低头装小客气点;看见那些软弱的、可怜的士兵,他就神气活现,欺压人。张先没理睬他。
“滚开!口蜜腹剑的东西!”赵天明骂道。
“唉!赵大爷你哪里知道那黄浪有多精?打几板子,手有多红?肿多高?他都是有数的。”杨疯子好像有无限苦衷似的,可是又怕黄浪发觉,说完马上提脚往外赶去。
赵天明抚摸着张先红肿的手,把他拉着坐在自己身旁。他深深地爱着这个行侠仗义,直率诚朴,具有劳动人民最优秀的品质的战友。赵天明仔细审视着他,觉得他进栊子后,已消瘦多了。本来他是一个红黑健壮的庄稼汉,可是现在已是黄瘦苍白得像个穷书生了。“栊子真像只野兽,它在无形中啃噬着我们的肉,吮吸着我们的血。”赵天明想着,看看张先,不觉怜惜起来。但是,这一切,张先都没发觉,他脑子里想着刚才抬出去的人,好像看见他们都在说:“老张!要为我们报仇啊!你看我们死的多冤哪!”张先呆望着暗黄的墙壁,忽然捉住赵天明的手腕道:“老赵!两天已失去了我们十个人哪!”他把手正反一比画,强调所说的数字。
“我知道,老张!这个问题要解决。”
2
由于周求进大力帮忙,经过一周左右时间,因打超剂量霍乱防疫针而引起的高烧终于退了下去。但是,白喉、猩红热、脑膜炎、流行性感冒等疫病又在难友们头上施虐了。
甬道里又有人抬着死尸在“游行”了。
监狱,这样的战场,赵天明还是新手。经过这两个月来的生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监狱的黑暗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伙食是如此低劣!疫病是如此严重!精神上的侮辱,肉体上的摧残……要保存力量,保存这批革命的力量是多么不容易!看着战友们一个个被抬出去,他深深感到自责:这都是我的责任啊!入狱已两月余,还没有根据监狱的特点,研究出如何避免大批死亡问题,以致使难友们人心惶惶,思想十分混乱。
回想和总结这两个月来的情况,他感到贺平才的方法是对的,他在这里到处都有群众,好像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似的。他和军事犯的关系很好,有些什么困难他们都愿意帮助他;他和监狱里的看守、职员像老医生之类的人物都有些交情;人们碰到他,他总给人留下一个较好的印象。但是,贺平才神通再大,依靠他一个人去和那些人周旋还是不行的,必须大家来干。只有这样,大家都像贺平才一样,团结军事犯,团结所有这里还有些人性、有点爱国心的人,才能使我们的工作立于不败之地。这大概就是我们在这个战场上的重要任务。过去我们把群众的范围仅仅限制在工人、农民中间,没有想到在国民党监狱里团结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军事犯。这类军事犯,就是那些曾经跟着蒋介石反对过我们的人;是那些曾经在战场上与我们交过手的国民党的士兵和下级干部,现在他们又因种种原因被蒋介石关了起来;特别是那些有着爱国思想、迫切要求抗日,被蒋介石从自己队伍里清除出来的“思想犯”。在这里不把这样一支力量团结起来是不行的,坚持不下去的。
“现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想,“不管是从自己五六年的战斗经历和革命斗争经验来看,还是从入狱以后的情况来看,困难是害怕不得的,你越害怕,它就愈加疯狂地向你进攻,压得你抬不起头来。可是当你鼓足勇气,迎着它、顶着它、克服它的时候,它却可以把你和你的工作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境地。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斗争生活啊!共产党员的生活就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正确认识这点,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赵天明想到这里,不禁脸上露出笑容,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惬意的愉快的光芒。这不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吗?为什么这条党的最基本的路线到今天才这样慎重考虑呢?这,这还是我的群众观念不强的表现,还是我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的表现。原来自己考虑的工作方针是,把坚强的政治犯组织起来,教育改造要求进步的军事犯和某些动摇苦闷的政治犯,打击、孤立叛徒和搞破坏活动的坏蛋。这个工作方针是对的,就是没有考虑要创造些什么条件才能去实现这个工作方针。没有群众的掩护,就像鱼没有水一样。所以,贯彻这个工作方针,首先要团结依靠这里的群众才行。
贺平才看赵天明时而微笑,时而沉重,时而轻快的样子,知道他在考虑重大问题。他是有心人,坐监狱以后早就有个打算。所以,开展了一些工作,可就是没遇到合适的人。两个月来和赵天明的相处中,他感到这就是他长久以来要寻找的那种人。所以,对赵天明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他都时刻注意观察。今天,从赵天明的表情上,已估计到他在考虑重大问题,就逗着赵天明问道:“老赵!有什么问题走走群众路线吧!”
贺平才半开玩笑的话却正对上了赵天明刚才的自我批评。赵天明想:“我的确是脱离了群众,你看老贺都在批评我呢?”所以,他慎重地说:“我应该检讨,近来我的确把群众路线丢了。”
“我不是批评你,是开玩笑的。不过,老赵!我也的确希望你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大家研究研究,集体力量总比个人的大,我们能尽多少力,一定全部拿出来。”贺平才解释完毕又十分诚恳地问,“老赵!你究竟在想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赵天明笑着反问贺平才。
“唉!你太小看我了,难道我连这一点相面术都没有吗?”贺平才有点着急了,“你究竟在想些什么?有秘密吗?”
“有什么秘密!我在考虑,我们如何能活下去!”
“看你笑笑的,大概是有了妙法了。”田九的病亦已开始好转,他又摆出了那副老姿势:两手抱胸,两脚叉开,大眼儿笑眯眯地望着赵天明说,“要活下去吗?我看很容易,只要你能把大伙儿的心换上你们政治犯的心就行了。你看这次要不是你们下决心想办法抢救,不知还有几个人能活命呢!但是天下哪里有这种事呢?说是很好,可办不到啊!”
贺平才说:“老田!就是你这办法儿好,可以办得到!”
赵天明也说:“现在我就想和你们研究研究这件事情。”
田九双手一摆,装作惊讶地说:“啊!你们政治犯真厉害,连人家的心也敢给换?”
张先用手指戳着田九,笑着说:“你不早已给我们换了一半吗?看你多麻痹,换掉了你半个心还不知道!”
田九不是笨人,当然他已知道他们所说的换心是指什么了。所以,就呵呵地笑着说:“要全换了才好呢!”
赵天明右手一摆,严肃地说:“说正经的吧!我想我们要活下去,就得接受这次打防疫针的经验教训。要是没有周求进、老医生之类的人肯帮忙,不知要死掉多少人。这应该说是老贺的功劳。他进狱以后就注意到这些问题,在他们身上下了功夫,所以到紧要关头就显出力道来了。但是靠老贺一个人是不行的,我们今后都应该像老贺这样,在栊子里找些有良心的正直人交朋友……”
“我不过偶尔碰到几个好人,交了些朋友而已。说我有力道那是老赵对我的鼓励。”贺平才考虑了一下,然后用商榷的口气说,“不过,根据老赵这样的要求,我想还可以提高一点,把‘交朋友’变成‘拜兄弟’,这样力道大些。因为‘交朋友’洋化一点,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自由主义色彩比较浓厚,无组织、无纪律,捉摸不住,所以,还不怎么靠得住。结拜弟兄呢,封建迷信色彩比较重。俗称是生死之交,组织纪律严格。因此,在订盟之时往往说什么‘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等。因为封建时代结盟主要是对付当时欺压他们的一种恶势力的。所以,被压迫、被欺凌的人特别欢迎,对待盟约也特别忠实。至于后来流氓利用群众这种心理,而搞什么收徒弟、拜老头子,拧成一股势力,借此敲竹杠,那又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今天以正确的思想采取结拜弟兄的形式,与他们是有原则上区别的。”
田九一听到拜兄弟这一他熟悉的形式,很快就理解了、接受了,他称赞着:“老贺这一席话真说到我的心眼儿里去了。老赵!我们就这样干!你看如何?”
赵天明说:“完全同意,栊门是开不久的。我们应该抓紧时间进行。”
正说间,只见田九脸色煞白,又捧着肚子登上马桶拉起来。
3
大家又忙乱起来,不知是什么病。贺平才摸了摸他的肚子瘪瘪的。田九指出疼的部位是在右腹部,根据情况贺平才估计这是胃疼,是饿得太厉害了。
正在这时,杨疯子带着服劳役的难友挑着一担饭菜进来了。那股熟悉的讨厌的霉味在栊子里弥漫着。“老田!是不是吃一点呢?”赵天明装了一碗饭,帮田九拣出石子、稗子、沙子。
“老赵!再怎么拣也总还有些细沙子。老田这个肠胃一点硬的东西也碰不得,不能吃。”贺平才说。
“那怎么办呢?”赵天明焦急地问道。
贺平才没回答,他浑身掏摸,摸出了一块钱交给赵天明说道:“这是一个军事犯请我写状子给的钱。本来准备还他的,因为他也并不宽裕。可是今天我们更困难,权且借用一下吧!”
“老贺!你收起来吧!这样的钱我素来不用的。”田九有股傲气,他劫富济贫搞惯了。给人家他是舒服的,可是用人家的,特别是那些可怜人的钱他就不舒服了。
赵天明拍着田九的肩劝说道:“老田!你这是错了。同难弟兄互相帮助嘛!困难,这里大部分都是困难的,不过有个程度不同。你已饿了好几天,普通饭又不能吃,再饿下去不仅是痛苦的问题而是性命的问题。用一下又有何妨?”
“老赵!不知怎么的,我用人家的,特别像那样可怜的人的钱,心里老是不受用。”
“老田!你错了,称英雄逞好汉不是在这个时候,英雄、好汉也要依靠大家才能生存啊!我们在社会里只有一分力量,我们靠人家,人家也要靠我们。人,就是这样互相依靠而生存的。今天,我们和那个军事犯帮助你,也许明天你帮助我们的地方更多呢!”
“这样?”田九弹动了眉毛说,“那就去买吧!”
杨疯子开过饭,手里又拿着一沓毛道纸,醉醺醺地进到栊子里来。“贺平才!他们都说你状纸写得好,都托我请你呢!”他说完就神气活现地把那沓纸往贺平才那里一扔,说,“贺老乡!你有这才华,到哪里都饿不死!”
“闲话少说,帮我买些东西来吃。”田九弄通了这个道理后,他就从赵天明手里把钞票拿过来扔给杨疯子。
“买什么?”杨疯子一把接住钞票问。
“买四两麻油,两块豆腐,剩下的都买馒头。”田九想多买些馒头来大家吃。他估计四两麻油,加上敲敲竹杠,至多两角钱;两块豆腐至多五分钱,余下七角五分买馒头,大家都可以吃个好样的了。没想到正在这时,黄浪像魔鬼似的黄着脸,瞪着一双狼眼走了进来。
“买东西要交食物税,一块钱还买这买那的。要买这些东西起码再拿一块钱食物税来!”
“怎么?”赵天明怒视着他问道,“你们不给病人吃病人伙食,我们自己买点东西,还要缴税?”赵天明气愤极了,要不是为长期打算,考虑到党的全盘利益,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这是监狱里的规矩!”已经失掉人性,没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法西斯走狗黄浪,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还理直气壮地说着。
“不买了!杨看守把钱还给我们!”赵天明从杨疯子手里拿回了钞票。这口气管谁都憋不住啊!
田九气得冷汗直流,肚子又是一阵剧烈的疼痛。他捧着肚子气得真想抡起两个大拳把黄浪捶死,可是一举手却半点劲也没有,只得又捧着疼痛的肚子,捧着满腹的气愤,忍受着。
张先坐在一边,早已身处烈火之中了,他再也遏止不住那跃跃上蹿的火头,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这种屈辱和欺负。他眼睛向四周一扫,发现以前难友们留下一个能装五七斤酒的大玻璃瓶子,双手一捧就要向黄浪脑后砸去。赵天明发现他的动作,赶快就势一接,还好瓶子没有砸上黄浪的脑袋。赵天明轻轻地嘘了口气,把瓶子往地铺上扔去,怒冲冲地骂张先道:“买吃的钱还不够,你还想买酒!”
杨疯子回头看见这举动,脸被吓得变成了紫色。田九倒洋洋得意,暗自佩服张先的胆量。贺平才也惊了一下,马上就装着十分镇静的样子。黄浪看他们脸色不对,满腹狐疑地问杨疯子道:“有什么事吗?”
杨疯子正想回答,瞥见赵天明、贺平才、田九等人严厉的目光。他停了一下,笑笑说:“刚才那只大酒瓶险些脱手掉在地上。”
“一个瓶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买就算了,要买一定得按规矩办事。”黄浪说着就和杨疯子一道出去了。
杨疯子送来的饭菜就要冷了。赵天明、贺平才继续拣石子,准备吃饭。只见张先气得转头睡觉了。
“老张!快吃饭啊!”赵天明推着他。
“吃不下。”张先说道。
“吃不下也要塞一点下去啊!看你到这里来才两个月,就瘦成这副样子。”赵天明爱怜着张先,感到张先进狱以来,对吃饭抱着自由主义态度,有一顿没一顿的,不能很好吃东西,把身体搞坏了。
“坐监牢,又不打仗。养好了身体有什么意思?我想最后和他们拼了算了,可你又不答应。战场上像我这样的人不知牺牲多少,为什么偏要我留在这里受这窝囊气呢?”张先正憋着一肚子的闷气无处发泄,赵天明这样一说,他就像戳了洞的皮球,气呼呼地直往外冒。
“不吃饭,简单地一拼了事,这是什么行为啊?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就是消极的退却啊!”赵天明严肃地望着他说。
“退却?”张先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痛恨敌人,不怕牺牲自己,就是在栊子里,也敢于和敌人拼命,怎么能叫作退却呢?他实在想不通。
“是啊!是退却!”可是赵天明却毫不留情地答复道。
“你这个帽子,我不能接受!”张先把身一转,背对着赵天明。
“帽子是否戴错了,你自己考虑吧!战场上和敌人拼命,自我牺牲,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战斗的胜利,是为了瓦解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最后在全中国取得胜利,这是它的目的与意义的所在。今天,我们的阵地是监狱,我们的任务是保存革命力量,将来一旦获得自由可以出去为党为革命做更多有意义的工作。你和一个看守员拼命,有什么意思呢?他们的走狗多得很,你拼掉了这个,他还可以派那个,监狱仍然是一片黑暗。不要说是个小小看守员,就是监狱长、军法处长,甚至是更大的官,也还不是揪掉了这个换那个。所以,我们今天和他们决胜负,不是表现在拼掉一个或两个人的问题上,而是表现在是否保存了自己。当然这个保存自己决不同于那些可耻的叛徒。这个保存自己是意味着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两项的。特别是政治生命。”说到这里,赵天明忽然闪着眼睛看着贺平才道:“老贺!你上次讲的以前一批难友打监狱长的事情,我想他们的斗争精神是好的,但是做法值得研究。你看呢?”
贺平才正听得津津有味,他进一步体会到党的力量的伟大。贺平才到监狱已半年多了。他尽一切力量在监狱里打下了一些基础,他是想在这个监狱里有所作为的。今天听赵天明发表的意见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特别是赵天明刚才对过去监狱支部做法的见解,竟和他想的一样,就更加高兴。听赵天明征求他的意见,他深邃的眼睛眯笑着,马上点头表示同意:“我也是这样想的!”
“对!我们应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共产党人是有理想的战士,而不是狭隘的复仇主义者。为了革命的利益,应该不怕牺牲,但决不等于可以随便糟蹋自己。因为自从入党那一天起,他的身体已经属于党,属于革命的集体了。党需要他勇敢地去牺牲的时候,他就应该毫不怜惜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反之,就应该克服一切困难,活下去,以便更好更多地为党工作。可是,老张!你入狱后,常常不能很好地吃饭,身体一天天瘦弱下来,这样下去的结果,不就是可怜地无声无息地死去吗?这正是敌人所希望的。”赵天明停顿了一下,又说,“所以,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有高度的斗争性,而且在必要时还要有高度的忍耐心。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我们的理想才能实现,我们自己也才能成为一个坚韧不拔的共产主义战士。”
张先如梦初醒,他满脸羞惭转身坐起来,慢慢地拿起饭碗,拣着石子,对赵天明说:“我错了,请原谅我。”
“能认识错误就好……”赵天明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喔唷唷!……”田九半天闷声不响,突然又捧着肚子叫了起来。原来田九肚子早就疼了,他熬住了没吭声,现在实在熬不住了。他咬紧牙关,头上的虚汗像黄豆似的滴下来。他的头刚向右边一歪,就倒在地铺上不吭声了。只听贺平才说:“快!灌点水下去!”
4
周求进从杨疯子那里听到二号栊子里发生的事情,一上班就把他们要买的豆腐、麻油、馒头等东西都带了进来。
“多少钱?交税了吗?”张先站在门口,他还关心地问着这欺人的食物税。
“钱倒不多,买这些东西一共只花了五六角钱。税,哪能不交呢?”周求进说。
“交多少?”张先问。
“一块钱。”周求进说。
“黑良心!”田九喝了点盐开水以后好了些。
贺平才把这些东西接过来说道:“不说吧!越说越气人,我们来弄给老田吃吧!”
赵天明把贺平才的一块钱交给周求进,可是周求进摇摇手不要。他说:“这就算我的,下次给你们买东西再拿钱。”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谢谢你!”
周求进一笑,但转眼就收起了笑意,端正着脸孔向门外走去。
赵天明布置张先到栊门口放哨后,就过来帮助贺平才为田九煮馒头、煎豆腐。他们把买来的油倒一半在碗里,又把半个破洋铁罐钻了一个小洞,把它罩在这个油碗上。撕开囚衣,掏出一点棉花,做个灯芯,从洋铁罐小洞里穿出来再蘸点油,就成了一个完全可以燃点的灯芯了。他们又揭开地板,那里有一只没底的破饭盒筐子搁在两块砖头上,小油灯就放到筐子底下。然后把豆腐和麻油放在一个饭盒子里,盖上盖子,放在那个没底的饭盒上。
他们又从囚衣里掏出一团棉花,把发给他们洗疮的灰锰氧粉撒一点在棉花里,然后就卷起来用力搓,把棉花搓成条条,边搓边闻,有一次闻了以后,他们把棉花条拎在手里用力一甩,火花就甩了出来,棉花就烧着了。他们把预先用草纸搓的纸煤子点着,伸到地板底下点着那个小油灯的灯芯,然后把地板盖起来,把毡子铺好,和平常一样。接着他们又以同样方法另做了一个小锅灶,用来煮烂已发硬的馒头。
搞好以后,他们就坐在地铺上等待,不时地揭开毡子,从地板缝里看看下面的蒸煮情况。不久地板缝里冒出了热气,用心听锅里还发出了煎豆腐的嗞嗞声。一股长久没闻到的香味咝咝地往鼻子里钻。田九贪恋地趴在地板上闻着冒出来的热气道:“香!真香!这味道太好了。”
张先也被这香味引诱着走过来,闭上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向地板下面看了一看。两座小锅灶正熊熊地烧得有劲呢!“这玩意儿倒不差呀!”张先颇感兴趣地说。
“是啊!不能小看了它,大锅灶的任务,它也一样完成了呢!你看它烧得又香又甜,怪可爱的。”赵天明觉得这套前人为他们遗留下来的小锅灶,似乎不仅是为了他们方便,而且是为了教育他们而留下似的。所以,他说:“工作好不好,不在于环境的好坏,不在于位置的高下,只在于能不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努力干……”看着这小炉灶成功地烧煮着,大家不免沉思起来。赵天明又揭开地板加了点水,嚓的一声热气直冒,张先赶紧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不久,就听见小锅里发出轻轻的嘟嘟声。“好了!”赵天明说时,贺平才就想揭地板。赵天明把他的手按住,低低地对张先说:“注意门外。”张先把头歪来歪去望了一下,没来人。他就做着揭地板的手势说:“快!拿出来。”
他们慢慢地把地板揭开,端出两个饭盒来,送到田九面前。然后把火吹熄了,盖上地板。
“谢谢,谢谢!”田九坐在铺上作揖又磕头。他端着那滚热的油煎豆腐说:“大家尝尝吧,大家尝尝吧!”
“留着你吃吧!你起码三天以后才能和我们吃一样的呢?”赵天明说。大家虽然很馋,但考虑到田九的肠胃,都不肯吃。
“你们这样,我也吃不下了。”田九把碗筷放了下来。
“老田!你这爽快人,怎么今天倒不爽快起来了!”贺平才说,“不要啰唆了,快吃吧。给那些狗子们发现了,吃不成还要挨毒打呢!这,你又不是新来的不知道!”
田九听这样说,只得端起饭盒子来吃了。好久没吃到这样香甜的饭菜了,再加上病后身体十分需要,所以,他吃得格外香甜。可是吃了一半,贺平才就不准他吃了,要他放下来,过几个钟点再吃。因为胃长期不工作,一下子给它的负担过重,会出毛病的。特别是肠子,尚未痊愈,多吃了会穿孔的。田九听到这个利害,才把饭碗放了下来。
“嘘!”张先在栊门口回过头来发出了一声警报,大家不知是什么事,赶忙把田九的饭菜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