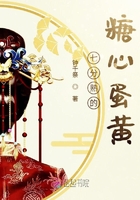香炉里的香块焚尽,再没有缭绕烟气;房中浓郁的药味便再遮不住,尖锐而刺鼻。
凤落以为自己已经坚强到不会再随便流泪,却不料与墨长亭的一番交谈,让她差点又如当初在墨归面前崩溃一样嚎啕大哭,靠遗忘来愈合的伤口又一次鲜血淋漓,痛不欲生。
那些残酷的回忆被她藏在脑海深处,尽可能不去回想,不敢碰触。
每每想起清白之躯终是没能逃过裴远书的魔掌,想起沾染了她的血与泪的床榻,她都痛苦得想要杀死自己。那种难过有些奇妙,不单单因为失去了宝贵的贞洁,也因为她没能守住的,还包括墨归不惜自伤也要保护的东西。
沉默,眼眸里的红血丝,转化为力量却藏身双拳之内无处宣泄的愤怒。
同样的反应,也出现在墨归身上。
指尖轻轻扫过他紧皱的眉宇,步青衣绵绵叹息:“看来对你而言,凤落也如家人一样重要。”
“除却没有血缘关系外,可以说她就是我的亲人。”怅然一声低叹后,墨归终于从沉重的回忆里走出。他松开因为紧握而发白的手掌,唇边满上一抹自嘲苦笑:“那时我爹还被困在水牢中,秦伯又是那种跟谁都热络不起来的人,所以凤落就成了我最亲近的人。我还自负地向她许诺,说什么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人欺负她,可结果呢?我早该猜到裴赞的用意,却因为马虎大意让他们父子奸计得逞,害了凤落。”
“的确算是你没能保护好她。不过,也没必要自责。”步青衣没有盲目地安慰墨归。她走下床榻浸湿布巾,一边为他擦拭掌心里的汗,一边淡淡道:“我想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要与裴赞对抗是多么困难的事。那时就算你料想到他的阴谋又如何?你能公开反抗,还是耍小聪明帮凤落逃过一劫?逃过一次,那下一次呢?我总觉得,以你当时的立场根本没有办法一直保护凤落,能做到那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墨归没有立刻回应,他静静看着步青衣平静侧颜,有那么几分失神。
过了半晌,他才收回遐思,一声感慨:“完了,与你相处越久,我越觉得喜欢上你是不可避免的事。我本来是不相信上天注定这种荒唐说法的,结果现在要被打脸了,还挺疼的。”
“少来这套,以为我没长脑子么?当初你说我嫁不住去之类的话,我可都仔仔细细记着账呢!”步青衣把潮湿布巾摔到墨归怀中,朝天翻翻眼皮。
“事实证明我没说错吧?你看,除了我还有谁敢娶你?”不等步青衣反驳,墨归一脸恍然大悟之色,“哦,对,还有个没眼力的缙王。不过阁主大人如此冰雪聪明,想必早就看明白他用心不诚,这种另有所图的男人当然不能算数。这么一看,数来数去还是只有我一个。我若能娶你,那也算是为天下人降服第一等妖魔,绝对的积德行善——嘶——”
要不是有些舍不得,步青衣非把他胳膊拧下一块肉来不可。
缓了缓,墨归揉着被拧得发青的手臂,试探道:“现在没问题了吧?我已经把我和凤落的事一五一十都告诉了你,你要还是小心眼心存芥蒂,那我……那我就再跟你解释一遍。”
“免了,听你说话脑壳疼。”步青衣一摆手,慵懒道,“我对凤落没意见,换作我是男人也会心疼她,谁让她长得好看性格又好呢?不过有一点别怪我没提醒你,你把凤落当妹妹是你的事,你有没有想过,她对你是什么感情?”
“想过,以前几乎天天想,天天头痛。”仰头一声长叹,墨归的笑容更加无奈。
凤落喜欢墨归,毋庸置疑,且是爱慕之心,而非亲友之间的感情。
这点,他很早很早就知道。
“风落的事,你大可不必过于介意。我对她从没有任何隐瞒,包括想做什么事,喜欢什么人。”墨归定定看着步青衣,眸中有种近乎倔强的执着,“凤落知道我以亲人待她,也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她也亲口对我说过,她从没奢望与我之间会有两情相悦、举案齐眉。如果你还是不放心,我会找个机会与她好好说清楚,我很确定,她绝不会为此而纠缠你我之间任何一个人。”
步青衣眉头一皱:“说得轻松。”
“是,说得轻松,做起来很难。但只要能让你彻底打消芥蒂,再难我都愿意去做。”被病色侵占数日的唇瓣多了一丝血色,墨归浅笑吟吟,满眼赤情,“我说阁主大人,我都这么坦诚了,你再给我设置重重关卡、种种障碍,是不是有些不地道?刚才亲口说的喜欢我,不是想反悔吧?”
本是一句玩笑话,却让步青衣蓦地严肃起来。她眉头微皱,正色道:“喜欢就是喜欢,不需要遮遮掩掩。我步青衣若是爱上什么人,绝不会心口不一,更不会装模作样欲拒还休。”
他对她的好,为她宁舍一切的忠诚,不需要再用什么来证明,她也不会无休止地怀疑、试探,又或者默不作声等待他捅破这层窗纸。
爱一个人是很美好的事,不该成为负担。
步青衣的主动认真反倒让墨归有些不适应,他愣了半晌,挠了挠耳垂:“我都做好准备攻坚克难慢慢追求了,你这么干脆豪爽,着实有些不按套路出牌。这样的话……”
拖长的尾音让步青衣眉梢一扬,黑白分明的眼眸一瞪:“有话说,别吞吞吐吐的!”
“嗯,那我就直说了,听过之后不管心情如何,你都不允许拔刀砍我。”
墨归深呼吸,接连三次,运足气势后才一本正经开口。
“打算在哪里成亲?孩子起什么名字?是咱们自己教还是送去私塾?男孩儿的话得多给他攒些财物,以后是娶个会功夫的媳妇好,还是娶个文文静静的媳妇好?女儿的话,嫁妆我觉得不能太庸俗,免得婆家……”
步青衣怎么也没想到,他这话题一转,竟然一竿子支到了几十年后。她回过神,连忙伸手捂住他的嘴,咬牙切齿:“姓墨的,能不能要点脸?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成亲了?你是不是病还没养好,大白天发白日梦呢?”
“那这梦可真够美的。”他悠哉悠哉。
深吸口气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步青衣收回手,抱肩而立:“你再胡说八道,我就去把你撩拨过那些姑娘都请过来,看你怎么收场。”
昔日帝都出了名的花间游子膏粱纨袴,如今一副刚从蜜罐里爬出来的专情模样,着实让人难以适应。
不过墨归才不管这套,他那双眼就没离开过步青衣的脸,唇上挂的弧度也只深不浅:“你尽管折腾,随意。反正等我能下地走动了,马上就去跟我爹商量着安排,早些把婚事定下来,免得什么缙王之流在角落里暗搓搓惦记我的人。”
故作老气横秋长叹口气,步青衣甩着白眼,心里却已然接受。
如她所说,她不是那种拖泥带水、扭扭捏捏的人。她总觉得,若真是彼此喜欢,又何必兜圈子熬时间,在不停的试探与考验中互相伤害呢?
她喜欢他,他亦钟情于她,足矣。
二人相处时间虽说不是很长,但对对方的了解也好,一同经历的风波也罢,都足够保证这份感情的真挚。既然如此,那么把婚事提上日程也是无可厚非的。
步青衣没有那么多顾虑,稍作思忖,才想要告诉墨归由她来安排婚事,却听得他口中不经意道出一句刺耳惊雷。
“明天我便去拜祭顾阁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的遗憾,终于能由我填补上了。”
那只是墨归随口且无心的一句话,却如一把锐利尖刀,狠狠刺入步青衣心口。
这算什么?
顾朝夕没能与她成为眷侣的遗憾,他来填补?他的柔情百转,他的至死不渝,难道是为了弥补顾朝夕的遗憾?
那她呢?
步青衣的脑子忽而一片空白,那个曾经无数遍反问自己的问题,又一次带着嘈杂嗡鸣回荡在脑海里。
他喜欢的是相处近一年的她,还是从顾朝夕口中听闻,早已认识十三年的她?
“青衣?”发现步青衣脸色忽地苍白,笑容也陡然散去,墨归意识到出了问题,却又不明白怎么突然之间她变了心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步青衣低下头,闭上眼半晌没有说话。及至她抬起头,再次与墨归对视时,片刻前眼中满溢的温情已被冷然所取代,连语气也变得淡漠:“你我之间距离谈婚论嫁还很遥远,先把正事都处理妥当再说吧。”
“你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又发什么脾气?”墨归不明所以,全然没有意识到刚才的话惹了麻烦。
原本安逸的心情被彻底揉碎,变成一片烦躁和郁闷。步青衣有种感觉,再多待片刻她可能会控制不住脾气,届时必然又会因为一些无聊琐事与他起争执。
风口浪尖上,还是先避开吧。
思及至此,步青衣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视线刻意飞快掠过墨归,抬脚径直往门外走去。墨归想要拦住她,一时情急忘了膝盖上的上,跳到地上时膝盖一软险些摔倒,幸而手疾眼快扶住了床帏。
只是再抬起头时,只剩下缓缓关闭的房门,步青衣早带着他读不懂的烦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