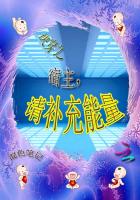“三皇兄!”
燕卿卿惊叫,连忙上前,查看燕武期的伤势。
冷箭显然是高手所放,准确无误的瞄准心脏的位置,打前胸刺入,从后心拔出,箭不留身,只剩下一个拇指粗的,醒目刺眼的血窟窿。
燕武期藏青色的衣袍被鲜血浸透,呈现出一种红蓝交界处的诡异之色,血腥味浓的令人作呕。
燕卿卿慌乱的按住伤口,鲜血却源源不断的从指缝中溢出。
“军医,军医在哪儿?”
她喊叫着,不顾远处火光里飘来的灰烬,在白净的脸上落下一道道灰迹。
血缘是个很神奇的联系,即便平日里不曾过多交流,即便她与燕武期在这十几年里,见面交谈的次数十个手指头都数的过来。
可当他就这么生生倒在她面前,还是牵动了心脏,隐隐作痛。
都说皇家无情,大抵她燕卿卿是个例外。
生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逝,她急的额上直冒汗,而燕武期却忽的笑出声来。
他觉得可笑。
自他出生起,便被身边所有人灌输,他将来,一定要争得皇位。
年幼时被定型的思想极其牢固,燕武期向来是个莽撞性子,直脑筋,他不会去想为什么。
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于是他骄纵,他跋扈,他仗势欺人,他不可一世。
二十多年来,他活给别人看,按照所有人的期待,野蛮生长着。
可直到这一刻,他感受到力不从心的这一刻,突然间开始怀疑,怀疑自己这一生的意义。
他想破了脑袋,努力想找到一丝丝自己真心快乐的片刻,哪怕只是一瞬间。
然而,没有。
这一生走马观花,到头来,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既没有成全他人,也没有成全自己。
“军医,军医!”
身边燕卿卿的嘶吼声将燕武期微弱的思绪拉回,他涣散的眼底逐渐有了焦距。
真没想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身边落泪的,竟是这毫无交集的妹妹。
燕武期缓缓抬起手,燕卿卿立刻握住,他神情费力,唇瓣一张一合,喉咙里发出开水沸腾的声音。
“你说什么?”
燕卿卿凑近,努力想听清他的话。
“燕……期,老……小心……”
燕武期费尽最后一丝力气,瞳孔逐渐失去神采。
他目光虚虚的投放在远处,手无力的自燕卿卿掌心滑落。
“三皇兄?”燕卿卿舔了舔唇瓣,晃了晃燕武期的身子。
潮湿的地面传递上来的凉气瞬间将燕武期包裹,他身上的热气迅速褪去,最后四肢冰凉。
“他死了。”
韩不周眉心微蹙,他上前,将燕卿卿拉起。
“是父皇派来的人吗?”她忽的出声,循着那冲天的火光看去。
“过去看看便知。”
话音刚落,韩不周在前快速走去,燕卿卿连忙小跑着跟上。
燕武期的三万大军尽数驻扎在此,一路绵延而下,竟有一里地,放眼望去,一片白色的蒙古包,在月色下宛若一个个惨白的坟头。
等燕卿卿与韩不周赶过去时,喧嚣声已经息下。
只剩下残兵伤将,相互搀扶着,在营地里包扎。
而前来攻击的人,半个影子都见不着。
燕卿卿随手抓来个将士,急问:“方才来袭击的人你可看出是谁的人?”
那将士被伤了胳膊,拇指深的伤口横在臂膀处,血肉模糊中,一截森森白骨清晰可见,将士惨白着唇,缓缓摇头道:“是一群蒙面人,看出手路数,不像是我们大燕人。”
不是大燕人?
燕卿卿拧眉,如果不是高宗派来的人,还有谁盯着燕武期这三万大军?
更值得推敲的是,前来袭击的人,打伤人便走,并不念战,而且看局面,这三万大军也没有伤到多少。
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一时半会儿还真猜不出个头绪来。
正疑惑着,韩不周的副将常溪匆匆寻来:“主子,宫里来话,六皇子从阮夏发兵,共有八万大军往京师来了!”
燕卿卿没站远,这句话一字不落的听了去,她面色一震:“怎么都赶在这个时候造反?”
韩不周深深看了她一眼,话里别有深意:“此事不是巧合,定是有人在背后操控。”
“是谁?”
燕卿卿实在想不到还能有谁能下这么大一盘棋。
“你四皇兄。”
“不可能!”
韩不周话音落地,燕卿卿便失口反驳。
她梗着脖子,气势不想让,韩不周扫她一眼,似乎早就猜到她会做此反应,也不与她争辩,只对常溪道:“高宗可有派人前去阻止?”
“有,派了大都督府的长子卫峥前去阮夏,但六皇子拥有八万兵力,卫峥只带了三万,定不是对手。”
韩不周闻言目光掠过这些伤残将士,顿时眸子一压,一抹异色闪过。
“你三皇兄将兵符藏在了何处,你可知?”
燕卿卿闻听这一句,先是一愣,后摇头:“我为何会知晓……”
一句话没说完,先前被燕武期打晕了的副将脸色煞白的找来,他见燕卿卿,哆嗦着跪下:“公,公主……这是兖州三万大军的兵符,小人上有老,下有小,若是小人死了,这个家也活不了了,还望此物能让公主能保小人一条贱命!”
燕卿卿茫然的瞧着手中赫然多出来的兵符,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可至于是哪里不对劲,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如今兵符在手,按照先前的计划,应当将兵符带回京师,呈给高宗,可眼下卫峥战况告急,他是秦岭雪中意之人,若是他出了什么事,秦岭雪那边不好交代。
左右掂量下,燕卿卿还是心一横,将兵符摆在燕武期副将面前,下令:“你去点兵,看看还能动的有多少,明早天一亮,我们便动身去阮夏!”
副将应声退下,燕卿卿目送着他的背影,不敢接下韩不周的视线。
“你这般做,正中人下怀。”
“什么意思?”
燕卿卿心一颤,追问。
韩不周却不再回应,只淡淡叹息一声,后揉着她的发丝:“你这性子,闯下的祸端也只有我能替你收拾了,十四,是不是该考虑下以身相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