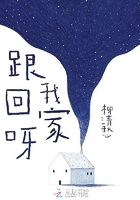舒金花脸色阴沉,挟恨挟怨,打断他的话,“你们怎么在搞,当老板的人居然弄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往后抬得起头,见得了人?”
“自从那年挨过一刀后,银花对夫妻生活就不满意,横挑鼻子竖挑眼,设着法子给我脸色看。我愿意这样吗,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庭,不就是为了她好,那可是我代她挨的一刀哩!替了她的死还不讲良心,把我当傻瓜,同这个男人眉来眼去,同那个男人嘻嘻哈哈。我对她实在够好了啊,什么事都顺着她,宽宥她,只差把心肝挖给她煮汤喝了。钱由着她花,衣服鞋子随她买,她太不知足了。舒娭毑也只是一味地帮她,好像是我不想要孩子,故意不给舒家传宗接代,见了面就冷眼相瞅。这个家庭都不明理,我把苦自个儿埋在心里,现在只好吐给你听。姐,这些年我哪是人过的日子啊!”唐魁灰头土脸,声泪俱下,那话仿佛从鼻孔里哼出来的,又腻又粘,软弱无力。
“该死的,这么不安份守纪,看来得好好地教训一番。”舒金花正要拿起手机训斥妹妹,唐魁慈悲心起,“银花正在气头上,寻死觅活要去修行,等过些日子气消了再谈吧。”
舒金花惦量着安慰他,“这个死妹子,什么事都积累在心里,我哪里知道你们这些私房事?既然事件已经发生了,只能朝好的方面想,有些问题我核实后会逐一帮你们解决的。”
家丑不可外扬,舒金花送走唐魁,反复思忖这一事件该不该告诉何子文?但凭自己的能量绝对无法摆平,更无法泄愤,终于她拿了话筒,低声道:“喂,你还在京华?”电话里传出何子文柔和的声音,“在京华,刚开完会呢,有事吗?”
舒金花处事不惊,尽量控制情绪,“家里出事啦。”
何子文步出奢华至极的会议室,不免有些紧张,“什么事?”
舒金花见自己的话初见成效,更是添油加醋,“绊人的桩子不在高,打狗还看主人呢!竟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是不是仗着王经理的势?”
“狗屁!乌龟王八蛋,看来这帮家伙都成不了大器。你别管,先把银花安抚好,然后将事件搞清楚,后天我回来收拾他们!”
“知道了。”
“挂啦?”
“嗯!”
接连两次西北利亚冷空气侵袭,温度下降了十多度,光秃秃的树枝变得僵硬萧条,在空中相互磨磕着发出嘎刺嘎刺的响声。午后,天越阴越冷,接着下起了小雨,雨下了一节课时间变成雪,雪不是雪片儿,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手在给农民兄弟撒尿素,白粒儿蹦蹦跳跳,沙沙作响。残败的枯叶被疾风吹得兜着圈儿转,墙角处几天前的积雪夹杂着腌臜的垃圾,萎缩成冰疙瘩还没有完全消失,新的寒潮再一次光顾。初入冬季,滴水成冰,老天爷似乎在酝酿一场大雪,给人们一个下马威。
舒银花提着布袋钻出中巴车,冻得瑟瑟发抖,她拉下羽绒服帽盖,吹了下冻僵的手,哈出的热气旋即整个变成了白雾。雨棚下三辆单轮摩托车主见有了生意,轰着油门驰了过来,舒银花寻思着上了一位长辈的摩托车。天冷小便长,风寒脖子短。雪天的人都有些滑稽,道上的男人个个弯腰曲背,抱着胳膊,蹒跚而行;女人头顶围巾,两手缩在荷包里,比阿拉伯妇女裹得还严实。摩托车呼呼呼逆风而进,十多分钟便到了渔场。强悍的北风越刮越大,空中的电缆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所有房屋门窗紧闭,巷道里米粒子雪像过流沙。舒银花付了车费推开虚掩的店门,招呼:“妈!”。
店铺里黑灯暗火,电视正播放言情剧,舒母应声而起,见小女儿口音沙哑,气色蜡黄,赶忙将藕煤炉和炕桌搬进房里,不时拿眼睛观察她,“你人不好?”
女儿见了娘无事哭一场,现在舒银花有事了,并且是大事,天大的委屈。她的泪腺太发达了,一把鼻子一把眼泪地诉说:“妈,我不活了,我要去庵里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