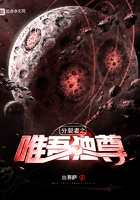叶蔓刚上大学那一会儿,削肩细腰,身量虽然单薄,好在脸还是圆圆的,看起来,倒也不是弱不禁风。
有时候,某一天没课了,她就会坐上环城车,回到市里面的小镇去,她家在那里。
“妈,我回来了!”她踩着嘎吱作响的梯子,走上二楼去。
两个弟弟在院子里洗着衣服,竹竿上挂着几床床单被套,不平整的水泥地开裂处长出了大簇的草丛。
叶蔓从门边,看着自己母亲浓妆打扮着,十分鲜红的嘴唇,脸上粉底卡粉严重,近看竟有些面目狰狞。
“是大小姐回来了?”一个蓄着短胡子的男人笑着和她母亲一起走了出来,调侃着她。
叶蔓心里升起一股浓重的厌恶,却又无能为力。
“蔓蔓,今晚我和你叔出去,你照看好弟弟们。”母亲拿着小镜子,又细细地看了一番,这才满意地合上了圆镜,风姿绰约地挽着男人出去了。
她打开二楼边上的窗,把屋内一股霉味散发出去。
“吃饭了吗?”已经是两点了,叶蔓放下小行李,问着他们。
去厨房里,简单地煮了一些面,姥姥年纪大了,在椅子上歪着头睡着,她摇醒了姥姥,端了一碗煮得耙烂的面给她。
“你妈呢?”老人浑浊的眼珠盯着她,声音有气无力。
姥姥的眼睛前些年就看不见了,听不到有人的声音就开始着急叫起来。
“姥姥,妈妈晚上有事。”叶蔓给她把脸上的老花镜取下来。
尽管眼睛都看不见了,她却已经习惯了架个眼镜在鼻梁上。
“你妈妈!”她突然愤恨起来,使劲拍打着椅子,手上青筋鼓起,“不检点啊!总不安个家,到处乱来,也不怕别人指指点点。”
叶蔓心里难受,为她母亲辩解着,“妈妈也是没有办法。”
“什么没有办法?前些日子,你一竹叔不是过来了吗?”
她沉默了,不再说话,看着弟弟们坐在门槛上吃面。
叶蔓十岁的时候,爸爸突然被抓进了监狱,原来他杀了人,奔走他乡,隐藏了身份,以为不会被识破。
爸爸被判了死刑,妈妈去收拾了尸体,叶蔓看着爸爸被装进了棺材里,那是桃花开的季节。
妈妈撕心裂肺地哭着,她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心里除了巨大的悲痛以外,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惶恐和害怕。
那年,弟弟才刚满一岁。
妈妈相看了几个男人,都被他们两个拖油瓶给吓到了。
后来,妈妈就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了,生活却能勉强应付下去了。
在妈妈怀上第三个弟弟的时候,叶蔓已经十五岁了,姥姥给接了过来,她只有妈妈一个女儿,过来帮衬着妈妈生计。
而那个一竹叔,以前是姥姥和姥爷给妈妈定的人家,只是妈妈一意孤行嫁给了爸爸,两人才不了了之了。
听说那人到现在都还没结婚,都快近四十岁的人了吧?
叶蔓把碗放进水池里,就着面汤洗了起来。
这间院子,和这个简陋的屋子,是她爸爸一个人一砖一瓦地修建起来,虽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上面的木头却还依然结实。
二楼上的小房间里,还有个小梯子,上面有个阁楼,里面堆放着各色的杂物。
“叶雷,小宝的鞋子怎么不给他穿上?”叶蔓看着光着脚丫到处跑的小宝,有点担心他的脚会被院子里的碎玻璃扎伤。
“姐姐,明天就回去吗?”瘦弱的男孩把最后一件破洞的床单挂在了竿子上,抬头看她。
“嗯,怎么了?小雷?”
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带着希翼地看着她,“姐姐,班里有个节目,老师要我们穿白色的鞋。”
叶蔓摸了摸刚刚到手的工资,咬着牙,带着他去了老街。
同样的一座城市,中心是灯火通明的夜,这里却依旧冷清一片,老年人居多的小镇大概都是这般特点。
给他买了一双鞋,看他在换鞋的时候,脚趾头从袜子里露了出来,心里又觉心酸。
虽然一直都想着,等日后生活就会好起来,然而这个过程足够消磨太多的斗志,拖垮太多的人。
给他买了鞋,袜子,又给小点的弟弟买了两件长袖衣服,她几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
第二日上午也是没课的,周二和周三往往都比较闲暇一点,她挨着姥姥睡,年老的人,身上都有种奇怪的体味。
姥姥半夜里又说起了话来,她自从看不见以后,白日里昏睡,晚上便以为是白天了,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起来。
叶蔓也睡不太着,依偎着姥姥,和她说着话。
门咚咚地敲响,叶蔓支起耳朵仔细听着,她知道是母亲回来了。
她不知道该和母亲说些什么,和她说话总有种局促的感觉,两人也说不了几句话,往往就沉默了。
听着母亲跌跌撞撞地推开门进去了,叶蔓支起身来,倒了杯水。
还在楼上就听见母亲的笑声了,她打开门的手一顿,还是回去躺着了。
那笑声回荡在空寂的夜里,无端让她心里升起几分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