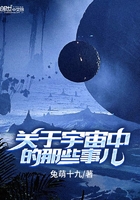夏元明手指有节奏的的在吉他上敲击着,然后看着两旁亮起的路灯,好似要将它们的情绪看透似的,沉默了许久后,才说道:“钱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东西,也是我这辈子最需要的东西,我赚的钱都拿去治病了,点到为止,这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
出于好奇,我侧着脸,想看看他面具下的真实模样,却发现他面具遮的严严实实。
“你带面具是为了搞行为艺术,吸引游客?”
“拉逼倒吧,想什么玩意儿呢!”
“瞧你这一嘴东北苞米茬子味道,牛的上天了,估计是丑的见不得人了。”
说完,我讪讪的笑了笑,有些不太好意思面对他,因为此刻我们的对话,有点类似于小情侣间的打情骂俏,两个大老爷们之间多少显得有些腻歪。
夏元明紧张的看着我,好似被我说中了什么,问道:“你调查过我?”
“别把自己说的跟逃犯似的,我闲大发了,去调查你,没看我到现在才下班吗?”
夏元明放松戒备的点了点头,目光没有再停留在我的身上,却有些失神的看着路灯下匆忙的人群,然后什么话也没说,收起吉他便起身顺着人群流动的方向,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固有的个性和尊严,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保留自己独特的灵魂,不至于成为千篇一律的复制品。看着起身离开的夏元明,我没有相送,甚至连互相道一声“再见”都没有,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还会再见面!
……
夜幕下,我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街头坐了多久,却提不起回家的欲望。兰州似乎是一座不夜的城市,而我却渐渐觉得有些孤独,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来源于何处,于是就这么孤独的流落在街头,在漫长的夜色中煎熬着,直到寂寞被一阵忽然而至的手机铃声所打断,但我仍过了许久才拿起看了看,竟是苏溪发来的。
“酒吧这几天已经慢慢上正轨了,滕子应该也好的差不多了,今晚我就不过去了,你告诉他一声。”
在给苏溪回复了一条短信之后,我随即拿起手机,给滕子拨了个电话,给他转达了苏溪的消息,我忽然想到了可以将酒吧作为活动的最后一站,这样不仅能够给酒吧带来一些经济收入,也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将酒吧推广开来,要知道这二十三位游客,身后是巨大市场的国际旅行团!
在交代滕子三天后晚上一些事务之后,我又具体的给酒吧空间上做了些建议,这才放下心来……
挂完电话,我终于在有些麻木的双腿中,找到了一些回家的欲望,这才拖着疲倦的身体,朝着公交站牌走去。
……
下车后,步行了一段路,终于看见了那栋与黑夜抗衡的17号住宅,片刻,我站到了门前,鼓起勇气打算从正门进入,好好与安沐谈一谈,可想起了她在昨天傍晚冷漠的模样,我便没有勇气敲响那扇铁门,她这种冷漠的状态提醒着我,她现在需要的是独处的空间,数次的反复之后,她已经厌倦了我再用所谓的厚脸皮去碰触她的底线。
我愣了很久,才将悬在空中的手重新放进口袋,从自己的身上获取着抵御严寒的温暖,然后静静的朝着住处走去。
回到家,打开前门,路过院子才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原本墙上打通的那扇门洞,此刻已经被安沐封闭了。
我有些失落,这个门洞多少有些象征意义,随着它的封闭,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将安沐那颗慢慢打开的心门,重新通过自己莽撞的行为,又将它封上了?
淘了点米放在电饭煲中煮粥,我照例在洗漱后躺在床上抽着烟,心中回想着自己与安沐认识以来的一点一滴,却在不经意间,已经经历两个季节。我们相识在那个深秋的午后,她就如秋的沉默一般,闯进我的生活,然后在孤独中与我产生了交集,而我却在不经意间,将这种感谢理解为相依为命!我想,不仅仅是我,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是孤独寂寞的,所以我们才会试图在人群中寻找温暖。可惜,似乎最终的最终,我们还是会只剩下自己,无论哭或笑,悲伤或快乐,只是一场又一场不走心的游戏。
房间的烟雾,将这个狭小的空间包裹的那么严实,以至于我一时间觉得有些窒息,我冲不出自己所设下的牢笼……我们在生活里、爱情里都希望拥有,于是,上帝站在他公平的角度,得到了彼此的呼吸,也得到了寂寞……
我蜷缩着,关上灯,安静的听着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在这无尽的黑夜中,看到了荒唐的爱情,荒凉的自己……点开手机,手机里传出陈奕迅低沉的歌声《从何说起》,那是我所喜欢的声音,陈旧、沙哑。
安静的夜,简单的情歌,手机屏幕跳动的灯光,在舒缓的调子中,渐渐呈现。我起身给自己盛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粥,它们似乎知道我的孤独,用带着温暖的热气包围着我,取出一瓶黄豆酱,我很敷衍的吃了顿晚饭。
在厨房洗碗的时候,忽然听到隔壁院子中安沐久违的声音,她似乎正在遛狗。
我迅速的将碗搁置在一旁,然后冲着院子对面不耐烦道:“谁这么没有公德,大半夜还大呼小叫的?”
对面的安沐忽然沉默了下来,倒是原本安静的萨摩耶忽然“汪汪汪”的叫了起来,我连忙进屋端出凳子,却没有翻过墙,只是站在凳子上,露出头,居高临下的看着安沐,煞有其事道:“这果然是一只忘恩负义的狗,得亏是我把它救出来的,否则还不跳过墙头来将我撕扯了,我也没见过谁家宠物狗像它这么凶的,跟个藏獒似的,它不是还没名字吗?以后就叫它“小心眼儿”吧!”
见我毫无疲倦的表情,安沐正色对我说道:“你精神抖擞的哪像休息的样子?”
我装作没听见安沐的话,依旧摇头晃脑的冲着萨摩耶喊道:“小心眼儿,小心眼儿!”
安沐仰头看着我,面对我的装腔作势欲言又止,却意外的没有反抗,对我说道:“是我打扰了,抱歉!”
这明显不是我要的结果,看着往回走的安沐,我有些急了,忙伸出手召唤到:“小心眼儿还没道歉,不算数,你给我回来!”
“回你个头!”
“你个头!”
我试图用怂无赖的方式拖住安沐,因为我很想找个机会询问她一下,这些天去了哪里?哪怕是不作为朋友,而是作为邻居间最基本的问候。
安沐似乎不耐烦了,抓起脚上的拖鞋就朝我扔了过来,我下意识的一个闪躲,却因脚下重心不稳,晃晃悠悠,一个踉跄跌坐在了地上。
我抱怨晦气的从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却忽然抓住灵感似的,佯装用虚弱,却足以让安沐听见的声音,开始咋呼道:“救命啊,土豪邻居欺负人啦,哎呀,我的腰,哎呀,我的腿,这是哪来的拖鞋啊!”
对面的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又喊道:“谁大晚上没公德乱丢拖鞋啊!哎呀妈呀……”
许久我终于忍不住,正打算爬上椅子看看对面的情况时,抬头却发现对面站在楼顶的安沐,正与我刚才姿势一样,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自导自演。她双手抱在胸前,然后分两次抬起脚,示意着自己两只拖鞋都在脚上。
我一手撑着墙,假装体力不支,心塞道:“居然诈我!”
她依旧不肯罢休,裹了裹睡衣后,带着责备,学着我刚刚的语气说道:“谁这么没有公德,大半夜还大呼小叫的?”
说完,她在风中别了别自己被风吹乱的头发,然后以一种不屑的姿态看着我,片刻便转过身下楼去了,留下风中语塞的我……
……
回到房间,我倚靠在床上,眼前都是安沐刚刚冷漠的模样,就这么重复着抽烟和阵阵失神这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
无聊中,我又从抽屉中拿出慕青的密码箱礼盒,把玩着,却失去了破解它的耐心……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事情都会逐渐的褪去它原有的色彩,快乐的、忧伤的、难忘的,抑或疼痛的。我似乎在平静中渐渐明白,慕青选择了想要的生活,本就是取舍的过程……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破碎的记忆,那些明媚的片段,再绚丽、再夺目,不过昙花一现而已。
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有些事情懂了并不一定代表就能放得开,听了那么多道理,可我觉得自己过得依然不好。我承认对慕青或许还是没有死心,还有些许的愧疚。若不是我的肆意妄为,她或许现在活得很好,我恨我自己把自己当做了情圣,想抚慰任何人的情伤,可是似乎我觉得自己错的一塌糊涂……
……
次日,我在闹铃中强迫自己醒来,看了看手机,这个夜我只睡了不到六个小时,却耽误不得工作的日程安排,我必须在七点半赶到酒店,然后掩藏自己所有的兴许,用最有诚意的笑容,对着外国友人说声早安!
洗漱的功夫,将昨晚剩下的粥放入微波炉中热了热,匆匆吃完,便打车赶往酒店与赵海静会合……
在酒店门口落实了大巴司机、野外医疗等人员之后,游客已经纷纷从酒店出来,可我发现最糟糕的事情,原本约定好七点二十到达酒店的赵海静却迟迟不见人了……
我边给她打电话,边在心里犯起了嘀咕,且不说赵海静知道这次事情的重要性,在我印象中,她上班从来不会迟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