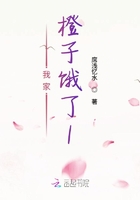雪诺最喜欢睡在高塔坚硬的石板上,看着沉重的天空朝他压过来,有种在天空飞翔的感觉。他还喜欢夜晚看着远处烛火一家家亮起来,照遍整座王庭的塔楼和厅堂。他更喜欢听远处狼群的吼声,似乎这种声音从小就在他的生命里。因此,在他有了记忆的那刻,一只母狼就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这么多年,他时常做梦,梦见一个婴儿在没有人烟的山洞里啼哭,声音穿透草原奔跑的狼群,狼群对着天空高歌,声音绵长而哀戚,一只母狼一路狂奔着朝婴儿走来,喂进婴儿嘴里。有时候,他还梦见一群狼将婴儿围成一圈,白天和通宵守护着他,任何一个狩猎的人都无法靠近,甚至还咬死了几个视图偷他的猎人。这个梦在雪诺梦里已有好多年了,每次梦醒之后,他都要盯着雪狼看很久,“梦和眼前这个时刻保护我的雪狼究竟有什么关联。”每次问雪狼,他都得不到答案,在他的记忆深处,雪狼已经舍身救了他两次。
六岁那年,他爬到胡杨树最高处掏鸟窝,不慎从胡杨树上掉下来,摔成骨折,稽粥派兵寻找一天也未找到。雪狼寻着雪诺的气味,扯着他的衣服将他带回了王庭。八岁那年,稽粥带着雪诺和列王到草原上狩猎,被草原上的狼群袭击,稽粥吓得脸色铁青,将列王拉近自己怀里。狼群朝人群飞奔过来,数十个卫士都被咬死或者咬伤,在一只狼扑向雪诺的那刻,雪狼也飞奔过来,一口咬住狼的后腿,鲜血流地,但没有死。雪狼将狼甩出去很远,咧嘴发出凶狠的咆哮声保护着雪诺,狼群见状迅速逃窜逃离现场。
“雪狼为何没有咬死狼?因为你们是同族?”雪诺依然睡在高塔坚硬的石板上,挪动僵硬酸麻的腿想。他翻身起来,认真审视身边的雪狼,“雪狼,你能告诉我答案吗?”他从城墙上跳跃而下,蹲在雪狼跟前,满心期待的自语,“你是狼,师父为何给你起名为雪狼,义父又起名我叫雪诺?我究竟是谁,师父和义父都不告诉我真相,假如我变成狼,我就能和你对话,是不是就知道答案了?”
曾经,雪诺问过义父稽粥一次,义父只告诉他,“洒下的种子已经长大了,时机成熟我会告诉你一切的孩子。”
从稽粥那里得不到答案,他只记得从小带他长大的师父布衣翎羽常说,“雪诺是上天神灵庇佑的孩子,而且,身上还流着狼的血。”至于其它的,师父也是闭口不说,也没人敢提起,他从来都打听不到他的父母是谁。稽粥对雪诺的要求就像对王子殿下列王,练武、治国、残忍、军训、执行犯人,而他一样都没学会。义父残忍暴力,杀人不眨眼,但唯一对他呵护有加,义父和上任大单于父亲一样,视他为心中的神和信仰。
他不喜欢被关在练剑房,周围全是兵器利剑,残忍的师父会将他折磨得惨不忍睹,稍不用工就会折磨得心生疲惫。他觉得剑房就是他的牢房,王庭是他的监狱,两任大单于就是监狱长。他渴望有一天,外面广阔的天地正在向他召唤。
他还听城里的大人们说,是稽粥的父亲维洛果大单于收留了他和师父,但他对维洛果丝毫没有任何影响,毕竟维洛果大单于离世的时候他才三岁。
雪诺记事那时候是六岁,那时候的他有很多的形容词,常常会听到城里的大人们夸他帅气、机灵、调皮、捣蛋等等。到长大后听得比较多的是俊朗、活泼、懂事。他神态恬静凌然、脸部棱角分明,五官清秀中带着一抹俊俏,帅气中又带着一抹温柔,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好复杂,像是各种气质的混合,在那些温柔与帅气中,有种独特的空灵与俊秀!他的眸子深邃,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辰,配上两道细长匕首般锋利的黑眉毛,看起来格外英俊。
王庭里面有很多大人和骑士家的小姐们喜欢和他玩耍,她们穿着各种鲜艳的衣服出现在他的面前。当然,有时候他也经常冲那些贵族家的小姐抛媚眼,但却惹来不少桃花,那些贵族小姐都要嚷着嫁给他。但最终还是争不过蓝雨婷公主,这位义父的千金一出面,准会让那些小姐离他远远的。
他经常将一头黑发辩起来,用一条黑色丝带扎在脑后,将自己胳膊上的衣袖挽得老高,然后时常在广场上练武,射箭。宽大结实的手臂散发着少年身上的气质活力,肌肉线条清晰好看,带着勃勃的生气,不像那些坐在桌子边喝马奶酒的侍卫和使者们,身材臃肿的像只肥猪,无法形容。
他也会蹿上后山的果树林里摘野果吃,或者站在落院里清扫秋天掉落的满屋顶的红枫叶,他修长矫健的身子仿佛一匹豹子一样灵活,而雪狼总会在不远处陪伴着他,必要的时候在他身边蹭来蹭去,瞬间他回想起师父会责备他又贪玩了,于是心里暗想,“完了,我的射箭还没练好,师父又要罚我了。”
“雪诺,你让我一顿好找。”布衣翎羽轻盈的从台阶走上来,看着躺在石板上的雪诺说。
“是焉吉尔哥哥来了吗?”雪诺优雅的起身,呼出一口气在空气中飞旋,他抬起头露出爽朗的笑容问。
“是你义父叫你到议事厅。”布衣翎羽皱皱眉头,“快点,跑着去还能来得及。”
“谢谢师父。”说完,便迅速轻巧的跑下阶梯台阶,雪狼立即跟在了后面。
“这孩子,一跑就是一整天。”布衣翎羽无奈摇着头,“也不知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雪诺刚走进广场,绕过一条小道,便撞见了王子殿下列王。他和列王从小就面不和心不合,见了面总少不了要掐起来,列王以权压人,他时刻在躲,但从不忍让。
雪诺绕过列王,继续往议事厅走去,列王上前伸出胳膊阻拦,“见到王子不下跪?你是不是想造反?”
雪诺停下脚步,回头扫视一眼列王,假装才看到的样子,“是你啊,我刚才没看见。”
“叫我王子殿下,而不是你。”列王纠正。
雪诺绕道走过列王要走,“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计较。”
列王转身又堵在了雪诺前面,立刻摆出暴躁脸色,“你应该学着怎样做好一个臣子,而不无视一个王子的存在。在我心里,你永远只是个野种,不可能跟我站在一个台阶上,父亲对你的期望跟我一样,我不明白究竟为什么?父亲会让你这个野种坐拥我赤牙的首领?”
雪诺心中有些不悦,皱眉说,“我永远都不可能跟你争什么,大单于位置永远是你的。但你得学着如何做人,更为重要的,你要学着有爱心,如何爱戴你的子民。”
列王嘴角露出一道残忍地笑意,“我是未来的大单于,所有的一切我说了算,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跪在我脚下称我大单于。”
雪诺眉头紧皱得更紧了一些,“师父时常教育我,人不应该跟疯狗计较,我还有事,恕我无法奉陪。”
“你敢骂我是疯狗?”列王脸色铁青,“野种,你再敢骂句试试?”
“别叫我野种。”雪诺纠正。
“你就是野种,没有父母,没有亲人,说不定你是狼的孩子。”
“啪!”雪诺一拳击在列王太阳穴,将他击倒在地上。一团黑影突然笼罩住他,他转头,身边海拔一米八的侍卫马赛克一把提住了他的衣领,“小子,悠着点,你打的可是王子殿下。”
列王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便和雪诺厮打起来,列王将雪诺绊倒,压在了身子底下,两拳打破了雪诺的嘴角。突然,雪狼嚎叫着扑了上来,将列王从雪诺身上扑下来,嘴角狰狞,在咬上列王脖子那刻,雪诺大喊,“不,雪狼……。”
雪狼斜看了雪诺一眼,收了狼嚎和狰狞的表情,从列王身上翻身下来,慢慢悠悠走到雪诺身边。
列王惊恐的望着雪狼,从地上爬了起来,“你给我等着。”然后横冲直撞的离开小道,雪诺目送列王远去,马赛克也跟着离开。
背后一个巴掌在他肩上拍起,雪诺转身,蓝雨婷站在身后,她身穿紫色衣服,头戴一只白色羽毛,将双手背在身后,她一边看着消失不见的列王,一边窝着嘴对他露出甜甜地笑容说,“哥,你可真大胆,连王子都敢打,我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我现在要去议事厅,没时间跟你聊天,我先走一步。”雪诺说完便迅速离开了。
“哥。”蓝雨婷委屈地在身后喊一句,“你每次见到我都这样,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雪诺没有理会蓝雨婷,急忙离开,他先去了自己的住所,将雪狼关在房内,到达议事厅的时候,大单于已经坐在王椅上。他头上带着王冠,列王在左,王后阿其娜在右。殿堂上下二十余人,赤牙各位大臣,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沉重的金锁和各种动物锋利的牙齿,似乎只有装扮这样,才能显出他们优越的地位。雪诺根本就无人顾及,他们各自议论纷纷,只有布衣翎羽看着他选择了门口角落最合适不过的地方停下脚步。他觉得这里刚好可以挡住义父的视角,说白了,他很讨厌来这种场合参加听政,所以他根本无心听政。
稽粥身子微微斜坐,手扶着龙椅上的把手,“据说牛特尔这老东西的兵力越来越强大,军队已经超过两个部落的兵力,十年前,父亲率领军队攻打氏月,丢了性命,损耗两万兵力,牛特尔占领凤尾城已有十五余年,你们各位大臣说说,对于牛特尔一事我们该怎么做啊?”
“对于此事我们再次帅军攻打也不是不可能。”王庭资历最老的大人都翁密侯在人群中说,他的头发和胡须早已发白,躬着腰身,身上带着大串铜钱,彰显他在朝中的贵族身份。
“都翁密侯大人。”你是不是该告老还乡了,我们吃了败仗精神头还没缓过来呢!”最高统帅贵霜王不肖的对峙,“听说你最近又从城里带来一位貌美如花的小女人,还怀孕了,我看你该带着一家老小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养老是件很不错的选择。”说话间众人早已哈哈大笑。
列王也忍不住笑了笑,阿其娜严肃而端庄的微笑并没有失她的身份,稽粥也一脸坏笑,“我们赤牙男人精力在西洲草原上是最充沛的,除了我大单于的女人,你们都可以睡光天下所有女人,当然,最漂亮的女人还是要留给我。”说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
“大单于,这是议政厅。”阿其娜在一旁小声提示。
稽粥极不情愿的撇了一眼阿其娜,收了笑脸,端了端自己的身姿,问人群中的布衣翎羽,“布衣翎羽,说说看你的想法?”
布衣翎羽谨慎看着稽粥,“大单于,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急不得,我们要准备充分的军队和物资,还要拥有一套全面的攻略图,如果再去攻打,要有十足的把握能赢才行。”十几年了,稽粥终于将攻打氏月之事提上了议事历程,他倒希望稽粥可以派出所有的军队攻打大氏月,以报家族之仇。
“大单于,安归伽三个女儿长得甚是漂亮。”贵霜王接上了话,“尤其是他那两双胞胎女儿,一个是罗布城最美丽的女子,一个称之为草原上的第一制香高手,何不让安归伽女儿去合亲,他和牛特尔曾经可是结拜的兄弟。”
“好。”稽粥拍着椅子叫好,“这个提议很不错,就让安归伽女儿去和亲。”
“这个主意不好。”布衣翎羽急忙接话,他知道他的主子十五年前与安归伽早已为雪诺订下姻缘,“如今的安归伽和牛特尔已经不是从前的兄弟了,自从罗布城归顺大单于,牛特尔早已对安归伽心怀恨意,恐怕……。”
“此事就这么定了,事已过去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妥不妥。”稽粥刚说完,拉上来一个野人,他的头发从未梳洗和打理过,一身棉袄奇臭无比,离他很近的人闻到味儿都会远离几步,甚至有些人会将嘴巴和鼻子悟起来。有人提议砍下他的首级,有人提议将他的手指剁下来,列王提议将野人五马分尸,把人头挂在胡杨林里给野人示威,好让野人远离西洲草原。
“前几日野人占领了焉耆,听说焉耆家族无一人生还。”稽粥被靠着王座,右手指在胡须上动来动去,“你们可有什么法子,让野人滚出焉耆?”
“野人队伍越来越强大,占领焉耆部落一事轰动西洲各个部落。”都翁密侯建议,“大单于,在下认为各部落可以各自清除管辖内的野人,至于焉耆部落的野人,大单于可以亲自率领军队和其他小部落军队一举歼灭,这样以来即不失大单于面子,您还可以亲自派一个心腹接任焉耆部落的领主,让焉耆部落从此归顺我赤牙人。”
“嗯。”稽粥点了点头,“这次都翁密侯大人的提议很好。”说着他将人群搜索了个遍问,“雪诺人呢?”
雪诺离得较远,既没有听到义父叫他,也没有听清他们在议论什么,直到师父走过来,喊了他一句,他才发现义父在喊他,于是,他从拥挤的人群中走出来,将左手悟在右边胸口上行礼,“义父有何吩咐。”
“你对野人一事有何意见?”稽粥若有所思地问。
雪诺没有认真听各位大人的议论,对野人占领焉耆一事更没有听清,师父本身极其反对暴乱和战争,于是,他思索良久说,“义父,孩儿认为野人也是人,我们可以试图和他们交朋友,就像各族部落和谐相处那样,说不定……。”雪诺话还未刚落音,现场一片哗然大笑。
“数百年来没有哪个部落可以跟野人交朋友的。”列王开口大笑,语言里也充满了不宵,“怪不得是狼喂大的怪物,你的思维就像野人,根本就不符合人的逻辑。”
“野人认为是我们掠夺了他们的土地。”贵霜王插话道,“各部落的子民都容不得有野人侵入,我认为杀光野人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跟野人交朋友,等于跟狼交朋友。”
列王给贵霜王一个得意的眼神,“贵霜王说得极是。”然后将眼神移向雪诺,耸耸肩膀,“你的建议还能再好些吗?你看看,朝堂之上没人顶你。”
“话虽如此,没有去试过怎么知道跟野人交不了朋友。”雪诺锁紧双眉,语音中充满了对峙,“野人也是人,有思想,有感情,就是我们赤牙人管辖的诸多小部落,我们一样难以跟他们交朋友,涉及到土地和利益,不都是血流成河?”
稽粥哈哈大笑起来,“从小到大这个俩个孩子都在掐,没有经历过生死看来你俩无法站在一起。”他略加思索后开口,“本王就派你俩去焉耆境地打探消息,摸清野人的队伍状况再做打算。”
“我才不要和一个怪物与狼共舞。”列王反抗,“他会让我丢了小命的父亲。”
“焉耆?”雪诺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诧异般的望着稽粥,“这跟焉耆部落有什么关系?”
“整个朝堂都在议论焉耆部落灭亡一事,难道你没听清楚吗?”列王回答,“你最好的朋友焉吉尔也死了。”
雪诺别过头,骤然觉醒的看着布衣翎羽,“师父,这是真的吗?焉吉尔哥哥一族……?”
布衣翎羽低下那肤色不一,花纹布满的额头,“我知道你从小和焉吉尔要好。”他说道,“事已至此,师父知道你是重感情的孩子。”
“义父……。”布衣翎羽话还没说完,雪诺便面向稽粥,“请允许我带兵攻打野人,我一定会拿下野人首领的首级献给义父。”
“这事先放放。”稽粥从座椅上起身,“我们得先去趟罗布城,把和亲的事定了。”说完他面向列王,“王子,安归伽的两个双胞胎女儿我得为你挑选一个,你也该到了成家的年龄了。”
“我不要。”列王拒绝。
“这事就这么定了。”稽粥走下台阶朝雪诺喊道,“雪诺你跟我来,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呃……。”雪诺愣了一下,没明白的指着自己,看看稽粥又看看布衣翎羽。
“大单于叫你呢,快去。”布衣翎羽扬着脑袋示意。
“哦。”雪诺这才反应了过来,朝稽粥走去。
列王挡在了雪诺前面,对稽粥说,“父亲,你为何对这个野种这么好?他对你使用了什么巫术?”
稽粥立刻变了脸色,“你若如此沉不住气,我就将你丢进天塔。”
此时,现场几位老臣都在不漏表情的微笑,雪诺也在微微嘲笑,这些老臣心里都明白,今后,若将大单于的位置交到如此没有诚服的人手里,必定会断送大好前程。倒是被关在天塔的长子纳兰学尽天文地理,和母亲一样能预知未来。在十八年前,小小年纪的他只有八岁,和母亲的预言分毫不差,算准了三十年后,赤牙人人在会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所以,老臣们期待能从这个王子嘴里听到丝毫关于未来的传说,但无人敢在接近他。曾经,维洛果在位时下令,若谁敢靠近纳兰,格杀勿论,并将此事交由教院的巫师看守,不得任何人插手此事。维洛果逝后,身为大单于的稽粥,也没能将自己的儿子救出来。
二十多年前,稽粥跟着维洛果清扫了东部一带草原的居民,杀了郁胭上下六十多口人。稽粥看郁胭长得清秀,便求维洛果留下了郁胭,并将她带了回来。稽粥为郁胭求情的那刻,维洛果就告诉他,“她若在王庭有丝毫不的放肆,我就一刀刺入她的喉咙。”
郁胭成了稽粥的女人,纳兰八岁的时候。郁胭将预言说了出来,并刺杀维洛果未遂,将一把剑刺入维洛果的胸口,而郁胭被维洛果的弓箭手刺穿喉咙,当场毙命。稽粥跪了三天三夜,才说通维洛果留下了纳兰,纳兰十八年前的预言,让王庭的臣民再次人心惶惶,稽粥只好顺从了父亲的旨意,将纳兰关在了天塔,与世隔绝。而稽粥只有在训斥列王的时候会突然提及天塔,是因为他压根就没忘记郁胭,阿其娜与他争吵的时候,常说,“一个死了的女人反倒住进了你的心里。”
他们一同走出议事厅,稽粥领着他们走过宽阔的广场,走过军队训练营,还路过了奴隶训练场,看着那些被绑在柱子上训练的奴隶,雪诺看了觉得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一面墙,墙上铺满了石子,脚下的石阶磨损得很光滑,这是经历了百年脚步摩擦后留下的轨迹。眼前是一座数百年建筑物,这个通往地底的冗长隧道,两边的墙壁上,雕刻着连绵不断的细密花纹,非常典型的水源装饰纹路。墙壁上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放置在石槽里的壁灯。不是用火光来照明,而是靠魂力维持着亮度。不过每一盏石灯都不太耀眼,所以,只能看清地下隧道里大概的状况,隧道的尽头,依然笼罩在一片死寂的黑暗里。越往下,温度越低,石阶和墙角,渐渐长起了一些青苔,墙壁反出一层湿漉漉的光晕,雪诺感觉自己在走向一个潮湿的地底墓穴。
再走一会儿,就到了台阶的尽头。一个略显空旷的石室,没有多余的装饰,石室中央是一个六角形的巨大石台。稽粥将墙上一块青花色的石台扭动两圈,墙上就开了一扇门。他们一同走了进去,走进一条隧道,隧道两侧点燃着蜡烛,墙上雕塑着历代赤牙大单于的肖像,通往隧道的路很窄,阴森而寒冷,似乎都能听到足音回想的声音,每走一步仿佛都能惊动他们。
维洛果的肖像在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他们走在他的身边停下,维洛果背部放置着一把长剑,工匠将他臃肿肥胖的身材和红扑扑的脸蛋雕刻得相似至极。
稽粥看着父亲的脸庞,便开口道,“雪诺,你最不应该忘记的人是你爷爷维洛果大单于,是他收留了你和你师父。”
“义父,我也应该感谢你。”雪诺说,“是你从小将我抚养长大,在你心里,我也是你的儿子,我能感觉到。”
稽粥微微一笑,“我赤牙人历史悠久,这些历代大单于骄傲的立在这里,保佑着我们家族繁荣昌盛。”他说着皱皱眉,“但这里面缺少了一个大单于,你可听说过头曼大单于?”
雪诺眨眨眼睛,“我当然听说过,赤牙历代大单于的故事我是听着长大的。”
“你师父是这里的元老,曾经一定见我过爷爷,我要他给我爷爷画张肖像,我的父亲虽憎恨我爷爷,也不愿将我爷爷肖像放入家族,但我总觉得,骄傲和荣誉也有他一份。”
“义父说得极是。”雪诺皱了皱眉眉头,“若头曼大单于泉下有知,定会感激您,义父您也算是为列祖列祖做了一件光荣的事。”
稽粥点点头,“这话说到我心坎上了。”接着他走到一个女肖像面前停下脚步,他将左手放在右胸口行礼,眼神恋在那女子脸上不忍离去,放佛要把她从肖像中换回人世,“她死的时候才十七岁。”他的声音因悲伤而变得沙哑,“我全心全意的爱着她,是父亲下令杀她,父亲的弓箭手用箭射死了郁胭,她死在了我怀里,鲜血都侵透了我的浑身。”
“她是?”雪诺不明白地问,看到义父脸上布满了忧郁。
“她是纳兰的母亲郁胭。”稽粥回答着,摸了摸肖像的脸,手指轻柔的滑过肖像表面,就像抚摸活生生的恋人。
列王倒吸了一口冷气,“是那个被关在天塔的纳兰吗?”他也细细审视了一番雕像,郁胭气质确实非凡,细腰纤柔,美丽的脸蛋上镶嵌着一对大眼睛,在整个西洲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这可是王庭最大的秘密,无人敢提及。”稽粥将手指从肖像上拿开。
“义父为何现在要告诉我?”雪诺睁大了眼睛又问。
“是因为你和纳兰的关系。”稽粥回答,“纳兰的母亲曾经预言,说三十年后我赤牙家族将会遇到一场浩劫,而纳兰在八岁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你就将他关在了天塔?”
“我知道你与纳兰从小要好,我怕预言成真,会让我整个赤牙家族都陷入万劫不复。”稽粥将郁胭肖像左边手指轻轻一扭,肖像身后一道门便开了,他将雪诺带入其中。里面很黑,稽粥顺手在烛台上拿起一盏蜡烛走了进去,里面是交错纵横的十几条隧道,走进第三条隧道门口时他才开口道,“这个口是为将来逃生用的,只有接任大单于的人才有资格知道这个逃生口。”
“义父为何要将这个逃生口告诉我?我能做什么吗?”
“雪诺。”稽粥的声音一再低沉,情绪低落,“你是神灵庇佑的孩子,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你都要保护好纳兰,也别让列王丢了性命。”他的话刚结束,廊道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音,他们立刻走出了洞门,关上肖像左边的按钮,当石门关闭时,北凉慌张朝着他们走进。
“大单于。”北凉谨慎看一眼稽粥,“纳兰王子……,他恐怕……。”
北凉的话还没说完,稽粥便脚步跨路离开,“召集两千军队,快去。”他朝北凉吩咐。
“不能和巫师硬碰硬啊大单于?”北凉跟了上去,雪诺也随即跟上。
他们赶到了天塔时,白鸦厉声尖叫,振翅飞离,停在了天塔削尖的高处,一个身穿红色长衣、带着红色帽子的女人从人群中走出来,她的队伍已经长长排列在门口。而北凉带来的两千多军队也整齐站在了一边,将天塔门口形成一条长长的廊道。
他看到师父也在人群中,红包巫师在等待稽粥走进,“大单于可是要救你儿子出去?”她低声开口。
“没有哪个父亲会看着自己的儿子去死。”稽粥说,“我不想惹恼你,但我也要救我儿子出来。”
“我会以死捍卫维洛果大单于的命令。”巫师连眼都不曾眨一下,“没有教院,你拿什么来救赎你的灵魂?”
“那我们就只好兵戎相见了巫师。”稽粥给出严重警告。
巫师的人已经抽出了刀剑,在巫师伸手阻拦的那刻,北凉抽出了手里的剑,移向巫师的脖子处,“让你的人退开。”他开口,“否则你的小名会丢在这里。”
“我可是教院的巫师。”巫师纠正。
“那又怎样?”北凉警告,“你的命在我手里。”
最终巫师终于妥协,稽粥获胜,他越过巫师,走入门前。门被打开,里面卧榻上睡着一位年轻人,头发好长,凌乱无比,看似很久都没洗了,满脸黑色的胡须将整张脸遮得丝毫没有一点表情,他的手臂上,脖子上,脸上,只要肉能露出来的地方,被鱼鳞状包裹着。
稽粥看到眼前的纳兰,身心俱碎,几乎连语言的基本能力都消失。一名医师走了进来,“看看这可怜的孩子,这样下去,自己受苦不说,对接触他的人也没好处。”
“我命你一定要救救他。”稽粥开口命令。
“我所能做最仁慈的事情就是给他一杯断肠草,让他远离痛苦,就此了结。”
纳兰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稽粥努力让情绪平静下来,然后吩咐,“我要你无论花多大代价都要治好他,否则你也别想活。”
医师无奈点点头,“我想想办法。”然后命人抬走了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