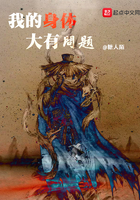时光如梭这个词用在没有明显季节变化的两广地区,比泱泱华夏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加贴切。在双层夹衫换成了单层薄衫,薄衫换成夹衫,夹衫再换成加了棉絮的长衣宽袍时,一年就匆匆落下了帷幕。
萧朝贵很好的履行了婚前的承诺,或宿于东厢房中,或值夜于营中,除过不得已的几次跟她同桌吃饭外(端午、中秋、冬至、元宵四节,会中集体放假,伙房临时关闭一天,个人伙食自理),再未踏足过她的屋子。
新春刚过,还未出正月,就传来道光帝驾崩,新皇帝即位登基,改年号为咸丰的消息。
在古代,皇帝死亡对普通百姓的唯一实际影响大概就是所用铜钱上刻的年号会改一改。但在赵杉当前所处的封建时代末世,对于那些已经预见到大动荡时代即将来临并一心思变的人们,此消息无疑是引爆那星星之火熊熊而成燎原之势的助燃剂。
这年二月,天地会多个分部在两广多地起义,初登大宝的咸丰皇帝诏命数路精兵良将入粤桂平乱。
未免树大招风,萧朝贵借“天兄下凡”传言,令教会中所有部众各自回乡暂避,待风声过后,召集亲友速来金田汇合,共入团营,择机扯旗举事。同月,洪秀全与冯云山离开金田,回广东老家隐蔽身份。原本喧嚣的拜上帝会总部一下子沉寂下来。
赵杉所做的仍然是一天天地看着一天天过去,再迎来新的一天。她自成为“天妹”,又招了个“贵婿”,做起专职“家庭妇女”后,就被刻意的跟外界隔绝起来。她本是最乐于做个局外人的,自然也就得过且过。
进入盛夏,沉寂许久的金田村忽然又变的躁动起来。
韦府后院的一片山坡地上,两三日之间便筑起一个四面篱芭墙的大院,里面搭了五个荫凉草棚,棚中盘炉支灶,盆口大的火炉连支了十五六个。
同时,一辆辆满载着锄、镰、锨、耙等铁制农具的牛马骡车,不断的自韦府后门涌进篱笆墙内。叮叮当当的锤打声由朝至暮,昼夜不绝,夹杂着黑色铁末的烟气雾气,弥漫天际,将整个村落笼罩。
韦家大院,一时成了方圆百里最大的打铁铺。
男人们忙着垒灶打铁,各家的女眷们也没闲着,将分发到各自手中的青蓝布匹丈量裁剪,为即将来金田团营的教众,缝制衣裳。为跟满清的服装款式相区别,所有新做袍褂衣裳的前襟均由左衽改为右衽。
赵杉每日闷着头穿针引线,也再无暇写字看书。时光弹指,转眼就入了秋。忽的有一天,锤锤打打的声音一丝也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鸡鸭鹅的喔喔嘎嘎的鸣叫声。
“打铁铺怎么一时又变成养殖场了?”赵杉心中又觉奇怪又觉好笑,放下针线,到篱笆墙里去看。
草棚中,原先垒就的铁匠炉跟堆着的的炭垛都不见了,只有满地撒欢蹦跳的家禽。
秦日纲与几个韦府家丁手提着麻袋,哗哗哗地往石槽中倒着糠皮谷壳,见了赵杉,咧开大嘴,笑道:“快到中秋节了,到时杀鸡宰鹅迎接外出的兄弟们回家。”
萧满头满头满脸的汗,领着一帮背着绳索的强壮男子从篱笆墙后通向后山犀牛岭的小路上走来,看到赵杉,把脸一沉,训斥道:“你不在屋里呆着做活,跑这儿瞎瞧乱看什么?”
“我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还要向你请示?”赵杉气哼哼的转身,抬腿往前就走。迎面正遇上神色焦急的韦昌辉,只得又转回了头。
韦昌辉大步来到萧朝贵近前,拉住他的胳膊,道:“到处寻你不见,快跟我来,四兄那里有要紧的事情商议。”又扭头叫住赵杉,道:“天妹也一起来吧。”
议事厅内,久未露面的杨秀清倚坐在窗前的一张藤椅上,面色苍白,脸颊瘦削,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萧、韦二人各搬把木椅,在他身侧坐下,甚是亲热的相互嘘寒问暖。赵杉只在靠门的一张小杌子上坐下。
韦昌辉看看杨秀清,咳了一声,开言道:“刚收到洪二兄传来的信,他跟冯三兄自广东回返,途中路经平南县花山人村,投宿在一户姓胡的人家。那家家资颇丰,当家人胡以晃是个武举,早有反清之心。洪二兄有意游说他入会,因而要过些时候,才能来金田相会。还有去往平南、藤县等地的林凤祥等兄弟也都传信来说,聚了好些同道中人,要同来金田团营。”
萧朝贵看看面色凝重的杨秀清,又瞧瞧神情焦虑的韦昌辉,不解地问:“有许多新兄弟来团营,这是好事啊,你们干嘛还苦着脸?”
韦昌辉叹气道:“王作新老贼又到浔州府去告黑状了。据陈承瑢传回的消息,浔州府衙门近来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动作。”
萧朝贵挥拳怒吼:“银子送了几千两,都喂不熟这些豺狼。倒不如豁出这身肉,直接反他娘的!”
杨秀清叹口气,徐徐地道“扯旗容易,难的是扯旗之后如何应对。听闻,原受命来广西做巡抚的钦差,就是那位曾经在虎门主持销烟的林大人已在来桂途中病故,咸丰妖头又派了个姓周的继任为巡抚,此人是有名的酷吏,杀人不眨眼。还有那几路从云南、贵州等外省来的妖将妖兵估计也快到了。眼下,会中的兄弟十之八九都分散在外头,村中都是些病弱的老幼妇孺,一旦公开扯旗起事,如何能抵挡得住那汹汹而至的豺狼虎豹!”
萧朝贵闻言,焦躁起来:“那就快招避风的兄弟们回来啊。这都火烧眉毛了,还缩在窝巢里躲躲藏藏,难道干等着被豺狼咬被虎豹吞吗?!”
韦昌辉道:“洪二兄、冯三兄他们没到之前,不好轻举妄动。”
萧朝贵翻着白眼“哼”了一声:“兴许是看着那家财主有势有钱,提前穿起龙袍,过起皇帝佬的瘾来了。”
“休得胡说。”杨秀清将手在案上一拍,喝止住他,对韦昌辉说:“除了各县州府衙的旧有眼线,再找些可靠机灵的兄弟,分派出村,探听消息。”
韦昌辉连声称是。
“有件差事交给天妹做。”杨秀清将目光投向赵杉。
“什么?”一直在旁像是个局外人的赵杉听到话音,抬起头,有些茫然地看着杨秀清。她本是最乐于做个“听众”的,但并不是每次都能做得了绝对的局外人。
“阿妹带几个姐妹在村口做活,我料想三五日内,必有不速之客降临。”杨秀清扬着眉毛,显出一副惯有的自信派头,“若到时那些人问话,阿妹尽可这么说。”教了一番如何应对的话。
平日里宁愿抡锤打铁,也不拿针捻线的黄雨娇,这次却主动请缨,跟着赵杉当起了探马前哨。
两人与韦家几个妇女,坐在村口谷场的石墩上,自早至暮,缝衣做鞋。
前三日,风平浪静。直到第四日日中时分,来了两个生面孔的人。两人面色一白一黄,都是同样装束,头戴黑色瓜皮小凉帽,肩背蓝条纹包袱,脚穿黑靴,一身的青衣黑裤。
赵杉针上的线用完了,从线滚子上扯下一段,穿针纫线,抬眼瞟了瞟那二人,见他们一前一后,缓步而行,走走停停,四面窥视。心里明白这就是杨秀清口中那所谓的不速之客了。轻轻咳了一声,黄雨娇等人都点头为应,提起警觉来。
两密探行至赵杉等人近前,黄面皮的那个开口问道:“敢问阿嫂,此地可是金田村?”
赵杉抬头,说了声“是”。
“听闻这金田是个很大的村子,人口应是不少,怎么不见一个兄弟啊?”黄面皮又问。
“今年天旱雨少,地里禾枯苗干,男人们闲懒无事,都到镇上赌馆酒肆,喝酒耍钱去了。”赵杉照着杨秀清教给她的话说。
“向阿嫂打听个人。”白面皮上前一步,弯腰低头,言辞恳切的问:家母重病在床,气息奄奄。闻这金田村里有个神医,不知他是否在家?”
“神医?莫非是来寻李俊良的?”赵杉心疑,弄不清他说的到底是哪个,只能含混而答:“我们这村里有好几个神医,分住在村东村西,不知是要找哪个?”
“好几个?”白面皮疑惑地皱起眉,与黄面皮耳语两句,步出谷场,向村东走去。
赵杉见两人入了村,招呼黄雨娇等人起来,回去吃午饭。几人吃罢饭,复拿了针线衣料,到谷场上做活。
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时,才见那两个密探从村西头出来,韦昌辉与几个庄客在他们身后,打躬陪笑相送。两个密探站在村口,停步看了赵杉她们片晌,才起脚上了大路。
赵杉感觉到了有人在盯着她看,却只假作不知,闷头做活。待那两人去得远了,方起身问韦昌辉:“他们是来求医的?”
韦昌辉道:“求医是假,顶着微服查访之名,打秋风要银子是真。亏了阿妹那句摸不着头脑的话。不然,怕是会有大麻烦。”
赵杉也无心去探问内中的玄机,只依旧每日缝衣做鞋。
送走了暗打秋风的密探,又迎来了明要银子的官差。浔州府知事与经历先后数次摆着仪仗,带着卫队,以督查秋粮征收为名,造访金田,都被大把的银票塞住了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