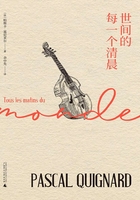老牛从床板上坐起来,一直在唉声叹气。
昨日整整一天,过得实在是太刺激了,简直如梦如幻。大中午的,二爷惹事泼大粪;等跑到街上,二爷又去帮人家赌棋;帮赢了,人家居然又想拿刀子捅他;然后二爷又忽悠人家,还做出一手好菜,生生让人家留他住下;到晚上又来一群大汉,明明是要下棋,忽然又要打要杀的,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好像又对他好得不得了,还输了二十五贯钱在他手里;最危险的莫过于大仇家最后登场,居然没找到他就这么走了——
唉,这样的日子,多过一天怕是都要折寿哟!
老牛望着窗外红彤彤的朝阳,心里菩萨佛祖地拜着。
“早啊,老牛!”身边的二郎终于醒来,伸个懒腰,打个哈欠,乐呵呵地跟他打招呼。
“二郎早,俺这就去给你打洗脸水!”老牛急忙报以一笑要出船舱。
“刚才你看着外面发呆,是求菩萨保佑今天别像昨天一样吧?”宁二爷脸上露出淡淡的坏笑。
老牛吓了一跳,这位爷怎么连自己想什么都知道?嘴里直说:“没、没有!”
“呵呵,别装了,我知道。现在晨时了吧?等会儿你上街溜达溜达,要是我物色的人靠谱,那咱们今天就平安了!”宁泽说完,又是一个大懒腰。
“平安了?”老牛有些不相信。不过想想,好像也很可能,经过一天的折腾,他觉得这位小爷身上发生什么都不算稀奇:“那我去打听什么?”
“看看陈金龙在不在家!”昨晚的密谋,他肯定不能让老牛知道。
“好,我这就去!”老牛穿上鞋,赶紧出门,临了忽然想起二郎还没洗脸,又规规矩矩打了一盆水回来,才匆匆离去。
等老牛走远,宁泽才慢吞吞下了床,抬手闻一下臂弯,头一歪差点被自己这身臭味儿熏死过去。赶紧把身上脱得赤条条地,拿起盆里白布开始使劲擦拭身上。好家伙,这身滋泥,真是层出不穷欲罢不能,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生生把一盆清水洗成了深灰色。
“这白毛巾,怎么还会掉色呢?”哪怕是他一人独处,也必须找个台阶好让自己有勇气面对这尴尬。
才细细洗到下部,忽然听到外面一阵疯疯癫癫的笑声传来:“二郎,二郎,真的不见了,真的不见了!”舱门撞开,老牛像打了鸡血一样扑进来,一脸的崇拜和开心。
“卧槽,这么快?”宁泽急忙背过身子,让出半边没什么个性的屁股对着老牛:“真不见了?”
“不见了,陈家正满城疯找呢。说是昨天半夜好好在家,天亮就没了人。床上留下一把刀!”
“好小子,有点执行力!”宁泽狂赞一句。赶紧把昨天包袱里准备的一身干净衣服换上,又让老牛重新去打了一盆清水,还特地交代连毛巾也换掉。
洗得清清爽爽的宁泽摇摇摆摆走出船舱,骄阳似火,白衣胜雪,眉心一颗红痣映得鲜艳欲滴,蓬松的头发随意用半截筷子插了一个发髻,水面风来,襟袖飘飘,若有人从远处望他,真是说不出的蕴藉潇洒。
“可惜这一身的短打扮,啥时候弄件长衫穿穿!”宁泽很不满意自己的平民衣服。平民只能穿过膝短衫,有功名的文人、捐了钱的士绅和衙门里的官吏才有资格穿长袍。
“哈哈,真想不到,二郎是如此的一表人才!”张顺远远走来笑道。
“二哥谬赞!”换了衣服的宁泽像换了个人,一派世家子弟风度,含蓄温婉。搞得张顺一愣,还真没什么心理准备,只好嘿嘿讪笑两声,低声道:“听说没有,昨晚上陈衙内竟被人掳了去。”
“哦?有这等事?”宁泽忽然鸡贼地笑着,两人相视,大大滴开心畅快。
张顺觉得有点服这小子了,忽悠功夫简直一流,自己是怎样着了他的道儿,一路路被他带着走都想不起来了,更别说昨夜那个方小乙,一定又是被他胡言乱语才做下这等大案。到底当时情形如何,张顺不知道,但他打心底觉得眼前这个二郎,似乎真有些本事。
河风凉爽,二人索性在甲板上席地而坐,享受这难得的清凉。
然而宁泽开口就煞风景:“呵呵二哥,陈家出事,你须得小心喽!”
“啊?关我鸟事?”张顺一脸的懵逼。
“嘿嘿,儿子失踪,满城拿人。身在官府,难道人家不报案么?报了案一查,便知昨夜陈金龙来过这里,还高高兴兴带了几十贯钱回去。你说,县太爷要不要把你捉去大刑拷问一回?”
“哎呀直娘贼,这事儿好像不是俺干的吧?二郎,你可不许袖手!”张顺一急眼,紧紧揪着宁泽裤袋说道。
“嗨嗨嗨,注意你的素质!放心吧,兄弟早给你想好了。不过,这些些许许的皮肉之苦,恐怕少不了。二哥,你若怕,那你等我先跑远了,回头再供我出来得了。”
张顺吼道:“你这可是小瞧二哥我,岂是如此无义之人,你但说,我照做就是!”
宁泽见他上道,这才微微一笑,抱着他脑袋细细说了半天,说得张顺连连点头,终于舒一口气:“这主意不错,这关恁是过得!”
宁泽这才又掉过话头,和蔼地看着张顺:“二哥,昨日小弟跟你说的事,可放在心上没有?”
“咳,正要说这个呢!”张顺一挑拇指:“二郎,啥都不说了,俺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终于得到张顺的明确答复,宁泽一颗心终于安稳落下。昨天所有的一切铺垫,都是为了这个答复,这才是他真正的目标,夺回家产,重振门楣,就靠这一买卖!
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昨晚床上详细推演,敲定,现在剩的是如何落实。他不能确定张顺的执行力有没有方小乙那么高,但也只能靠他了。
“二哥,我准备这样安排:第一,你须得多派几个沉稳没话的兄弟,细细打探那王炳林的行动规律,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走;第二、也要弄清那张翠儿的情形,是一个人呢,还是有老鸨儿妈妈陪着;是有人服侍呢,还是自己料理;是住里间呢还是外间;房里什么摆设,什么朝向,能越清楚就越好。”
张顺沉吟道:“头一件也还容易,兄弟们平日都有出进衙门送鱼的,要打探没甚难处。只是这第二件么——”犹豫片刻,猛一点头:“也罢,破点钱财,也须弄了来!”
宁泽放心了,展颜笑道:“这就好。还有第三,等探听到了实情,定下日子。到那日,我需要你带着几个胆子大能乔装打扮,脸皮又厚会装疯的兄弟跟着,有没有难处?”
“这个使得,没问题!”
“嗯,最后一样,你得帮我弄几件物事,到时候我要用——”
一番细细的谋划,在两人不断的推敲中渐渐周密。作为一个参与者和执行者,张顺从刚开始忐忑的心情,被宁泽一句句轻描淡写却无可置疑的计划,甚至可以说是指示中,变得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
知道最后一个步骤敲定,张顺自己都忍不住摸着胡茬嘿嘿痴笑起来:“如此,怕是弄不死那老咬虫!”
“呵呵,切记,怎么弄都可以,只不许把他弄残弄死,否则,咱哥俩做这些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这个俺省得、省得。要是换了个空肚鸭来,岂不是前功尽弃?”张顺笑道。
“好了,今天便是这样,小弟也要同老牛上街溜溜了。”宁泽双手一拍膝盖便要起身。
张顺奇道:“不是说多住两日么,怎地便走?那小衙内虽不见了,可那笑面大虫还在哩,撞见了如何开交?”
“他家都成那样了,还有心思管我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那我也服了他。”宁泽打个哈哈,带上老牛扬长而去。
虽然离家不远近在咫尺,可是昨天的心情和今天已经截然不同,宁泽居然有些归心似箭的感觉。走在大街上,不住地加快脚步,匆匆朝宁家老宅走去,累得老牛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等到了家门口,因为正院已被陈金凤占据多时,只能绕从旁边小巷里走侧门进去。来到侧门,门环紧闭。老牛止不住的兴奋,赶紧去扣门环。可是通通通通十几声敲过,就是无人回应。老牛诧异地转头看着宁泽。
宁泽也觉奇怪,正要上前亲自敲打,旁边一个声音悠悠叫道:“唉,二郎莫敲了,没人。”
宁泽急忙回头,却是巷口一个摆小摊的邻居,他记忆里没这个人的印象,只好拱拱手笑道:“那,他们哪儿去了?”
“作孽啊!昨日午后不就,陈家便来了许多人,把这院子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俺们哪敢靠近?只好远远瞧着。只听你们一会儿哭声一片,一会儿又是翻弄捣柜的声音,你老娘和你三弟,竟被他们赶了出来。连个衣服包裹都没拿!”邻居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摇头叹气。
“啊?!”宁泽双目喷火,两手攥得紧紧的咬牙问道:“那他们到底去了何处?”
“只见你娘带着三郎,哦还有你家牛嫂,一起慢慢朝南门外去了,临走偷偷对我说,他们只好去财神庙暂时存身,让我碰见你们告诉一声呢。”
“有劳老丈!”宁泽重重作一个揖,头也不回,大步朝南门走去。
财神庙。
好像天下每个县城都有一座财神庙。
庙里的财神据说掌管着天下财富,他想给谁,就会让谁发财。
可惜几乎天下的财神庙,没有一座是干净、整齐、像样的。全都破破烂烂放在那里,财神的塑像色彩斑驳,脱得七零八落,一手举着断了半截的钢鞭,一手压住无头的黑虎,就这么故作姿态地看着这冷清的财神殿。
财神庙的门口永远会贴上一副对子:手持钢鞭长进宝,身骑黑虎镇财门。
然而他却连自己这点微薄的身家也镇不住。
一年到头,人们只有在最肯花钱的那几天,拿几柱香,两根蜡,来敷衍敷衍这个掌管天下财富的落魄鬼。
滑稽的是,那个本该是穷酸的孔夫子,偏偏也在天下每个县城都有一座文庙。金碧辉煌,气宇威严,天天冷猪肉,享尽尊荣。
是不是很讽刺?
不是,这只说明一个道理:钱,虽然人人都爱,却不值得尊敬!
可更讽刺的是,那些从来只拜圣人不拜财神的人,却没几个是不爱钱的。他们气度威严,冠冕堂皇;他们口吐莲花,正人君子。一转身却猥猥琐琐数着那肮肮脏脏偷鸡摸狗赚来的钱,半点违和感也没有。
唉,人世间的事,真是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