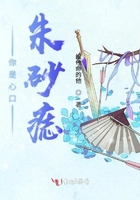严氏眼里似乎只有艾草的肚子,沈规既然是来看艾草,她作为主母说上几句,就该识趣些离去才是,可左等她也是不走,右等她也是不走,连沈规都要走了,她还待在艾草屋里。
艾草身为姨娘面对着主母,哪有一刻的放松舒心,又怎能安心养胎。
“好了,她又不是三岁小孩,这屋里又是婆子又是婢子,你难道要抠了眼珠子放在她身边才肯罢休吗?”
沈规扔下这句话就走了,阿元跟了几步,讪讪的停了脚,她还盼着能把沈规给拖到严氏屋子里呢?
严氏和沈规之间有没有姨娘,姨娘身子方不方便侍奉,好像对于他们俩的关系,皆没有半点影响。
阿元愁苦的看了严氏一眼,她却半点不为所动,终于舍得走出艾草的屋子,欢欢喜喜的道:“走吧,去厨房看看给她炖的补品怎么样的。”
连阿元都觉得严氏很有些问题,‘有什么好叫她这么欢喜?’未免也太贤德了些,阿元觉得贤德这个词形容的也不是那么妥帖。
长夜漫漫,沈规依旧睡在书房里头,辗转反侧,难以安睡。
郑令意彻夜难眠,吴罚静静地陪伴着她,两人思量着对策。
郑双双则觉得,自己快要淹没在这长夜里了。
夜来人静风凉,寝殿内门没有关好,不知哪处漏进来的风将她吹醒了。
许是停了药的缘故,又或是因为睡前硬吃下了半碗米糊,郑双双身上有了些力气,艰难的从床上挣扎起来,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这些时日,只有花腰一人伺候的尽心尽力,她累极了,已伏在床边脚踏上睡着了,月光落在她身上,像一条单薄的蚕丝绸子。
郑双双坐在床沿边上看了她一会子,将自己身上裹着的一件袍子扯下来盖在她身上,起身从花腰身边迈了过去。
今日月明,她想再看一看月亮。
屋里寂静,外头却还热闹着,月下虫鸣,闹中有静。
天地静谧,岁月流转,不会因一个人的境遇而改变。
郑双双穿着件素白的中衣,靠在院中树下,看着天上的澄澈明亮的月,忽然喊了一个人。
“娘。”
她只喊了这么一个字,就再说不出什么,像是不敢,又像是觉得自己不配。
黑洞洞的内门紧闭着,突然就开了,花浮左右手来回扔着一个荷包,从门里走了出来,月光将她脸上的笑容照得清清楚楚。
冷不丁瞧见一个白影站在树下,花浮吓了一大跳,看清是郑双双后,她恐惧未散,又添几分虚心,将荷包藏到身后,道:“娘娘站这做什么,奴婢扶您进去歇着吧。”
“我想赏月。”郑双双眼神空洞,像是压根没注意到花浮的异样。
“娘娘好兴致。”花浮已将郑双双看做一个死人,讽刺了一句,竟就自己歇去了。
郑双双的眼神从虚化至凝神,落在花浮的背影上,蓦地亮了一瞬,像是这月光,又给了她一些生命之力。
月隐日升,天亮了。
皇城小南门开得最早,宫里的采买最是要挑剔,果子连夜从树上摘下来,连着绿油油的枝丫,凝着一片一片的露水,新鲜无比。
“这位新牵上线的小郑大人倒是乖觉,每每总是多出一成之数供咱们吃喝。”
两个负责采买的太监拿着一串杏子,边吃边说闲话。
“生意人哪有老实的?”
“也是。”
搭上皇家,可比什么金打造的牌子还有用,鲜果斋的生意越发的好,夏日里上市的果子又多,郑启君狠狠的赚了一笔,惹得不少人眼红的厉害。
吴柔香便是其中之一,她不善持家,没有理财本事,嫁妆一年薄过一年,明知底下人里蛀虫不少,却没法子清除,她心烦的很,闭目塞听想要欺骗自己,可这银子又不能凭空的长出来。
吴柔香又撺掇着苗氏和钱氏去蔡绰然跟前说项,说她们三家凑在一块,要入郑启君的生意。
苗氏自然是不会去淌这趟浑水的,她内宅之事把持的住,虽然打理产业也不怎么精明,不过郑容尚是一把好手,虽然身子骨不济,但颇有识人之能,任命人才总是很准,她的日子可比吴柔香好过多了。
钱氏倒也是囊中羞涩,可她心机颇重,怎么肯让自己做了这个出头的椽子?
吴柔香只好自己去说,那日郑启君正好在,简直叹服于她那城墙般厚实的脸皮,道:“大嫂嫂莫不是说笑吧。”
“哪个同你说笑了,掏了真金白银出来同你做生意,有什么可笑的?”吴柔香急道。
搬着拾柴火,搭炉灶,杀鸡鸭,这才能最后分一杯羹,眼瞧着菜都上桌了,只端个碗过来说自己出了力,还理直气壮的要分菜吃,这不是笑话又是什么?
吴柔香使出水磨的功夫也没叫郑启君松口,有些绷不住要骂人时,郑启君忽地道:“城北的吴记漆器可是嫂嫂的嫁妆?”
吴柔香叫他这样问上一嘴,不由得有些警惕,道:“是又怎样?你怎知道?”
“不过是看挂着吴字招牌,漆器又是京中难得佳品,所以打听了一下。”
郑启君说得合情合理,吴柔香也就信了,这个铺子是她嫁妆里最赚钱的,从前吴老将军将这间铺子划给她的时候,乔氏难得说了吴老将军一句好话,她这个爹,到底是疼子女的,吴柔香心里难得忆起这个爹的好处来,不过也只是一瞬。
“漆器这样的好,怎么没想过做皇家生意?”
蔡绰然看了郑启君一眼,他这话,怎么像是要替吴柔香牵线。
吴柔香也听出来,只是有些不敢相信,狐疑道:“宫里的漆器大多用得是江南李家,我这铺子虽也不逊色于李家漆器,可毕竟供不住宫里那样大的花用。”
“李家毕竟隔着路途,宫里偶尔间要用个什么漆器,都是叫人出宫采买,吴记近水楼台,若能抓住这条路子,打响了招牌,生意岂不就越做越大,偏京、硕京,一路做到南边去也未可知。”
吴柔香被他说得心动起来,一下站起来要追问郑启君是否要替她引荐,郑启君伸手一挡,道:“诶诶,嫂嫂可莫要求我,我也就是这么一提,嫂嫂怎么说也是国公府的长媳,难道连点门路也没有吗?不至于吧。”
郑启君这明晃晃的讽刺自然难听,可人家刚给了条赚钱的路子,听起来也并不难办,吴柔香没发出火来,只觑了他一眼,
也没道谢,就走了。
“哪有这样的人?”蔡绰然厌恶道,又问:“你今个怎么这么好心,教她赚银子?”
郑启君微微笑着,在蔡绰然耳畔道:“有用。”
如此一句,蔡绰然自然听不懂,正要细问,耳廓尖尖叫郑启君用唇一啄,她浑身一麻,顿时娇羞不已,光顾着捶打郑启君去了。
…………
郑令意今日在家中设了小宴,要谢过沈规帮她偷偷送药给郑双双。
郑双双的命被延住了,却好不利索,郑令意还担心着,但也比先前那般无头苍蝇似的乱撞,要好过许多。
沈规也是心里一松,那个女子果然没这么容易就折损了,惯会装相的人,大多是想要好好活着的。
不过离能放心还远的很,传信人说,郑双双宫里冷落的连苔藓都长成厚毯一块了。
席上大家都没有提这件事,只是沈规受了吴罚和郑令意的敬酒,彼此心照不宣。
见着两人当着他的面还要你给我夹菜,我给你勺汤的,沈规把筷子一搁,酸道:“你们腻歪够了没有,还让不让人吃饭?”
酱生眨巴着眼看看他,又看看自己的父母,他从小看着父母恩爱,舅舅娶了舅母后更是变本加厉的腻人,他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童言无忌的问:“您和叔母难道不这样的吗?”
郑令意知道沈规与严氏素来不睦,怕他听了心里不舒服,连忙道:“小小年纪,竟还打听起长辈家事来了。”
“你也不必拿我当个花瓶供着,他小孩子一个,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我同我家那个,哪来的这些浓情蜜意之举。”
沈规夹了一筷子凉丝牛肉吃,语气听起来是无所谓,到底是垂了眸子不欲叫人窥见情绪。
这些感情之事,旁人怎好置喙,吴罚想了想道:“到底是快做父亲的人了,也是大喜一件。”
这自然是高兴的事情,沈规笑了起来,听见酱生问:“是弟弟还是妹妹。”
“如今怎么知道?”郑令意用帕子拭了拭酱生嘴角的汤汁,道。
“我倒盼着是个文文静静的姐儿,家里小子实在是多。”沈规目露神往的说着。
寻常人家说起生男生女,总归是说男孩好,女孩也好,这个‘也’字,把‘好’都削薄了几分。
不过郑令意想想张氏那院子里成天收拾且还乱糟糟的样子,深信沈规说的是真话。
不过一想到萱姐儿伸手拽她祖父的胡子壮举,郑令意抿了唇只笑,谁说这女孩子,素来就是乖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