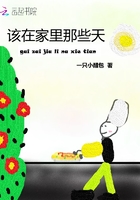李鸿章是个伟人,但他也有软肋,那就是对金钱的迷恋。瓦伦丁·吉尔乐爵士曾有过很好的机会在当地研究李鸿章和他的事业,他在1896这样写道:
“就连他的崇拜者也承认,腐败以最大最无耻的规模在他的亲朋好友中繁盛起来,这些人是他在社会上的追随者和政治上的支持者;很难让人相信他的双手是干净的,因为他以巨额的财富而为人所知,许多人说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腐败行为如何影响了他的军队管理,他的裙带关系是如何直接导致了海军在1894年到1895年的失败,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他的两位相对比较廉洁的同代人和评论家,即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的看法,自乾隆时期富可敌国的大学士和珅以来,李鸿章和大太监李莲英要为公然腐败的风气负有相当的责任。
维新派的报刊的确喜欢把李鸿章比作和珅,也喜欢唤起这样一个事实,即和珅的悲惨结局是由他的无度贪婪引起的,他在别人心中会唤起贪婪的回忆。李鸿章实际拥有的财富可能被过分夸大了;其财富肯定远不及我们洛克菲勒家族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但在中国也算是十分巨大了。在远东地区没有遗嘱检验和遗嘱公证;而且也没有像收取所得税的欧洲一样,有规避性的匿名财产。这个有钱的中国人把大部分积蓄投资在了各种零售业中(比如钱庄、典当行、鸦片、食盐和粮食等),其资本在这些行业中可以赚取极高的利润;于是他的资产成了公共财产,随着他操作范围的扩大和贪婪程度的增加,他的富有名声越来越大。他把另一部分财产变成了可动产(比如金条、珠宝、皮毛和翡翠)。于是在1894年底,当厄运降临时,坊间盛传他的可动资产在他的一个儿子的负责下被秘密向南运往了安徽老家,整整一船的大箱子、板条箱、盒子和袋子,正如1901年慈禧在外地暂住后返回京城时带了整整一列火车值钱的东西一样。
随着财富的积累,李鸿章的贪婪欲望越来越大了。在与“常胜军”共同镇压太平军的时候,他已经表现出了很多贪婪的迹象:他与戈登及常胜军其他军官的关系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一直不愿放弃支配薪饷的权力。他宁愿让军队靠打劫平民以维持生存,也不愿从自己的支票上拨出定期的给养。无疑,前面一章已经讨论过他个人对金钱的考虑影响了他的决策,在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削弱了他的决心和意志,他考虑到自己在朝鲜的既得利益,害怕战争的负担会让他的财产严重受损。这些都是不需争辩的事实。但当我们为之评论和谴责他时,应该记住盗用公款在东方是官僚的权力,是可以被接受的一种阶级特权。
在中国人的是非观里,这些在公共服务中有成就的官员可以把这种财富作为报酬。老百姓并不是不尊重官员的清廉,但他们认为这样的品质是不正常的。就如同他们对张之洞这样清廉的总督所具有的世俗的智慧所持的态度一样。对于这个穷学者,他们的尊敬之情里混杂着同情心,这个人无法向他们教授圣人的智慧,即“有钱人的财富是他坚固的堡垒”,以及“礼物为人留出地方,带他接近大人物”。
李鸿章很好地运用了东方经典的智慧。这种智慧代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在他身上十分明显,由于他名扬四海,由于他显然打算接受其他的理念和方法,这是他与欧洲文明接触的结果。亲眼见过李鸿章作为管理人和外交家而取得成功的欧洲人,希望他成为新制度的预言者,这个新制度会带领官僚们走出贪污的荒野。他们认为每一个伟人,无论他多么杰出,总是祖先和教育的产物,就像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他无法改造那个造就了他的社会:
“伴随着整整一代人,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随着这代人的制度、语言、知识、行为以及大量的艺术和工具,他也是巨大力量凝聚的产物,这些力量已经协作了很多年了……所有这些变化的产生都在他这代人中存在着主要的原因,而他是这些变化直接作用的结果。”
人们想要找到官僚阶层中诚实的美德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阶层的理想和行为是产生他们的制度的结果。吉尔乐爵士(写到李鸿章时)这样公允地观察到:
“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一个欺骗性组织。一个中国人一旦进入官场,他就属于寡头政治集团了,这个集团完全和国家的其他人是分离开来的,完全被它世袭的高傲所联结,捆绑在自身利益上。他也许会努力保持廉洁,但如果他妨碍了别人,那么自己就会惹上麻烦。”
李鸿章对于这个孤注一掷的想法从来都没有尝试过。他和慈禧太后一样,都小心谨慎地奉行着官场弄虚作假的传统,书写着激情四溢的奏折,描述着他忠诚的管理,宣扬着裙带关系的丑陋和大公无私的美好,用绝妙的古典风格书写着有关道德的陈词滥调。但是为李鸿章总督事务之外管理财政的那些人,和行政人员是不同的,他们非常不适合那种为国家金库担心的职业。
李鸿章的衙门允许“压榨”这样的古老权力,并且大众接受了这样的行为,但在他担任总督的某个时期,衙门的名声在百姓心中非常臭。中国舆论,按照惯例都希望官员走一条介于贪污和责任之间的中间道路。李鸿章女婿张佩纶那不知廉耻的流氓行为和随之导致的危险后果已经为人所知;张佩纶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却也典型地代表了李鸿章手下那些提着钱袋子或坐在海关收款处旁的官员们的样子。这些人身上带有上司所有的缺点,却丝毫没有可敬的品质。
李鸿章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宫中的盟友大太监李莲英一样,连再小的钱财也不放过。他有着敛财的卑鄙本能,这和他在其他方面的宽厚品质相矛盾。比如在1900年9月,当所有人包括逃亡中的慈禧太后都急着盼他从上海赶到北方去承担他为中国提供的服务中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任务,他的行程却神秘地耽误了两天。谣言说俄国人提出了新建议,让他乘坐俄国的汽船去北方,因为这比坐英国的轮船要安全;还有说是因为克劳德·麦克唐纳德爵士反对李鸿章的和解政策,等等原因。事实上他耽搁行程的真正原因是他正想方设法从上海道台那里压榨他给圣彼得堡发电报花掉的3000两银子,但是上海道台并不上当,两人心里都清楚得很,在这样的时局下,指望京城报销这笔花费是不太可能的。李鸿章在家里的节约习惯大家是知道的;他喜欢寻欢作乐,却没有心情对付花钱的痛苦。
李鸿章在总督任期中,不止一次地在御史们的谴责下被迫公开表示自己廉洁正直,但当时的舆论裁决并没有受到影响。的确,他所积累的巨额财富以及他在重要岗位上安排的那些人的品质让人们毫不怀疑他贪污的行径。他的某些心腹在大把大把捞钱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厚颜嘴脸,常常引发一些严重的丑闻,为此朝廷不得不出面谴责李鸿章。郑克同因为在巴黎没有授权就借款而被革职;李凤苞是驻柏林的外交官和巡洋舰采购员,在国外遭到批评;盛宫保和张佩纶在中国已成了笑柄。与李鸿章比起来,这些人的手段是笨拙的;但当李鸿章反击对抗时,他坚决地支持这些人,所以他的敌人把他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视为同样的性质,很自然地认为他也从他们的身上分到了不少好处。他在处理比如黄河整治和运输粮草等事情上,也由于对财富的贪婪而玷污了名声,这就如同他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管理军事事务时表现的一样。
与注重实际的常识相比,李鸿章头脑中迷信的一面经常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和慈禧太后一样,他很少让迷信改变他为了私人利益或公共政策而采取的行动。在他的一生中,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相信神灵的影响,相信天地间存在无形的力量,如同他老家最卑微的辛劳者一样,他的信仰是儒家不可知论和具有返祖趋向的超自然信仰的奇怪混合物。只要是和守护神或鬼魂相关,他总是准备好给予合理质疑的利益,只要他的腰包不会马上受影响。
外国观察家对李鸿章在天津衙门从事的进步活动往往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原始的迷信只是对公众感情加以巧妙调解的一部分,并不是真实的;但外国观察家在这一点上弄错了。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李鸿章不会讨论不朽的神灵或者魔鬼的力量,但他对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总是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在1864年的时候,他庄重地给皇帝交了一份奏折,请求在常州的一个庙里树立一块皇家石碑,以此纪念这里的守护神,感谢神灵的帮助使其击败了造反派。
1887年,北方各省遇到了特大干旱,于是李鸿章派人去请神圣的求雨碑,此后便上奏皇帝,说这样做对龙王的影响十分让人满意。1894年,我们再一次发现,李总督在一份长篇奏折中庄重地向朝廷报告,天津附近大运河两岸河堤上有个十分危险的裂口,是一个凶恶的河神造成的;后来花了很多钱在供奉这个河神上,最后神怪被安抚好,裂口也被填好了。为了这件事,朝廷在李鸿章的请求下赐予所谓的河神一座庙宇(政府开支)。
但是如果李鸿章敏锐而务实的眼光意识到了有利可图的机会,这种对古代祖宗的崇拜和迷信就会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上了。比如在他的管理之下,第一条电报线在天津和北京之间连接起来的时候,地方保守分子破坏了电线和电杆,以此发泄心中的愤恨。他的下属告诉他破坏这些东西是由管风水的神灵愤怒所致。李鸿章毫不客气地拒绝承认此事和风水有关,下令让属下严惩搞破坏的人。同样,吉林的鞑靼将军裕禄极力阻止吉林到锦州的铁路和新唐铁路在奉天连接,当时反对的理由是这条线路会破坏这座圣城的神灵安息。李鸿章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说铺设一条这样必需的铁路只会给奉天的风水带来好处。在这两个例子中,他都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在1900年,当外国联军计划拆除天津的老城墙时,绅士和贫民都向李鸿章请愿,要求停止这个工程,理由是如果城市没有城墙那么就像女人不穿裙子一样。李总督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说这些旧城墙已经失去了防御的作用,它们被拆除后是对大家有利的。
通过对旧城墙周边土地的拨款,很多土地投机商赚了大笔的钱财,他们当中有许多外国人,还有李鸿章手下的几个随从,而成千上万个不幸的居民变得无家可归了。李鸿章竟敢如此违背“老习俗”并干扰风水,通常都会有财政方面的充分理由。
赫德在他那部有关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的形势和前景的作品中,把排外运动部分地归结为西方伤害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他说他们“天生的自傲,有着广阔高贵且自我陶醉的无知背景”——为种族而骄傲,为智慧而骄傲,为文明而骄傲,为优越而骄傲,但他们的骄傲“受到了外国极大的伤害,让中国人性格中的其他闪光点受到了打击而无法做出反应”。
李鸿章肯定充分怀有这种民族自豪感,他相信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有着难以形容的优越性,通过敏捷的思维,他通常能够把他对实际问题的无知藏在睿智的外貌之下。但他的无知在很多方面还是“广阔而高贵”的,就像他那个著名的同僚——武昌的总督张之洞一样。直到1895年他出使日本为止,李鸿章一直夸口说他从未出过国门一步,除了几本翻译过来的英国教科书外,他对欧洲文学和科学毫不清楚。甚至在商贸和财政这些实际事务方面,他也经常是误入歧途,自负地认为经典知识已经足够让他以平等的姿态与外国的特权者和金融家打交道,以至于在很多时候他都会被那些西方冒险家弄得非常窘迫。但是他天生的智慧通常告诉他用柔道智慧来掩盖缺乏的知识,他的对手会反而显得非常愚钝。跟外国人打交道时,他总是习惯性地把话题引导到他喜欢说的事情上,经常问些不相干却看似天真、通过深思熟虑的问题,以此向敌人发起口水战。这些简单的技巧为他赢得了世界名声——举世无双的具有东方智慧的外交家。
但是,在李鸿章为直隶统治者之前,和戈登的交往让他认识到,尽管对一个总督来说无知是可以原谅的,但它却是中国官员的弱点;中国官员应该学习外国人,掌握他们的机械技术和设备的应用技能。由于对欧洲文明的伦理和思想不甚清楚,所以他觉得中国只好通过教科书来掌握这些技巧和器械,以便与西方在平等的关系中打交道。他虽然聪慧,却似乎也没想到国家的衰弱不在于机械,而是在于制度;如果不对官僚集团反复灌输责任感和公益精神,那么任何军事改革和财政改革都是无用的。他认为只要用一些西方的科学就可以加强东方的智慧,仅此而已。
当李鸿章鼓励人们把欧洲大量的科学和历史著作翻译成中文时,却也仍然很乐意地讴歌神农或女神元妃,并从孔孟著作中引经据典。1877年,他请求朝廷设置一所研究外国文学和科学的教育机构,当时他的目标不是去干涉已经存在的为仕途而设置的经典教育,而只是在官员之外培育一批人,去接管熟悉孟子著作但无法胜任的特殊岗位的人。
在李鸿章自己的总督生涯中,他经常因为自己不懂外语尤其是英语而感到遗憾,因为这种无知让他不得不和翻译员分享官方的最高机密;因为让接受四书五经教育的人去管理铁路、电报和外交事务而导致浪费,他也感到十分懊悔。所以,作为达到明确目标的手段,他提倡“师夷”,于是到1898年为止,他一直被维新派人士当作进步者的领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