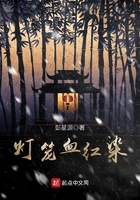陈其说感到奇怪的是,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卢浮宫博物馆了,但是那天晚上他看了看窗户,外面阴雨绵绵。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张人脸。
于是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去卢浮宫那个地方,他从不相信所谓的直觉,但他觉得在那个地方能偶遇她。
他出门走得很急,围上了红色的围巾,说来奇怪的是,他曾经最讨厌这个颜色,但是现在他在他的整洁的床上只能找到这个颜色的围巾。
今天的天气不太好,雨不大却增添了凉意。巴黎的秋意太浓已经快入了冬,陈其说的帽子和手套却找不到了,单薄的围巾在风中飘荡着,他一手拿着伞,伞也是红色的,是翡丽上次忘在他那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红色都找上了他,他讨厌红色,红色在他的眼里是嗜血的冲动,是魔鬼的轻笑,当然他并没有把他的这个想法讲给其他人听,他想着其他人或许会认为他疯了。他虽然觉得,疯子才是真正的天才,但他并没有把话说出口,他明白现实世界荒谬可笑什么都有,可容不下一个普通人的自白。
是的他是疯子,在他看来人人都是疯子,如果有谁不是疯子,那么多半无趣至极。
一阵冷风灌鼻,一向被人贴着谨小慎微标签的陈其说谨慎得呼吸着,渐渐地他感到凉意透过皮肤直进入了他的脑髓。他的脑子此时却异常得清醒,他的手上拿着一个已经有些凉了的塔可,在渐强的风和淅淅沥沥的雨中,他的手指尖刚刚失去了最后的暖意。
他的脚步在雨水形成的洼里越来越快,渐渐地消失在人海。道路两旁法国梧桐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有几只小鸟正在地上跳着,对许多的行人并不太感到惊慌,等到最后一刻才慢悠悠地闪避着。陈其说脑海中冒出一个想法,他感到有些不妥,在他的家乡的麻雀总是对行人十分地在意和警惕,那些鸟毕竟是没有丧失生存的本能,可是这些鸟已经太过安逸失去了对人的警惕,他觉得这绝对不是幸运。
成都在陈其说的心里没有巴黎好看,但是成都已经藏在他的脑海的最深处,陈其说觉得连他自己都打不开他的脑海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而那些潜意识,就让它们永远沉睡在自己的脑海吧,陈其说不是一个对自己坦诚的人,但他知道他没有选择。他曾经看了许多的心理学书籍,自认为不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学得差,不过他这样认为却并没有表现出来,一个成年的中国人如果总想像孔雀一样开屏去招惹他人对于自己美丽的关注,是不现实且幼稚的可笑的,陈其说在他认为他被逼隐藏时总会隐藏进人群,在阴影中他感受了自己的存在。
陈其说还没走进卢浮宫的内部,就已经有许多人在卢浮宫的门口和周围叽叽喳喳地拍着照,其中不乏许多中国的来客,对于他家乡的同胞的做法,陈其说早就见怪不怪了,但倒也并不赞同。陈其说是一个骨子里无比淡漠的人,您要是能钻到他的肚子里,就会看到那里面不过是灰暗灯光下的空气一样的透明状态。他对任何事物都感兴趣,他会钢琴和古琴,甚至会作曲。他相信一切都会越变越差的,换句话说,他不相信“永恒”这个词语。他是一个常常改变的人,但是许多人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陈其说曾经喜欢在朋友圈发着他的摄影作品,有时候其中还包括了他的自拍,他也幼稚得喜欢用九宫格来表达自己,但是他知道那根本表达不了自己。他之后再也没有在朋友圈发过他的自拍了,因为他知道她没有看到过,他想让她看到,他想感受到她的温度,他的心里除了那他自己都不愿意面对的潜意识,就只有她了。
他走着走着,已经走进了卢浮宫的内部。今天是星期五,但是人还是不亚于星期六星期天那么多。人潮涌动着,陈其说走了神,回忆起那年还没来巴黎的时候,高中一次五一节的时候他和一个人约好一起来巴黎玩,他问了问他爸爸在旅行社当老板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一个人时候的行程和路线,在得到那个叔叔的建议后制定了行程,他把一切准备好了,还满脸笑容却心中不悦得答应了亲戚们的代购要求。但是他所能记得的是在巴黎的那三天最终却几乎没有那个朋友的身影,他只是想不起了那个朋友是谁。陈其说的记忆有时候就像雨中的纸船,只是不知道到底漂到哪个地方了。下着雨,纸船沾湿了,陈其说的记忆变得模糊超市,而他的记忆很少会变得这样。他想起了以前在小学看过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又想起中学时学过的《周庄水韵》,中国的文章有一种更深层次涌动的东西,好像古典水墨画中看似无意其实特意而为的墨晕,晕染开的是中国人的诗意与浪漫,是中国人的柔情与倦意。是孤独与寂寞变成了艺术,翡丽曾经在中学时去过周庄,她回来后对陈其说说道:“周庄真的很好,只是到底有些太柔和了,我甚至觉得有些伤心了。”陈其说看着翡丽,没有告诉她的眼睛真的很黑,她的头发真的很黑。
陈其说的脑子里浮现起《周庄水韵》这篇课文,教课的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她的脸上仍然充满着女性特有的柔和的光泽,她的脸颊有点红扑扑的,声音很轻很细,这样的老师在2019年的中国不多了。老师脸上的柔和的色彩让陈其说想起自己在读《周庄水韵》时的感受,也是这样,柔和得泛着光,周庄的滤镜是中国古典诗意与传统文人的浪漫给它加上的滤镜。陈其说在巴黎的两年知道巴黎与中国有太多的不同,巴黎的确是艺术的城市,可是艺术家其实都有一种理性,他们都相信某些观念与主义,他们信仰某些哲学观点和艺术理念,他们有所追求,有突破挣扎。
记得小学音乐课的时候,音乐老师对陈其说说:“同学们觉得交响乐怎么样?老师在之前的课上给你们播放了中国传统乐器的音乐演奏,你们觉得和交响乐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来说说你们的感受呢?”
那天的温度也有些凉,陈其说想起在成都时之前去市音乐厅去听了一名中国钢琴家参与的交响乐演奏。陈其说从小喜欢听音乐,他更喜欢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在几十场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演奏会的熏陶下,他渐渐有些明白了这其中的相似点。中国的音乐总是带有诗意,有时候不过是一曲婉转小调也极富韵味。中国的音乐与绘画美就美在它们都充满了某种随意的潇洒与浪漫,神来一笔总是藏在细节里。他热爱这种神来一笔或者“画龙点睛”,陈其说在小时候看了太多的成语辞典,导致他常常在脑海里会蹦出几个成语。他想起了姜其果,他不知道的是姜其果此时也和他在同一个地方。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姜其果的身影,都快失去了自己的意识。他喜欢中国艺术的美,是因为那美从不带着一丝理性,那才是真正的中国的美。
翡丽还站在他的面前,他没有告诉翡丽的是:他其实和翡丽有着同样的感受。太柔和优美事物的会让人倦怠,那倦怠来自于柔和的风景让人想醉,一醉就难以醒过来了。陈其说不喜欢醉,他宁愿痛苦也不想醉,还好他这个淡漠的人并不常感到痛苦,除了有时候,比如想起她的时候。姜其果在他的脑海里一直不肯走,她的手还是那么冰,就好像他刚刚在街上时手指的温度那样冰。
人潮涌动着,蒙娜丽莎展品的的前面站着不计其数的游客,其中也包含了许多中国人。陈其说这接近两年的时间在巴黎看到了许多的中国人,他发现在巴黎的中国人其实并不一样。比如呆久了的中国人和刚来巴黎的中国人还是有些不同,他觉得刚来巴黎的中国人大部分都穿得非常华丽漂亮,而在巴黎呆久了的中国人却穿得越来越简洁,追求的是风格而不是好看了。他身旁的人真的太多了,许多人拿着手机对着蒙娜丽莎拍个不停,有工作人员过来阻止那些开闪光灯的人们。陈其说以前已经看过这些展品了,并且人真的太多了,于是他挪开了自己的脚步,朝一个其他的方向走去了。新来的游客喜欢朝蒙娜丽莎,汉谟拉比,断臂维纳斯和胜利女神这四样最热门的展品。
陈其说又走了神,他甚至走着走着差点摔了一跤。他只是想不起那个和他一起来巴黎却最终没有出现的人到底是谁,只记得那个人的头发和眼睛太黑了,脸色苍白,陈其说想起那个人是个女孩。女孩的化妆技术还很生疏稚嫩,画出来的妆容不够美。陈其说忘掉其他的细节了,只记得女孩脸上打上的腮红好像无数条毛细血管破裂从皮肤薄膜渗出的带点淡色乌紫的鲜血。陈其说突然想起这个人是谁了,是翡丽。上个月翡丽说好带她的女朋友一起来巴黎,但最终她独自前来,走的时候忘了一个东西,留下了一把红色的伞。翡丽的脸更加苍白了,她脸上的血管好像真的渗出了血一般,她的头发和眼睛还是那么黑,但是陈其说注意到她的眼睛里也有了迷雾。
原来是高一那年的五一节,陈其说约翡丽一起去巴黎玩,翡丽对陈其说突然严肃得问猜猜她在做什么,原本严肃和疑问这两个词是一点也不搭配的,可是翡丽偏偏就是要这样用,陈其说愣住了不到一秒的时间。翡丽在电话那边的声音突然失去了一切温度,她的声音变得很小很锋利尖锐:“陈其说,你知道吗,我在看一本书,那本书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书。你不是以前有一次嘲笑我,说我这么喜欢哲学,以后难道是想当职业哲学家吗?说真的,那时候我觉得你说话说得太重了,你是在嘲笑我甚至侮辱我,你根本一点也不了解我和哲学,但是说到底,现在我想通了,你说的对,就是这样,我想我是一个傻子不是吗?米兰昆德拉是捷克的哲学家,他把自己的哲学写进了小说,可我呢?我没有自己的哲学,我是个支离破碎的人,我能把自己的哲学写进小说吗?你知道我没那个能耐,就是那样,我没那个能耐,我想对你说的是,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我从还是个婴儿开始,从有记忆开始,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的父母一早就抛弃了我,从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我想就是这样,我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因为我不懂爱,更不懂什么哲学。我所懂的哲学就是其实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我所懂的哲学就是连我的亲生父母都不爱我,我又算个什么呢?我是一个弃婴,我想没有人会真的在意我我是正常的,我不是一个能让人在意的人,否则我也不会被我的父母遗弃……”翡丽那天晚上说了很多很多,她真的说了很久,陈其说一直听着,没有打断她,他想在这个时候做个安静的聆听者,他知道他不需要说什么,只需要听着翡丽的话,让翡丽知道他一直在。他听见翡丽说到最后声音仿佛在哽咽,他无法用手到电话那头拭走她的泪,他没有对她说他也喜欢米兰昆德拉,毕竟在她的眼里,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没有对她说她想知道的她想听到的,她知道她在等她的托马斯,但是她不是他的特丽莎,因为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萨宾娜,他要和与她一起对抗这个温度过剩的世界,这个媚俗的世界。他知道他们已不再年轻,但是他知道他们有能力凭着一腔热血对抗这个世界。陈其说感到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凭着他很高的视力在人潮里发现他的萨宾娜。
“果然不能相信直觉。”陈其说匆匆地离开了,走向了博物馆二楼的咖啡馆。
她突然叫住了他,陈其说却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