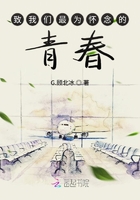现代政治撒风漏气,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瞒得住人。关于平房改造的事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在梨城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说好话的不是没有,阴阳怪气泼冷水的也不少。如今社会偏偏又是好话难出门,坏话传千里,卢定安怕夜长梦多,一些大人物如果望风扑影提前表了态就不好办了。同时他也怕自己变卦,就在市政府的大会议室里召集了一个会议。请来了各局、委、办的负责人,各区的区长、分管城建的副区长,以及市建委的中层干部和一些平房区的街道办事处主任……
卢定安的面前放着一个装满茶水的阔口大玻璃瓶子,这是用大号水果罐头改成的茶杯,外面套了一个手织的红色的塑料隔热网,他手扶罐头瓶子亲自主持会议:
“这个会我们酝酿了好长时间,也等待了好长时间啦……梨城这么大一座城市,不能像摊煎饼一样再向四外无规则地乱铺摊子了,要把人疏散出去一部分,还商于市,还绿于民,城市就应该有集中的大绿地,并趁机改造危陋平房,这是我们梨城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今天,我们就先务虚,请梨城大学建筑系主任夏尊秋教授,从宏观上讲讲现代城市的规划布局,以及老城改造的趋势。夏教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建筑学的博士学位以后,又做了两年的博士后,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权威了,大家欢迎。”
夏尊秋白额细肩,自然而清灵,一身淡茶色,长上装是西服领收腰身,下身配不开衩的一步裙,携带着一份矜持,一份庄重。讲课是她的职业,优雅而从容地开场了:“市长出了个大题目,这个题目在大学里至少要讲一个学年,我尽量把话说得简单明了,争取在四十五分钟之内,也就是用一堂课的时间交卷。许多具体问题以后我们还有时间讨论……现代国际大都市,是以有现代化的人为主旨。现代化的人除去知识、观念上的条件以外,还要有现代化的办公条件和现代化的生活居住环境,改善居住环境也是改变人,环境变了人必然也跟着变,所以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建设和改造之中。但并非摩天大楼越多越好,发达国家一些著名的城市也不都是高楼林立,有的甚至把高楼集中在一个区或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如纽约的曼哈顿。其基础设施也可相应地集中搞成大管道、大容量,节省能源消耗,便于配套和管理。然而在我们南方的一些城市,却出现了忽视城市规划,忽视城市长远利益,忽视城市的文化价值,迁就房地产开发商,盲目扩大土地批租,见缝插针、随心所欲地建高楼,布局不合理,后患无穷,加大能源消耗,增加交通流量,破坏城市生态因子,甚至会产生城市热岛效应。”
参加会议的大小官员们都大大方方地不错眼珠地盯着夏尊秋,不管你眼睛多馋、多奸、多贪、多毒都没有关系,这是官的。开长会的时候前边有个赏心悦目的女人在讲话真是幸事、乐事。无法知道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认真地听进了夏尊秋的话,有多少人在欣赏夏尊秋的容貌,开官会并不是经常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官场里好看的女人本就不多,能够坐到前面长篇大论讲话的更是凤毛麟角……开官会的时候思想开小差也是官的,不开小差的人倒是不多。就说眼下,会场上得有多少人在回味有关夏尊秋身世的种种传说?梨城官场里盛传她是前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杜锟的私生女,大家借这个机会正好可以仔细比较他们长得像不像。杜锟的儿子,应该算是夏尊秋同父异母的哥哥、河口区长杜华正也坐在下面,这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是感到难堪,还是感到自豪?卢定安不可能不知道夏尊秋的故事,为什么偏偏让她来讲这一课?不错,由她来讲这个内容比较合适,但梨城大学的教授那么多,市建设委员会优秀的工程师也不少,能讲这个课题的人并不是只有夏尊秋,这是有意给杜锟难看,还是巴结杜锟并得到了老头儿的支持?
给这些人讲课也真是难为讲课者了,深了不行,太浅了也不行,眼下这却是一种潮流,表明领导干部是多么的谦虚好学,甚至也可以算是一种开明和美德。好在夏尊秋出于职业习惯,往前面一站就极端敏感,谁在听课,谁走神儿了,谁信服自己,谁反感自己,都了然于胸。她未必不知道这些人会怎样想她,也未必感觉不出来下面各种目光的含义,但她无须交流和提问,自己的眼睛不在任何一张脸上特意地停留,也不放过任何一张脸,似看非看,视而不见。她额头光洁高阔,把高雅和睿智袒露无遗,且有自己的思想和久经训练的口才,足以镇住听讲者:
“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因此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就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建筑的本质是人性,在大地之上,苍穹之下,是人类生活发生的空间。城市的建筑,应该照顾到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城市的文化内涵,经济效益,环境观念,群众意识,空间变化,节能措施等等多元并存。好的建筑要体现‘六缘’:地缘——建筑的地域性;血缘——建筑的民族性;人缘——建筑的社会性;史缘——建筑的传统性;业缘——建筑的技艺性;学缘——建筑的时尚性。鉴于目前每个城市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对旧城区的改造更是迫在眉睫……旧城区,应该是土地利用率最高,能产生最高的经济效益。可我们许多城市的旧城区恰恰是最糟的。比如城厢区的同福庄,可以说是我们梨城的梨核,谁都知道这个梨核似乎有点烂了……如何提高中心区的经济效益,标志着一个城市的建设水平。应该让能够产生高效益的行业占据中心,一方面拆旧,一方面建新,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会议室里的大部分头头们,渐渐被夏尊秋的话而不是她这个人的身世故事所吸引,但不像听上级领导讲话那样做记录。官员们开会做记录首先是做给比自己大的官员看的,其次是回去传达时作参考,或出了问题时便于核对。对一个教授就用不着装样子,更没有传达任务,就轻轻松松地只是眼看耳听了。倒是市长卢定安不停地往小本子上写着什么,不知他是在记下夏教授讲的知识,还是在为自己等一会儿的讲话准备草稿。
夏尊秋顺手在大黑板上画出一个图形:一个狭长的直角三角形,在直角处写上三个英文字母CBD,她嘴里咕哝出一串英语单词,然后用普通话解释,底边这条线代表城市、建筑物和地域。她在直边顶端画出一个箭头,干脆不再写英文字母,直接标出汉字“土地效益(地租)”把三角形分成四份,在最里边的一份内写上“商业”,在第二份内标上“工业”,第三份是“居住区”,第四份是“农业”……她对着图形讲解:“这是目前我们这个城市的布局,中心区里应该以商业为主,现在却拥挤着太多的破旧平房,应该按规划在市外建几个大的新型住宅区,在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上要更具诱惑力,吸引大批居民疏散出去。大家看到的第二个格,紧挨着中心区分布着许多工厂,是城市噪音和各种污染的根源,也应该迁到规划的工业区去,腾出地方让第三产业进来,比如服务业、保险业、金融业等等,这就是所谓的‘退二进三’,也有人把它形象地称为‘腾笼子换鸟’。”应该说大家听得正在兴头上,夏尊秋却收住了自己的话头:“感谢大家听得这么认真,我占大家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就此打住。”
梨城多种级别的领导干部们,听惯了上传下达的套话,不管原先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却不能不为夏尊秋的风度、智慧和谈吐所折服,掌声也是由衷的。卢定安拿过了话筒说:“有人还想提一些问题,只能等下次讲课的时候再请夏教授回答了。等一会儿学校里还有她的课,我们就不能不放她走了,我们也休息一刻钟,再一次感谢夏教授。”
夏尊秋向大家点点头,由金克任陪着从前门走出会议室,她来到市政府的院子里,从手包里掏出遥控器,“吱扭”一声打开了汽车门,向金克任伸出手:“再见。”杜华正意外地从楼上追下来:“夏教授。”夏尊秋不解地看着他。杜华正也含笑对视,他风度修洁,脸孔白皙,带着一种喜欢与人比肩的自信:“我是河口区的杜华正,感谢您给我们河口区设计了一栋全市最漂亮的大楼,我还有一些事情想求助于您,但约了您几次都没能约上……”杜华正彬彬有礼,满脸诚意,连对他怀有深刻偏见的夏尊秋,此时也不能不客客气气:“您真是礼貌周全。”杜华正不想就这么被打发了:“您什么时候方便我去当面请教。”
夏尊秋立即警觉:“我一个教书匠,能帮上您什么忙呢?”“当然是您能办的。”“最近不行,我带的研究生要毕业了,还有一个国际会议要在我们系里召开,我得做些准备工作。”“我可以给您打电话吗?”“当然。”“那我们电话里再约时间。”
夏尊秋上了汽车,轻快地消失在大门以外。杜华正咂咂嘴,像是对金克任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自己有车,自己驾驶,这样的大学教授当得真够潇洒。”
金克任看看他,没有搭腔,也算是默认了他的话,两人一块儿转身进了楼。在他们身后又有一辆汽车开进政府大院,从汽车里下来的是杜锟,须发斑白,却面色红润,深目高颧,腰挺背直,仍然带着梨城顶尖人物的沉重威仪,由秘书搀扶着进了楼。参加会的人又都回到大会议室里,卢定安正要宣布继续开会,却看见杜锟从门口走进来,只好迎过去问候。前面的人“杜老、杜老”地喊着,对杜锟十分客气和尊敬。更多的人则是小声在议论:“杜头儿来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即便是那些当面喊他“杜老”的人,背后称呼他的时候也都冠以“杜头儿”。在姓的后面加个“老”字,显得谦和平易;在姓的后面加上“头儿”,就给人以活力和权威感,尽管他已经退休,好像仍然是这个城市的头儿。称呼表达了一种现象:梨城市重要部门的高中级干部,都有杜锟的部下,或经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或经他推荐而被提拔起来的,包括现任的市长卢定安和市委书记来明远。在官场中,这套由上下级关系组成的纵横交错的网络非常重要!
杜锟虽然年近七十,却精神健旺,气派威严,不矜而重,走进这样的会场,没有丝毫的怯意或不适,仍像一市之主那样顾盼生威。他心不在焉地应答着别人的问候,眼睛向四周踅摸,似乎是很随意地问卢定安:“我听说今天有大学的教授讲课啊?”
卢定安不无遗憾地告诉他刚讲完,于是,许多人都明白“杜头儿”突然出现的目的了。杜锟却立刻改口:“怎么,明远同志不在这儿?我来是找他有点事。”卢定安问:“要不要派人把他找来?”“不用,看这意思你们的会还没有完,那我就不打搅了。”杜锟跟大家点点头,在人们的簇拥下又走出了会议室。
卢定安重新坐回位子,沉了有好一阵子会议室里才安静下来,他宣布继续开会:“在简陋平房里住过的人,请举手。”他自己先带头把手举了起来,竟无人响应。他又重复:“不论时间长短,住过一天也算。”经过如此启发,稀稀拉拉,全场响应者也不过三五个人。红庙区年轻的副区长袁辉,今天穿得格外朴素,迟迟疑疑地把自己的手举起来。卢定安又问:“进过简陋平房的人,请举手。”举手的人略多了一些,都相互看看不明究竟……卢定安让人们把手放下后才开始了他的正题:“世界上的许多事,怕调换个位置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让我们这些人也住在那样的危陋平房里,我们会怎么看待现实社会,怎样考虑问题?对危房的改造着急不着急?现在不是提倡城市要有城市的素质、现代人要有现代素质吗?我看作为一个干部最基本的素质,就是有真心有热情为老百姓解困救急,办点实事,办点好事。现代城市的人口密度应该是一平方公里一万人,我们梨城却平均每平方公里两万人,简陋平房区则平均五万人,老城厢一点五五平方公里居住着十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七点八万人。市内的六个区我都跑过来了,把各区向我报告的数字加在一起,全市共有成片的危陋平房七百四十万平方米,里面住着六十万户,大约有一百八十万人。诸位,我们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了,这是我们政府欠下老百姓的一笔大债!市政府的年年问卷调查,反应最强烈的一直是房子问题。也许我们还能说出上百条不改造这些破平房的理由,但非改造不可的理由只有一条——老百姓太苦了,绝不能让这一百八十万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进入下一个世纪!市长办公会已经开过了,市政府下了决心,从今天起,用五到七年的时间改造完这些危陋平房。今天就请各区区长,当众讲一讲你们区的危陋平房的情况,并跟市政府签下责任书。”
各区的头头们交头接耳……红庙区的女区长钟佩问袁辉:“我们是一百三十五万平方米,这个数儿出入不大吧?”袁辉自作聪明:“这个数只少不多,应该再多报一点,我估计哪个区报得多,市里给的钱就多。”钟佩摇摇头,没有吭声。她面容温和端秀,在一片流行的官脸中显得格外的明慧恬淡,让人更容易想到贤淑的大嫂、坐冷板凳的女学究之类的人物……
杜华正当仁不让要打头一炮:“大家都知道河口区是梨城发展的摇篮,文化沃土积淀很深。梨城的第一所小学、第一所中学、第一所大学和第一条商业街,都诞生在河口区。只是到了清朝后期,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梨城,占了东部和南部,划分租界地,修建小洋楼,市中心开始向南移……惟河口区始终是地道的中国地,走土路,吃井水,住土房。附近几个省份的农民,遇有饥荒,就顺着几条河和官道来到梨城的河口一带,搭个棚子就安顿下来,慢慢就形成一片片的棚户区。所以我们区的危陋平房格外多,一共一百八十万平方米,三义里只是其中比较大的一片。市长到我们区调查的时候我已经表过态了,在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准备用六年时间改造完这些平房。”
袁辉有意说给钟佩听:“听听人家多有气魄!”钟佩没有理他,兀自开口了:“市长,我说吧?”卢定安:“好,红庙区。”钟佩气质沉静,说话低调:“我们是工业区,那些四十多年前的工人新村,早就成了旧村、破村了,实在是不能住人了。刚才市长说,这些旧平房是我们政府欠下老百姓的一笔债,一点不假,我们区欠下的是建设我们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债。刚解放的时候,咱们梨城的第一任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该恢复战争创伤了,可是还得拿出大批财力抗美援朝,国家经济面临着严重困难,只能给你们盖这些简易的平房当宿舍,先暂时住着吧,十年后推倒重盖,盖大楼!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十年以后,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又进入困难时期。到了第二个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是砸烂和毁坏的运动,不是建设的时期。一耗就又是十年,现在已经进入第五个十年了,这笔债该还了。我们区应该改造的房屋面积是一百三十五万平方米,我对所需的资金心里没有一点底,能在七年里完成就不错。”
这个低调的表态竟惹得区干部们为她鼓起掌来。不甘寂寞的副区长袁辉高声补问一句:“市长,没有人认为老平房不应该改造,您就说市里给多少钱吧?”
卢定安反问:“你们想从市里拿到多少钱?”会场上立即静了下来,一时没有人能听得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卢定安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市里有足够的资金,分给各区建委盖房子就是了,还把你们招呼来干什么?”
“啊?”会场上不约而同地发出一片惊讶之声,“这是什么意思?市里不给钱?”袁辉小声嘟囔:“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
卢定安提高声音:“但也不是把任务交给你们就不管了,人是活的,钱也是活的,能搞到资金的办法很多,下面就请克任副市长讲一讲关于怎样筹措资金的一些想法。”
尽管金克任提出了不少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但坐在下面的人已经无法集中精神听他讲了。一听说市里不给钱,各区、局的头头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的会,甚至是一个圈套,军令状无论如何不能签,便各想各的退路,于是就在下面交头接耳,小声议论:“有办法不等于有钱,上下嘴唇一碰办法就出来了,谁都能说出一大堆办法,可钱哪?那是下决心说大话都弄不来的,当今世界千难万难最难的就是搞钱,千好万好最好的就是有钱……”参加会的人对卢定安还不敢太放肆,对金克任可就随便多了,到落实具体责任的时候都耍滑头,往后捎,当第一个慷慨激昂地表态要支持危改的杜华正又被点到名字的时候,一下子变得缩头缩脑、油嘴滑舌了:“得了,金副市长,你就饶了我们吧,我得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再定,你算过没有,这几百万平方米的破房子拆了,光是把废土拉出去,没有千八百万都不行,要再想建起新房子谈何容易?有高人早就说过了,钱就是人的第六感觉,没有了它你就没法使唤其他的五个感觉。你金副市长的大名还不是先得有金子,然后才能克服困难胜任工作嘛。”大家哄堂一笑,不了了之。前面的讲课、务虚都很成功,到最后却未能落到实处,即使卢定安还想硬逼也逼不上去了,只有先散会。
卢定安一宣布散会,头头们呼啦一下都走了,生怕走慢了被市长拉住就不好办了。大会议室里很快就只剩下了卢定安和金克任两个人,卢定安怒从心起,脸孔铁青,额头阴云密布,双手用力抓着自己的大茶杯,身为一市之长,为危改做了那么多大量的调查研究,为这个会也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居然就推不下去,愣是被下面给顶住了!这样的市长还当个什么劲儿?表面上看是因为没有钱,实际上是他缺少应有的权威……他只顾呆坐着,回想今天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会却没有开好的原因。金克任见市长不走自己也不敢动弹,只有默默地陪着市长——金克任暗想,谁能想得到呢?堂堂梨城的正副市长竟对屈服于金钱魔力的部属无计可施,只剩下感叹和无奈。金钱是盛世的膜拜,这个会再典型不过地暴露了现代人跟金钱之间又渴望又恐慌的关系,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将要推行的危改工程都要置于金钱的风险之下了!
——这一对搭档并没有想到一块去,卢定安想的是人跟人的关系,金克任想的是人跟钱的关系。卢定安按着自己的思路开口了:“克任,看来我们得成立一个危陋平房改造办公室,选个能干的人上来,负责协调、推动各区的危改工程,必要的时候就先打开局面,给各区做个样板。”
金克任赶紧调整自己的脑筋以跟上市长的想法:“今天连我们都推不动,这得调个什么样的人上来才能打开局面?”“简业修怎么样?”金克任暗骂自己一声太笨了,他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如果说卢定安相当于过去的元帅,简业修就是他的急先锋,一有大仗、硬仗,就想起自己的哥们儿来了。他当然不会反对:“简业修这个人行,又懂行,脑瓜儿也好使。”“让他当危改办的副主任,干具体事,主任由你兼着。”
金克任身为常务副市长,当然不愿意再兼这种属于自己下面的职能部门的小头,却又不敢公开推辞:“还用我兼吗?让业修当主任也可以嘛。”
“不行,你得兼。”卢定安口气生硬,也不多说理由,好像就这么定了。
梨城市委书记来明远,已经六十岁出头了,看上去和跟在他身后的才四十多岁的副书记常以新差不了多少,标准的身材,合体的浅色西装,白面含笑,风神挥洒。常以新手里提着一大兜时令水果,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梨城著名的黄埔花园——这是一座充满神秘色彩、有着诸多传说的旧宅院,里面确有一个花园般的巨大庭院,红墙绿瓦,花木扶疏,充盈着曼妙春色。几十棵参天大树中掩映着一幢欧式小楼,幽静典雅,在早晨的霞光里如金装玉裹。杜锟穿一身考究的休闲服,正在一株杨树底下的台子上作画,看见来明远略感意外,放下画笔相迎……来明远来看老上级,神色谦恭,老远就拱手:“杜老,您好,没有打搅您的休息吧?”
杜锟也笑逐颜开:“我今生只剩下休息了,欢迎你们这样的稀客来打搅。”常以新把水果递给女佣,但没有忘记加上一句:“这是来书记给买的。”杜锟道谢。来明远走近台子看画,宣纸上一团大红大绿的牡丹。他顺嘴称赞:“杜老的牡丹名动梨城,听说收藏者们把价格抬得很高。”谈画显然是搔到杜锟的痒处,他哈哈大笑,连连摆手:“没有的事,纯属谬传。我这个人不喜欢运动,不过是借画画健身磨性子。”他声音沉厚有力,说得自己脸上放光。来明远适时地再搔一下:“您看上去的确显得年轻,充满活力。”这是老头子们最爱听的话,虽明知是恭维,当不得真,也高兴,又何必认真呢?只要觉得受用就行,杜锟得意:“这就叫手舞足蹈,七十不老。”来明远继续凑趣:“如果我厚着脸皮讨一幅您的牡丹,舍得吗?”杜锟脸色清朗,精神畅旺:“不胜荣幸,你显然也听我那个孙子说过,要想哄我高兴,就是见面要画,哪怕拿到门外再扔进垃圾桶呢!”“没有,没有,我可没有听到这样的笑话。”来明远对杜锟的诙谐机敏感到吃惊,庆幸自己来对了,这位梨城市的老一号人物仍未失去智慧、深度和凝聚力。他也变得轻松多了,“那天听说您去了市委,正赶上我不在,不知您有什么事情,今天特意来看一看,没有影响您作画吧?”杜锟收敛了笑容:“别客气,那天是路过,什么事情也没有,感谢你们来看我,到屋里坐吧。”来明远拦住:“这儿不是很好吗?又凉快,又干净。”花坛旁有一小圆桌,桌上放着茶壶茶杯,桌旁还有几把椅子,杜锟喊来用人沏上新茶,给来明远和常以新换上新杯子。杜锟问:“明远同志,你们二位肯定还有别的事情吧?”
真厉害!想瞒住杜头儿的眼是不容易的,来明远自愧不如,立刻严肃下来,甚至面有难色:“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前几天定安同志下了死命令,还让各区局的领导同志当场签署军令状式的责任书,要展开全市性的平房大拆迁。这如同一场大的运动,涉及到要拆除七百四十万平方米的旧平房,要重建两千七百万平方米的新住宅,在五到七年里先后将有一百八十万人口没有栖身之所……”
杜锟点点头:“我听说了。”来明远有些意外:“定安同志事先跟您商量过了?”杜锟脸上无波无浪:“没有,是来串门的人讲的。”来明远又叮问:“您支持这项计划?”杜锟非常富有特点的哈哈一笑,带着一种金属音:“我已经退下来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来明远也笑了:“杜老,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您可不要不爱听,您是人退责任退不了,我和定安同志都是您提拔起来的,我们有了难题还得找您,惹出麻烦也得请您出来给坐镇。您长期担任梨城市的党政领导工作,政绩有口皆碑,不论是市委、市政府的干部,还是梨城的老百姓,仍然把您当成最有权威的老领导。”杜锟严肃地摆手:“哎,不能这样说。”
来明远则语气诚挚:“自从我和定安同志主持梨城市委和市政府的工作以后,自信两个人配合得还不错,可他做这么大的决定,竟然不跟市委正式地打招呼,也不拿到常委会上讨论一下,那天就是在楼道里跟我简单地说几句,我当时也没有表态,可定安同志就真的干起来了,市委这边议论纷纷……”
杜锟恢复了顶尖人物的敏感和气势:“都议论些什么呢?”
来明远看看常以新:“以新同志,你跟杜老讲讲吧。”
常以新看着老头儿的脸色,说话气很冲,口气也比来明远激烈得多:“用来书记的话说,解放四十多年来,梨城的哪一届领导班子都比我们这一届资历深,水平高,有魄力,有号召力。以市长为例,在曾经当过梨城市长的人中,有才子型的,有德高望重的,有开国元勋式的人物,有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的,但谁也没有在平房问题上大动干戈。实在是动不起,七八百万平方米的旧房子,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大火药库,里面住着一百多万人,而且都是最底层的收入最少、怨气最多的一部分群众,你再把他们的房子拆了,这么多人怎么安置?各种矛盾借机大爆发,惹出了事端怎么向中央交代?”
杜锟若有所思,半天没有出声。他对来明远是没有戒心的,但关系并不是很亲近,原因就是无论是谁跟来明远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发展朋友关系,但也不会成为仇人,只能是工作关系,而且是那种枯燥的工作关系,没有甘苦与共的默契和创造的大快乐。这个人本事不大,但坏心眼儿也不多。论感情,杜锟似乎觉得跟卢定安更近些,卢定安这个人还有其朴实的一面,能让人抓得着,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实话说他对常以新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刚才这番话实在说得他心里舒服,禁不住点点头:“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中央派北京的市长来梨城当市委书记兼市长,他只想在任期内建三百万平方米的房子,他想这么大一个城市建三百万平方米的房子还会有问题吗?最后就真的没有建起来,计划中途流产,搞得灰头土脸,无功而返。”杜锟的话里留有很大余地,他的身份在这儿,不能偏听偏信或太过偏激。退一步说,他也不想搅和到现在领导班子间的矛盾中去,往后他光剩下求他们照顾自己了,得罪了谁都不好。
来明远暗暗透了一口气,接过话茬儿说:“自古土木不可擅动,何况眼下国家对泡沫经济格外警惕,不是大兴土木的时候。”杜锟问:“定安是怎么考虑的呢?”
来明远不知是格外敏感,还是天生好脾气,一提到卢定安语调立刻就变得温婉了:“不知道啊,他没有跟我详细谈过,摸不清他的真实想法,其实谈不谈倒也无所谓,我担心的是闹出大乱子,所以想来听听老领导的意见。现在知道了您的想法,心里就有底了,也只有您说句话定安同志才肯听。”
杜锟终于明白了来明远和常以新的来意,或者说就是常以新的来意。因为在他的印象里,以来明远的性格是不大会站出来对市长的工作提出异议的……他们想让他说服卢定安放弃危改工程,而卢定安是出了名的犟眼子,气死他爹都不戴孝帽子,又是已经公开讲出去的事情,能听他一句话就改变计划吗?杜锟犹豫了,开始说卢定安的好话:“定安是个老实稳重的人,也许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他的工作水平不是很高,但他踏踏实实不会出大格。怎么突然想起要捅这个马蜂窝呢?”
他在问来明远,回答他的却是常以新:“有人称他为‘平民市长’,这是一句好话。但不能变成‘平房市长’,更不能搞大跃进那一套,以为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啊!老书记再不出头,我怕定安同志将来收不了场。说到底我们还不都是为了他好?”
杜锟精明一世,看出来是在被人利用,可手里没有权了想不被利用也不行。他故作爽快地说:“你们正副书记交办的任务,我哪能推辞,可以先跟定安同志谈一谈,听听他的想法,你们最好也当面跟他交换一下意见,该批评的批评,该支持的支持,不要因此生出嫌隙。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两个党政一把手起了摩擦,受损失的可是工作。”
来明远忙不迭地点头,常以新随声附和:“好的,有您的支持我心里就有底了。”
看来他是决心要把杜锟套住。杜锟看着他们,身上有了一丝冷意,这位锋芒外露的市委副书记似已羽毛丰满,看来雄心不小,是个厉害角色,他不同意卢定安的危陋平房改造肯定只是个借口,那么他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呢?梨城要多事了……杜锟暗暗提醒自己,不管他们怎么斗也不关你的事了,千万不要蹚了浑水。得机会还要告诫儿孙,要有所防备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