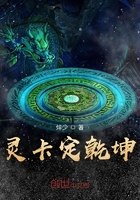曾有记者问过我,
为什么热爱文字编辑,终身不辍?
因为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环,
是弘法的资粮,
人不在,文字还在。
一个人因为一句话而受用,
这辈子,乃至下辈子,都会对佛教有好感。
透过文字媒介,
不只是这个时代,不只这个区域的人,
都可以接触到佛陀伟大的思想,
几千、几万年以后,
此星球、他星球的众生,
也可以从文字般若中体会实相般若的妙义。
我作为一个出家人,除了知道一些佛理以外,梵呗唱诵应该是不合格的,可是佛教里最需要的就是梵呗唱诵。一个出家人会得梵呗唱诵,到处都会受欢迎,有一句话说“会得香云盖,到处吃素菜”,就是这个意思。偏偏我五音不全,连“香云盖”都唱不下来。以这么样的条件,在佛教里,可以说应该是走不出去的。
好在我生性勤奋,欢喜舞文弄墨。在焦山念书的时候,我的作文甚至老师都还替我誊清,送到江苏省会镇江的报刊上发表。我原本也没有学过诗词歌赋,由于焦山位在长江中心,在那样的环境,偶尔晚餐后,在沙滩上散步,真有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感,每每引发我写一些小诗。寄到各报刊,篇篇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可见得,人生的道路很多,此路不通还有彼路,不要墨守成规,也不必自以为愚痴不会,所谓“愚者也有一得”,所以我自己培养文学的兴趣,兴趣也成长了我。
我想,既然喜欢写东西,就应该进一步学习编辑。因此,每个月规定自己编一本专属自己的刊物,叫做《我的园地》。跟一般刊物一样,有发刊词,有社论,有讲座,有专论,有随笔,有新诗,还有编后记,甚至小说,每个月再怎么样功课忙碌,必定把《我的园地》书写完成,如期出刊。其实这本刊物的读者,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离开焦山以后,第一个获得的工作就是宜兴白塔国民小学校长,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同学智勇学长也长于文字,两个人志同道合,编发一份《怒涛》月刊,这份刊物取名叫“怒涛”,意思就是要用怒吼的波涛,冲毁腐旧的恶习,还给佛教一个清净的本来面目。
当时在那个乡村地方,也找不到印刷厂印刷,就由智勇书写钢版,我做发行。这一本油印的杂志,每次发行五百份。原来以为这份油印的杂志,应该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再者,里面的文章立论激烈,可能会引起佛教界的反感,结果,第一期出刊之后,就得到素有佛教杂志权威的《海潮音》替我们刊登一个义务广告说:“我们又多了一支生力军!”这个鼓励,给我们很大的力量。
原本以为家师志开上人也会怪我兴风作浪,没想到,他不但没有怪我,还寄了五百令的纸赞助我们,这又给我们无比的鼓励。
这份《怒涛》前后编了二十多期,后来因为白塔国小这个地区是国共交火的地方,实在生存困难,不得已我又回到了南京。
一九四七年冬,承蒙江苏徐州《徐报》的王老董,要我替他主编副刊,定名为《霞光》;可惜,我只编了一期,就爆发了“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当然,这个短命的副刊也就夭折了。
因为徐蚌会战震动了南京,当时局势风声鹤唳,我在前途茫茫之下,就随着“僧侣救护队”,在只想逃命,也不问前途的情况下,就这样到了台湾。
我到了台湾后,知道在台中的学长有一份《觉群》旬刊。这是一份抗战胜利后,由太虚大师创办,在上海发行的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广,可以说,是一份走改革佛教的杂志,因为战争的缘故没有办法继续出刊,就由我在焦山读书时的学长、时任上海市佛教会秘书的大同法师负责,将这份杂志从上海带来台湾。
一九四九年初,大同法师因为“匪谍”嫌疑远走香港,遗留这份《觉群》还没有出刊,其他人也不知如何办理。因为我在大陆有编写的经验,他临走前交代他们,要我去负责主编。因为这是太虚大师要革新佛教的一份杂志,我当然很有兴趣为它服务,也愿意做出贡献;但是我只编了一集,出版后,就受到警察的调查。当然,我不能为了编辑杂志,就跟警察、安全人员挑战,同时也怕连累到中坜圆光寺居住的问题,我不敢再到台中。因此建议台中宝觉寺的住持林锦东法师(又叫宗心法师)另请高明。他就请到台中图书馆的总务主任朱斐前来主编,终于在夏秋之际,杂志复刊出版了。
没想到,在第一版上声明,今后《觉群》要更改为纪念印光大师,弘扬念佛法门,提倡净土学说。我在中坜圆光寺看到这样的启事,大为不满。我认为太虚大师、印光大师,都是大德,但是,这好比张家的祠堂,你不能随便把它改成李家的祠堂,我就写了一封信去质问他,你怎么把太虚大师创办的杂志,拿去纪念印光大师呢?这张冠李戴,怎么也说不过去。
原来,朱斐居士是跟随李炳南居士学佛,二人同是印光大师的弟子;他把我的原信刊出,并且说我不赞成净土法门。其实我一生,打的佛七约有百次以上,再加上早晚念佛、周六共修,那就更多了。我是倡导“禅净共修”的人,主张“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共修”。为了这一段文字编辑的因缘,招来我在佛教界一段很不好听的名声,说我反对念佛,增加了我在台湾弘法的困难。
后来,《觉群》改名叫《觉生》,发行了一年之后,再改名《菩提树》。这就是在台湾发行多年的《菩提树》杂志的来由。后来《菩提树》出刊,我经常投稿,我和朱斐居士也时相往来,成为很好的道友。
这个时候,因为我的文章不断在《觉群》、《觉生》、《菩提树》发表,居住在新北投的东初法师办了一份《人生》月刊,要我去为他主编。我原本就已经断不了的文字编辑因缘,又再继续下去了。
我断断续续编了六年的《人生》杂志,这六年中,我没有用过《人生》杂志的一张稿纸,也没有用过它一张邮票,也没有支过它一分钱的车马费,说起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为佛教的文化做义工了。
后来东初法师跟我讲,因为我的这一份杂志,让你们扬名立万了。又说,现在你也应该帮忙,我们把杂志从二十四页增加到二十八页,新增的四页,就由你出资好了。
我为了编辑的兴趣,很辛苦地筹募这四页增加的费用,甚至光在宜兰这一个地方,我就介绍了三百多个长期订户。这都是靠着信徒助印、捐献订阅支持才有的。
在编《人生》杂志期间,我学到很多,比方花莲大地震,东初法师要我去救灾,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如何救灾。还有,他写的文章经常在发表后,引发外界的一些争论,他都说那些文章是我写的,我也必须学习代他抵挡这些议论。
《人生》杂志在当时的佛教界,算是一份很有权威的杂志,因为有东初法师好评论佛教,有南亭法师专写佛教长篇文章,煮云法师、心悟法师都加进了我写作的阵容,我真是废寝忘食地要把这份杂志编好。
每个月,我必须从宜兰到台北两次,一次是送稿给印刷厂排版校对,过几天后,再上来做最后校对印行。记得那时候也没有经费坐汽油车,都是坐普通的运煤车,必须经过二十三个山洞,每一次宜兰台北一趟下来,鼻孔都塞满了煤灰,期间的辛苦,现在的人已经难以想象了。
后来我不能为《人生》杂志继续编下去的最大原因,主要是《觉世》旬刊在一九五七年,由台北健康书局张少齐、张若虚父子出刊。因为他们想要办一份弘扬佛教的刊物,以报纸型发行,预计每十天一期,要我担任总编辑。
他们本来要叫做“旬报”,但我知道,依政府的规定,每周出刊的,可以叫“周报”,但十天一期的还是名为刊物,所以我就建议他们叫“旬刊”,《觉世》旬刊就这样定名下来,并且在同年的四月一日创刊。
《觉世》旬刊是一份四开的报纸型刊物,我虽然没有编过这样的期刊,但觉得很有挑战性,特别是我一向有“做中学”的性格,于是就边做边学。总听人说“皇天不负苦心人”,确实,我只编了二三期,得到好友李春阳的指导后,自己就能上路了。
我本着公平原则,报道佛教各界的新闻、活动,我也秉持公正精神,撰写《云水楼拾语》,评论佛教的是非得失。当然,这份《觉世》蒙佛教各界的重视,发行得非常广泛。
编辑《觉世》旬刊的同时,听说《今日佛教》忽然宣布要停刊。我乍听之下,觉得非常可惜。实在说,《今日佛教》是一本很好看的美术画刊,由广慈、煮云等法师,以及李春阳发起。它的照片精彩,图文并茂,编辑得相当精彩,当然,画报画刊要比文字更容易得到读者的欢迎。尤其,它也刊登了大陆的锦绣河山、介绍大德高僧等内容,大家看得很欢喜。
经办不到一年,就宣布要停刊,必然是因为经济不够周转。这一停刊,就有人不甘愿,由台北善导寺住持演培,监院悟一、妙然等,组织了一个八人的社务委员会,由我担任执行编辑。于是我又披挂上阵,开始了文字的编写工作。
改编后的《今日佛教》,我就写了一篇《我们的宣言》,还获得李炳南居士来信给我赞美;接着我又写了《我们要有殉道的精神》,时值戒严时期,哪里能随意讲话,但是为了要弘扬佛法,我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豁出去了。
在我编辑《今日佛教》不到二年的时间,原发行人广慈法师又把它讨回去自己办,我就专心去办《觉世》旬刊了。
佛光山接手《觉世》旬刊之后,有朱桥(朱家骏)、陈剑慧、慈惠、慈怡、依晟等人都来帮忙编务,前后发行四十年,从来没有休刊过。尤其我创了一个纪录,旬刊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出刊,我必定在这之前,将旬刊送到读者家中,没有延误过一期。我自感安慰,这也显示了我准时的性格。
《觉世》旬刊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
一、帮忙智光商工创建筹款。假如今天大家翻阅一九六五年前后的《觉世》,就能注意到所刊登的功德芳名。
二、帮忙建设佛光山开山初期工程。
三、引发社会公论,维持正义。
例如,一九六四年,西班牙的斗牛要移到台北表演,表演最后要把牛杀死。我们觉得这太残忍了,基于慈悲的立场,提出反对斗牛的意见。那时候,“立法院”就凭着《觉世》的一篇评论,最后阻止了这一场血腥的表演。
又例如,政府曾反对台湾民间的信仰,要取缔五日一大拜、三日一小拜的情况。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这是民间社会问题。因为人民一年的辛苦,他借由大拜拜可以宴请亲朋好友,这也是他们相互联谊、娱乐的生活之一。如果剥夺他们拜拜的权利,只准许高官厚禄的人天天吃大餐、跳舞享乐,这也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喊出口号:不可以“取缔”拜拜,可以“改良”拜拜。所谓“改良”拜拜,就是用香花素果代替大鱼大肉,以素食的东西来祭拜,既不杀生又不造业,又能维护信仰。后来,这满天的风云,就因为这样的建议,社会就安定了。
这份助印的刊物,每期发行四十万份,遍及四十二个国家地区,扮演着海内外几百万佛教徒沟通的桥梁。直到二〇〇〇年,并入新创刊的《人间福报》,也就是现在《人间福报》的“副刊”与“觉世·宗教”了。
文字编辑工作是会让人上瘾的,而我更乐在其中。在宜兰弘法时,我除了帮忙当地的《国光》杂志、《宜兰青年》写稿之外,自己又编印了一份《莲友通讯》,每半个月一期。当时,委托一位家里开设中华印刷厂的青年吴天赐帮我印刷,后来因为这份通讯的关系,度了他跟随我出家,他就是后来佛光山的第二任住持心平和尚。
说来,我对带动台湾出版界的进步,应该有些许的贡献。例如,朱桥先生帮我编辑《觉世》和《今日佛教》的才华,为《幼狮》杂志所欣赏,就把他请去担任主编。当时我建议他标题做大一点,字不要排得密密麻麻,结果,一出版就引起震撼,当时很多杂志也随之跟着改头换面,为台湾杂志的编辑掀起大大的改革运动。
我初到台湾来的时候,有一份《今日青年》杂志,是仿当时《今日美国》杂志而创办的。当时,中兴大学教授秦江潮先生(后来担任台北市政府人事室的主任),因为我经常投稿,特地到中坜来看我,要我去做该杂志的编辑。
我跟他说:“我要做和尚。”他就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了这个时候,和尚也要爱国。”我回答他:“我连和尚都做不好了,其他的事还能做得好吗?”我仍然坚持做一个和尚。就好比古德有一首偈云:“昨日相约今日期,临行再三又思维。为僧只宜山中坐,国事宴中不相宜。”虽然拒绝了他,但我后来还是经常帮他撰文写稿。
那时候为什么那样喜欢写文章、欢喜编辑呢?又没有稿费可以拿。我完全是基于护教。例如:名伶顾正秋在永乐大戏院演京剧,内容有对佛教不利的地方,我就写了一封《致顾正秋小姐的公开信》,跟她抗议,也不管她的背景是任显群还是蒋经国。
曾有记者问过我,为什么热爱文字编辑,终身不辍?因为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环,是弘法的资粮,人不在,文字还在。一个人因为一句话而受用,这辈子,乃至下辈子,都会对佛教有好感。透过文字媒介,不只是这个时代,不只这个区域的人,都可以接触到佛陀伟大的思想,几千、几万年以后,此星球、他星球的众生,都可以从文字般若中体会实相般若的妙义。
好比,我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提倡“每月印经”,将艰涩难懂的经文,采新式标点符号,加以分行分段编辑,如普通小说体裁一般,使得佛法能普遍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后来,我继续创办《普门》杂志,以普遍化、生活化、艺文化、趣味化为宗旨,在发行二十余年后,二〇〇〇年时,就转型到马来西亚发行了。
曾经获得“优良图书金鼎奖”的《佛光大辞典》,于一九七八年起开始编撰,耗费了十年的时间才终于问世。在此之前,一九七七年我发起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以编撰现代佛教圣典为目标。春去秋来,佛光山编藏的工作已接近四十年,总共完成了《阿含藏》、《禅藏》、《般若藏》、《净土藏》、《法华藏》等,共一百九十八册。我想,等到十六部藏全部完成时,应该也有千册左右了。
如今,随着科技进步,《佛光大辞典》及《佛光大藏经》也都发展出电子版,以方便携带保存,并且易于查询检索、比对。
二〇〇〇年,佛光山启动了《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的编务工作,历时十余年,终于在二〇一三年出版。当年,我叫如常法师编辑这部图典时,问她需要多少钱,她说大概需要一千万。我就将《浩瀚星云》这本书所得的版税一千万元,悉数给她作为编务行政费用。可见我们并不是光口头叫人家做,自己也要先有所行动才行。
这一部二十巨册的美术图典出刊后,对建筑界、艺术界、教育界、工艺界,应该都会有相当的贡献;尤其在佛教的历史上,透过这许多艺术的呈现,让世人知道,佛教对全世界文化的影响,是抹煞不了的。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华文版出刊后,英文版也正在努力编写中,预计二〇一四年问世。感谢来自世界各地许多友人如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冰岛、丹麦等,尤其中国大陆给予我们的支持最多,都先在此说声谢谢了。
除了上述大部头书籍的编纂工作,为了鼓励佛学研究,早在一九七六年,我就创办了《佛光学报》,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创会之后,每年也出版一本论文集。接着自二〇〇一年起,由满果法师主编《普门学报》,每两个月一期,整整编了六年,每期我也参与其中,贡献自己一篇文章。
除了《普门学报》,我还邀约两岸的佛教学者共同将经律论中重要的著作,做系统的整理,翻译成白话文,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了一百三十二册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
这是因为在长久的弘法过程中,经常有人告诉我,他没有学佛的原因,是因为他看不懂佛经,假如有一本白话文的经典,那他学佛就不难了。为此,我就一直有心想要替佛教编辑一部白话经典。
可是,佛学的翻译是非常困难的,无论翻译成英文,或是翻译成日文、韩文、西文、法文、德文等,不管翻译哪一国文字,都相当不容易,甚至连文言文的佛经要翻成白话文,也是一样不简单。
例如,每一部佛经的开头都有一句“如是我闻”,光是这一句话,要把它译成白话文,就让我煞费周章,思考怎么样把它说得让人懂而又不失原意。后来我发觉到,只有译成“《金刚经》是我阿难听佛这样说的”,或者是“《法华经》是我阿难亲自听佛这样说的”,才比较符合原来的意思,这确实是花了我许多的时间思索,才敢这么断然决定。
因为要让人懂得经典的内容,只有像鸠摩罗什大师那样的意译,才比较容易让人明白。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师中,尤其以玄奘大师和鸠摩罗什大师最为特出。他们一位是直译,一位是意译。罗什大师的意译经典,如《阿弥陀经》、《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等,因为文字畅通,读诵容易,普遍较为大众所接受,流传也比较广泛。而玄奘大师虽然也翻译过《金刚经》等,但都不流传了,为什么?意思虽然到口,但诵读起来困难,也就少为大家所熟知了。
因此,我曾经请依空法师、吉广舆夫妇把我的意思带到大陆去,邀请学界帮忙翻译佛经;我也请慈惠法师到北京和许多学界人士多次沟通,而有现在我们看到由海峡两岸一百二十位作者所翻译的《白话经典宝藏》。
以白话文来阐述经典,是一个尝试性的突破,可是这个工作由于人才的不足,成果并未能尽如人意。尽管如此,当初能有这样白话版本的发行,确实相当困难,也可以说为佛典的翻译史写下新页了。
《白话经典宝藏》编辑之后,我知道大陆许多的硕、博士生都以佛学作为他们的研究方向。我从中选录了四百多篇的论文,集成《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全套十辑,精装一百二十册,分为思想史、历史、制度、语言、文学、考古、建筑、艺术等六大类,总共加起来也有数千万言。
感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程恭让教授的协助,永明、永进、满耕等法师的参与,可以说花了很多的力气才得以编辑完成,印刷出版。
当然有的文章难尽人意,有的文义也不容易明白,甚至我也知道,这些硕、博士论文里,有的人不一定从信仰入门,甚至有些从批评的角度撰写,曲解佛教的也有,但我都将他们的原文搜罗出版,为什么?因为我要让后代的人知道,这个时代的文化产物就是如此,我们必须把它留给后人去研究,不能让这个时代的历史就这样消失。这就是我编辑《法藏文库》出版的缘由了。
由于我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受过什么文化的训练,但是我对佛教的教育、文化,可以说如痴如醉。例如,当初创办《人间福报》的时候,多少人劝我,现在平面媒体走下坡了,不要办了。以前我们因为贫穷,没有办法自己办报,只有在各报买版面,由我们编辑内容提供给他们印行。现在我们有力量了,我们必须为佛教发声,为佛教留下一个历史。就这样,我亲自带着几个徒弟,从策划、邀稿到版样设计,全心全力投入。《人间福报》终于在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创刊,由依空、心定法师先后担任发行人。
有人问我,为什么选在愚人节这一天创办这份报纸?我想,因为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人间福报》首任社长是依空法师,记得我还跟她说,我筹了一亿元给你办报,你能办到三年,倒闭了我也不怪你。
欣慰的是,《人间福报》至今已经十三年了。可以说,种种苦难、挫折都有,但我不计较,因为这些苦难、挫折滋养了我们的慧命。如今回想起来,我要谢谢那些当年好意相劝的人,他们给了我危机意识,也给了我永不退缩的坚持。
历任的社长从依空之后,陆续有永芸、柴松林教授、妙开等人担当起社务工作,现在则由符芝瑛小姐担任社长。
符芝瑛小姐是政治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曾在《联合报》做过记者,在天下远见文化公司担任编辑时,替我写过传记《传灯》,还登上年度的排行榜,之后又陆续写了《薪火》、《云水日月》等。二〇一〇年底,她从上海回到台北,推动《人间福报》各项编务,充实版面内容。尤其,她广邀学者、专家为“百年笔阵”专栏撰文,替福报增色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陆续有全球各地的华报,如:新西兰、新加坡、菲律宾,以及芝加哥、纽约、圣路易和澳门等,都表示福报的内容充实、清新,是一份很好的华文教材,希望我们能提供内容给他们的报纸刊登。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了。
除了《人间福报》,前后我又创办了佛光出版社、佛光文化、香海文化公司、人间通讯社以及上海大觉文化公司等,陆续有永均、蔡孟桦、妙蕴、妙开、满观、妙有、妙普、黄美华等人负责执行编务、发行等工作。其中,蔡孟桦对我的书籍出版用力甚多,像《迷悟之间》、《人间万事》、《星云法语》、《人间佛教丛书》等,还曾经获得印刷界的“金印奖”。而这几年,上海大觉文化公司在大陆为我出版简体字版相关书籍,承蒙大陆读者的厚爱,竟然也让我挤进所谓的“版税富豪排行榜”了。
因为出版与编辑,我也替佛门培养了许多人才。例如六十年前,慈庄、慈惠等人就是喜欢写文章,欢喜我替他们改文章而进入佛门,后来又在台北三重文化服务处工作,我们写下了许多佛教文化的辉煌纪录。例如印行的《中英对照佛学丛书》之《经典之部》、《教理之部》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出版品。尤其,慈庄法师负责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对早期佛教文物、出版的流通推广,贡献很大。
而佛光山派下第一代弟子,像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心定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著作出版。之后,在报纸、杂志、出版以及编藏等方面,像依空、依晟、永明、永进、永本、永芸、永庄、满义、满果、满光、满济、满纪,以及《人间福报》的妙熙、觉涵等所有的出家弟子等,都有一些杰出的表现。
现在,佛光山年轻一代的弟子,不仅能写,还能画、能摄影、能使用电脑编辑。为了鼓励他们编写,我无论工作多忙,都会替弟子的书写序,甚至在书名、标题、编辑等方面提供建议。
由于担任杂志编辑又喜欢写作,我也结交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例如:柏杨、刘枋、司马中原、高阳等,和武侠小说作家卧龙生、梁羽生,文坛夫妻档何凡、林海音也曾多有往来。
我从一个二十岁不到、为佛教改革与前途振臂疾呼的僧青年,到台湾驻锡弘讲、建寺安僧,靠着一枝秃笔生存立足,乃至后来创办佛教的文教事业,将佛陀教法透过文字与出版品流传到世界各个角落。我这一生也由于文字编辑的因缘,扩大了视野,广交文化界能人异士,可谓无限欢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