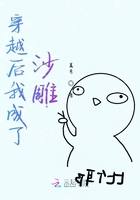“阿七,怎么能对自己的夫君这么无礼?”
南宫琰不是一个人过来的,他的身后,还站着南诏皇后。此刻,正板着一张脸看着虞七七。
她前一刻还蕴满警惕的脸霎时没了,欢声笑语地朝自己的母后走去,“阿娘,你怎么和殿下一道过来了?”
“太子殿下是我命人传唤过来的,都到了用晚膳的时辰了,你怎的还在睡觉?”平日里南诏皇后待她倒是不严苛,可现在有南宫琰在,她必须要拿出身为皇后该有的威严。
“今日女儿陪母后出去走后回来,便觉得困乏得很,这才不小心睡着了。”虞七七抿了抿唇,不敢正眼看向她。
她皱了皱眉头,“怀里还抱着一头牲畜,生何体统?!”
闻言,虞七七赶紧将阿黄放下来,让它自己乖乖地进了笼子。
尔后,南诏皇后的脸色才稍稍舒缓开,她侧过脸朝南宫琰说道:“太子殿下,让你见笑了。”
“他又不是第一次见我这样...”虞七七嘴里嘟囔着,但不敢说得太大声。
南诏皇后听到,回过脸狠狠瞪了她一眼,她立刻闭嘴了。
南宫琰笑了笑,“七七与我待在东宫里都这么久了,这些我早已司空见惯。”话里透着释然,仿若跟她很熟了似的。
“是吗?...”这回,轮到南诏皇后的脸有些挂不住了。
没过多久,晚膳盛上来了,南诏皇后和南宫琰吃得还好,就是虞七七坐不住,她三两下就用好了。
南诏皇后瞧出了她的为难,也没多说什么。
一同用完晚膳,她还没和南宫琰说上几句话,虞七七便寻着个理由将他赶走了。
说是他今日在皇宫里绕了一圈也累了,该早些回去歇歇,若是她不放人,那便成了她的不是了,只好赔着笑脸让南宫琰先回去。
“你这是怎么回事?白日在外面不是还好好的吗?”等他走后,南诏皇后开口问她。
虞七七挽过她的手,将她扶到软卧边上坐下,“阿娘,您就别操心女儿的事了,我与殿下好着呢,只是我今日实在困乏,便先将他打发走了,不然平日里他可要吵着黏着我呢!”
她在东宫里的辛酸,怎可能会同她的阿娘讲,所以只能自诩自己与南宫琰的感情很好,这样才能让她安心。
南诏皇后怜爱地看着她,目光里有温和在涌动着,过了好一会她才开口,“阿七,你若是在东宫里受了苦,大可以在阿娘面前说,躺在阿娘怀里哭,可若是你什么都不说,阿娘才是真的难过。”
旁的话她不想听,她只想听她说实话。
虞七七一怔,猛然间,眼睫染成一片湿意,这细微的神情躲不过南诏皇后的眼睛,“你本就不是个爱哭的孩子,若是实在难受,也可以哭出来的。”她抬手,温和的掌心抚过她的眼角。
“阿娘...”
一瞬间,虞七七扑到她怀里。
南诏皇后眉眼松动,伸手覆上她的后背,轻轻顺着,“阿娘就知道,那燕京的东宫不是那么好过的。”
她虽嫁过去了一年多,可南宫琰看着,与她也没有多亲密。
“其实殿下他,他并不喜欢女儿,他会娶女儿,不过是因为被他父皇逼着罢了。”她支支吾吾着,说出这番话来。
“别怕,虽然我们是战降过,可你还有我与你父皇给你撑腰,还有你的几个哥哥们。”
南诏皇后一下一下的,宽慰她。
“阿七知道,阿爹阿娘和哥哥们都很关心我。”虞七七在南诏皇后怀里躺着,你,泪光闪烁。
“嗯,只是你嫁给了他,也要把自己的性子收敛起来,不能一味地与他针锋相对,男子最不喜的,便是自己的妻子与自己硬着来,该撒娇的时候还是得撒娇,你可是要在东宫里过一辈子的。”
她将自己多年来为人妻的经验传授给她。
“可是,卿哥哥说了,他会想法子把我从东宫里带走的,我不会一辈子都待在里面。”
虞七七抬起头,眸光里仍旧带着期许,晏世卿总能给她心安的感觉,所以她信她的话。
“好孩子,阿娘知道世卿那孩子喜欢你,可你终究是太子殿下的人了,就算是他再有能耐,也斗不过太子殿下。”
到底她的眼光毒辣些,虽然只仅仅和南宫琰见了两面,可南诏皇后看得出来,南宫琰是个城府极深的人,璇玉贵妃当年的手段,她也略有耳闻。
是以,璇玉贵妃的儿子,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相反,现如今南诏成了战降国,西楚又一家独大,若是将来燕京与西楚相斗,那依燕京的实力,虞七七待在燕京的能安然生存的机会更大。
可若是跟着晏世卿回来,那就不一定了。
“阿娘为何对他有这番赞赏之意?”虞七七不解,南宫琰在她眼里,也就那样,还经常对她冷冰冰的,她才喜欢他。
“可就怕他将来...”南诏皇后嗫嚅着,到底是没把话全说出来,她低下头,摸着她的后脑勺,笑着,“没什么。”
虞七七眨了眨眼睛,又重新躺回她怀里。
在南宫琰陪着虞七七回南诏的这段时日,晏世卿和蔺朝赋加快了步伐,赶在南宫琰回来之时,让蔺老侯爷上朝参他一本。
此番他不在燕京城中,是最好的时机。
朝中许多人都知道蔺老侯爷回来了,他带过的学子也曾私下去探望过他,他在朝中的威望又渐渐树立了起来,有很多人都想不通他为何会突然回燕京城,不过一想到当年的事,便又渐渐明了。
当初他告老还乡时曾说过,只要南宫琰在这太子之位上坐一日,他就绝不踏入燕京城一步。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人虽少,可时日久了,传的人也就多了。此次回来,八成是跟南宫琰有关。
这一日,燕景帝与大臣们正在上早朝,蔺朝赋忽然从臣列中站出来,开口说道:“回禀皇上,微臣有事相奏。”
燕景帝正看着手里的折子,听到他的声音,这才抬起头来,目光落到他身上,口里缓缓吐出一个字,“说。”
从来不理朝政之事的蔺小侯爷竟然有事相奏,真是稀奇。不过,他的眸光倒是慢慢冷了下去。
“微臣的祖父近日回燕京城,是为了替当年的一位故人伸冤。”蔺朝赋低着头,面色不慌不乱。
燕景帝的眸光一滞,还是沉声问道:“哪位故人?”
蔺朝赋敛了敛眸,“薛景成薛老丞相。”
“放肆!当年他勾结外臣,蓄意谋反已成定局,何来的冤屈所言?!”燕景帝拍了一下龙桌,蔺朝赋说出口的这个名字惹恼了他。
立时,蔺朝赋跪到地上,“其中的内情,只有微臣的祖父才知道!恳求皇上让我祖父进来觐见!”
按理说,蔺老侯爷已告老还乡,是不宜出现在朝堂之上的。
“薛景成一案,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定了,叫蔺老侯爷来也没用!”燕景帝两颊上的肉微微颤着,整个人的脸色一片阴阴沉沉。
曾私下去见过蔺老侯爷的大臣,见到二人僵持不下来,立刻也跪到蔺朝赋身后,替他求情,“皇上,蔺老侯爷一生都在为燕京朝局出力,可谓是恪尽职守,当年太子殿下一登上太子之位,他便匆匆告老还乡,这其中想必是有内情啊!”
“是啊,皇上,微臣恳求皇上让蔺老侯爷上朝觐见!”
“微臣恳求皇上让蔺老侯爷上朝觐见!”
...
又有好几位大臣跪到了蔺朝赋的身后,一一附议。
“你们...你们这是要逼朕?”燕景帝看得出来,他们都是曾被蔺老侯爷当初带出来的臣子,他们想要找南宫琰的麻烦他不反对,可他反对的是将薛景成当年的祸事挖出来。
“祖父曾扬言,若是太子殿下在位一日,他就绝不踏进燕京城一步,如今他为了薛老丞相的事回来,可谓是重情重义,还望皇上能看在祖父这么用情的份上,让他将当年的内情说出来!”
蔺朝赋不肯让步,跪在地上,头埋得低,但是说出口的话却掷地有声。
朝下,已经跪了将近一半的臣子,他就应该在得知蔺老侯爷回燕京城时,就将他叫到宫里来,如今这种局面,他们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了。
朝堂上沉默了半晌,他抬起眼眸,瞪向蔺朝赋,语气愠愠地说了一句,“宣蔺老侯爷!”
“是。”一旁的内侍,匆匆跑了下去。
一阵传召声之后,蔺老侯爷穿着一身黑色直裾朝服,头戴官帽从殿外从容自若地走了进来,“老臣,参见皇上!”他一走到朝堂上,便朝燕景帝跪下行礼,这番举动,庄重威严,想必今日是要使大招了。
“老侯爷请起。”
燕景帝对他说话的语气,还是带着一丝丝尊崇的,他毕竟,是两朝元老,从前朝下来的老臣,在朝堂上的面子他还是要给的。
蔺老侯爷朝他颔首,从地上缓缓站起来,“老臣今日前来,是为了申诉薛丞相的冤屈。”薛景成曾经是他的幕僚,俩人一起共事多年,是他在朝中的好友,他为了他申诉,倒也说得过去。
“朕不知道,薛景成的案子都已经尘埃落定这么多年,蔺老侯爷手里有何证据,这么坚持要为他翻案?”
燕景帝沉着一张脸,但是嘴角边上却挂着笑意,倒让人看不出究竟是喜还是怒。
“回皇上,当年老臣匆匆辞官,执意要告老还乡,实际上是为了躲避追杀。”蔺老侯爷头微微扬着,神色从容不迫。
此言一出,朝上的臣子们皆一片哗然。
燕景帝也皱了皱眉头,“此话怎讲?”
“当年薛丞相被指谋反一案,实则是被人陷害了,在皇上下令诛薛丞相一家时,他派人到侯爷府上找了老臣,交给老臣一样东西,上面的字是他用自己身上的血,一字一句写下来的。”
蔺老侯爷从袖口里拿出一张陈旧的布条,呈给内侍,他继续说道:“后来,有人追杀到侯爷府,将前来告密的人杀了,还蓄意要杀老臣灭口,若不是府上侍卫来得快,只怕老臣的这条命早就没了。”
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畏惧,更多的是愤怒。薛景成与他一样,当年都反对南宫琰登上太子之位,他被人陷害,他心中自然恼怒。
闻言,燕景帝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当年他辞官时,他只以为是他真的觉得自己年迈,所以才请辞,如今看来,其中的内情,倒是有些瘆人。
他目光阴沉,开口问,“刺客是何人派去的?”此时,内侍已经将血书呈到他面前,他翻开血书,低头看去。
待他看到一半后,蔺老侯爷才缓缓开口,“老臣怎么也想不到,派去追杀的人竟是太子殿下派去的。”
这下,朝堂之上的哗然声更大,有几个臣子已经被吓得面容失色。
另一边,拥护南宫琰的臣子们已经站不住了,立刻站出来指责蔺老侯爷,“老侯爷一回来,就来到朝堂之上构陷太子殿下,是何居心?!”
“各位大人,老臣不过是揭穿了太子殿下的真面目而已,免得日后你们拥立错了君主。”
蔺老侯爷转过身子,笑得瘆人。
“当年你就反对太子殿下登上太子之位,如今太子殿下不在燕京城,你就趁此机会来搅乱朝堂,其心可诛!”
这一点,朝上的臣子都看在眼里。
“就是,老侯爷是何居心?!”
“是何居心?!”
...
朝堂上,又是一片吵闹。
在双方争吵之时,燕景帝已经将蔺老侯爷呈上来的血书看完了,上面的内容,是薛景成向他申诉的言语,一字一句说得皆为动人,他看了都不免心中一阵炽热,他到底是为了朝堂出力了多年。
一件祸事,就将丞相府全都化为了乌有。
“住口!”
看完后,他再次用力拍了一下龙桌,下面的吵闹才噤声,全都低下头规规矩矩地站着。
“朕问你,除了薛景成的这封血书,你还有何证据能证明他说的都是真的?”燕景帝握着血书的手很紧,手指头还在微微颤抖。
上面的证供,全都指向南宫琰。
“有。”
蔺老丞相掷地有声,手里拿着一个荷包,里面装着燕景帝想要的东西。
燕景帝的眸光震了震,下面的臣子们全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亲手将荷包交给燕景帝的内侍,特别是拥护南宫琰的那帮臣子,大气都不敢出,此时此刻,南宫琰的地位很危险。
内侍呈到燕景帝面前时,他要伸出手的手滞了一下,最终,还是猛地将荷包拿了过来,将里面的东西倒到龙桌上,传出一阵“咚”地闷响,他凝紧眸光一看,是他在南宫琰七岁那年,送给他的玉扳指!上面的雕龙花纹,他记得最为清楚!
他虽不满璇玉贵妃为了他争权夺势,可那也是他的儿子,他小时候也宠爱过,而身为长子,他送他的东西自然要尊贵些,这个玉扳指,他在璇玉去世的那一年,就从未见他戴过!
而那一年,薛景成一家也因谋反一罪落得个满门抄斩!
“这是薛丞相让告密的人交到老臣手上的,这么多年以来,老臣一直随身带着!”
蔺老侯爷义正言辞,脸上一片厉色。
燕景帝将玉扳指紧紧握在手里,脸色凝重,嘴里不发一言。
他继续说道:“皇上,当年璇玉贵妃一家入狱,本就是她咎由自取,太子殿下却因个人仇恨,将这样大的罪名扣到薛丞相头上,就是为了替璇玉贵妃一家报仇,其罪行累累,如何配得上太子之位?!”
他言外之意,就是要让他废黜太子!
当即,拥护南宫琰的那帮臣子,全都吓得面如土色。若是失去了南宫琰这个靠山,他们的官位可就不保了。
过了许久,燕景帝才缓缓开口,“如今太子不在燕京中,此事,朕会慎重考量。”
薛景成的案子,是他当年一手拍定的,现如今蔺老侯爷要翻案,他将这案子翻了就是在打他的脸。
“皇上!此事证据确凿,不能因为太子殿下不在京中,就将这件事搁置,可以遣人去将殿下押回来,与老臣亲自对质!”
蔺老侯爷义愤填膺,燕景帝话里的意思他知道,就是想这件事先缓一缓,等有了转机他再拿出来说,到那时候,恐怕黄花菜都要凉了。
“太子此去南诏,是朕亲自指派他护着太子妃回去看病重的母后的,难道他这份孝心,老侯爷也不让尽了吗?”很明显,燕景帝拒了他的请求。
“皇上...”
一时间,蔺老侯爷也不敢再如方才那般挺着腰杆说话。
“不过是要等上几日的功夫,殿下了回来再处理,老侯爷不会连这几日都等不了吧?”
见事情有了转机,拥护南宫琰的臣子立刻开口揶揄他。
“你们!...”蔺老侯爷怒目看向他们。
蔺朝赋悄悄扯了一下他的袖子,眼神示意他不要再争执下去,燕景帝的脸色已经极度不耐烦,他给他的面子,已经够大的了。
蔺老侯爷怔愣一下,只好低下头,“老臣听皇上的。”
这件事,才算是暂时落下了帷幕。
一下了朝堂,就有人给南宫琰暗中递了风声。
得知蔺老侯爷从朝堂下来后不久,晏世卿悄悄来到了侯爷府中,朝堂上是什么情况,他还不得而知。
到了那,只见到蔺朝赋,蔺老侯爷一回来,便躺到了床上,他年岁已高,又在朝堂上争斗了大半日,这身子骨早就有些承受不住了。
一见到晏世卿,蔺朝赋便摇了摇头,口中缓缓吐出两个字,“没成。”
晏世卿的眸光立刻暗了下去,思衬了片刻,他才开口说道:“看来燕景帝对他这个儿子,还是维护的。”
不然,构陷当朝丞相谋反一罪,足以将他拉下太子的位子。
蔺朝赋却再次摇了摇头,“你还不够了解他,我们这位皇上最爱的,是自己的面子。”
“你是说,他不愿翻出当年的案子,就是怕打自己的脸?”晏世卿敛紧眸光,脸上布着震惊。
蔺朝赋点点头。
“祖父睡下了。”
这时,蔺朝歌从屋内走出来,碰上在长廊上说话的俩人。
“没能亲自看一眼蔺老侯爷,实在抱歉。”晏世卿朝他们二人颔首。
蔺朝歌的眸光沉了沉,面带担忧看着他们,“哥哥,你能不能告诉歌儿,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为何祖父上了一次朝堂,回来就这般疲累?”她担心蔺老侯爷,将一直没问的话问了出来。
蔺朝赋的脸色滞了滞,只笑着宽慰她,“没事,祖父此次回来,是为了替一位故人伸冤,皇上不愿翻出当年的案子,这才训了祖父两声。”
“既是为了故人伸冤,为何晏世子也在这?”她抿着唇,小声问道。
晏世卿面露难色,目光中带着为难,“我仰慕蔺老侯爷的名声,所以这几日来的次数频繁了些,若是惊扰到了蔺小姐,那日后我便少来一些。”
蔺朝歌立刻否认,“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们好像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歌儿,是你多想了,从小到大,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蔺朝赋将她往自己身前一揽,将她带下去了。
尔后,他回头朝晏世卿打了个眼神,晏世卿匆忙转身离开。
三日后,南宫琰收到了朝中臣子带来的口信,他们让他先不要急着回燕京,在南诏再待上一段时日。
说蔺老侯爷回来了,在朝堂上参了他一笔,翻的是当年薛景成的谋反的旧案,无论是薛景成亲手写下的血书,还是蔺老侯爷手中交上的玉扳指,种种证据都指向他,蔺老侯爷是想借着薛景成一案,让燕景帝废黜太子。
“该死!”
南宫琰握紧双拳,嘴里又恨恨说出这两个字来。传口信的侍卫被他的怒色吓到,急忙退了下去。
楚裴钰看着他退下去的身影,尔后,收回眸光看向他,“殿下,看来蔺老侯爷一直以来,就没打算放过您。而且,还是趁着您不在燕京城的时候动手。”
“我说当年我的玉扳指怎么不翼而飞了呢,原来他还留着这一手。”南宫琰冷笑一声,眸光一片阴冷。
“那我们要不要赶回去?”楚裴钰的心里,生出几分担忧。
他立刻开口制止,“不,本殿下倒要看看,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嗯。”
楚裴钰稍稍点头。
外面,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还有阿笺嘟嘟囔囔的声音。
“殿下可在里面?”虞七七在门外问楚裴钰。
“殿下在里面。”他轻声回了一声。
“这是我母后叫我拿来给你的。”
下一刻,虞七七已经到了他的寝殿里,递上一盘石榴,颗粒饱满,一颗颗全都是她剥的。
彼时已经七月,她那个石榴园种下的石榴树上面,开满了果子。
她记得,他不喜欢是甜的东西,但既然是她的母后说让她缓和一下和南宫琰的关系,她便想出了这么一个法子。
“我不喜欢吃甜的东西。”果真如她想的那般,他下一刻便说出了这句话。
但是,南宫琰突然看向她的手,幽幽问,“这是你剥的?”她的手指头上面,还残留着一丝渍迹。
虞七七点头,“是我剥的。”
“那留下吧,我可不能辜负了太子妃的一片心意。”他立刻改口,态度转变得十分地快。
一时间,虞七七的脸色也变了,她攥了攥手,紧而又松开,笑着说道:“那殿下可要全吃完,万不可浪费了。”
“好。”
他微笑应承。
一出了他的寝殿,不止虞七七,阿笺也欲哭无泪,但她还是撑着脸皮说,“公主,奴婢再去给您摘。”
为了给南宫琰摘,她已经爬了一早上的树了,虞七七还忽悠她,南宫琰不会吃的,到时候她们两个就分了去,谁承想,一切都不如她预想的那般。
“好阿笺,这都是母后的意思,你要怪,就怪母后去吧。”虞七七赔着笑脸,树上的石榴特别难摘,宫里的小太监们都不愿爬上石榴树去摘,唯有阿笺能供她使唤。
阿笺的脸色立刻变了,“奴婢哪敢怪皇后娘娘。”
“那不就是了。”
虞七七笑着,拉着她往石榴园去。
一连好几日,燕京的朝堂上都吵闹得要命,全都是为了薛景成谋反的旧案争辩的,一方站在蔺老侯爷那边,一方站在南宫琰那边。
燕景帝的头,快要被他们吵炸了。
正当他在御书房里愁眉不展时,仪嫔从外面走进来了,手里还端着一碗羹汤,说是要给燕景帝补身子的。
“咣当!”
他一挥手,仪嫔手里的羹汤摔到地上,溅了一地。
“皇上这是做什么?难道还怕臣妾毒害了你不成?”仪嫔目光凉薄,阴阳怪气地问他。
“你是来看朕笑话的吧?”猛然间,燕景帝抬起头来,目光阴毒地看向她,让她觉得心口一阵发凉。
“那还不至于,等薛景成的案子真的翻了,到时候臣妾才是真的来看您的笑话。”
仪嫔掩唇,笑得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