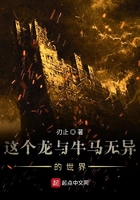“轰隆”!
巨大的爆炸在某处阴影内响起,接着一个全身冒火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半空,随即重重跌落在地。一只焦黑的手颤抖着从腰间取下一枚坠饰,然后迅速握紧,将那价值不菲的蓝色水晶狠狠捏碎。
片刻后,大量白色光芒凭空出现,在他的身边来回飞舞,不断没入他受伤的部位。很快,伤势与疼痛一起消失在某种吟唱之中,力量重新灌入他的身体,刺客不由自主地长出一口气,接着借助长刀的力量缓缓站起身,惊疑未定的目光来回扫视着身边的阴影。
就差半秒钟……就差那么半秒钟,他就险些永远跌入暗影,再也无法归来。
“呼……呼……”
也许是死里逃生带来的巨大心情落差,本就到达极限的刺客腿一软,竟然直挺挺地栽倒在地,勉强依靠手里的长刀才支撑住了摇摇欲坠的身体。
他的视线仍旧锁定在阴影上,然而,平时能够给他遮蔽,为他掩护的大片阴影,此时却如同塔尔塔斯深渊张开的血盆大口,令这位游荡者避之不及。
作为刀尖舔血的佣兵,刺客本人长年游走在生与死的边缘,因此对于“死亡”这种事情并不是过分畏惧。
但是有一件事,唯有这件事,是远远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的。这不仅仅是他的噩梦,更是所有与阴影打交道的生命的梦魇。
那就是“消失于阴影之中”。
说来很可笑,以潜入阴影为生的游荡者、刺客还有其他衍生职业,最警惕的反而是保护他们的阴影本身。
这种恐惧的源头已经不可考证,唯一的凭证就只有师徒之间代代相传的告诫:
“不要在阴影里迷路。”
看似很可笑的话语,却没有一个游荡者敢无视它。那些嘲讽老一辈们的愚蠢之徒早已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不再出现在世人面前。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陷入最悲惨的境地,每个游荡者宁肯暴露自己的行踪,也一定要在自己身上留下一条“丝线”。这当然不是真实的丝线,而是一系列只有他们本人才知道的标记,凭着这些标记,即使他们再怎么被不知名的存在遮蔽双眼混淆感知,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找到回归光明的道路。哪怕,在那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死亡,是酷刑,是前所未见的巨大灾难,也永远比在阴影里迷路要好得多。
至于刺客本人?他虽然相信这个传说的存在,但从不认为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会找上自己,也不认为他会在阴影的世界,自己的后花园永久失踪。久而久之,他已经忘却了老师的教诲,将阴影视为自己生存的必要手段,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
也正因如此,当他感受到那只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的冰冷与沉重,当他嗅到那不知死亡了多少岁月的腐臭呼吸,当他听到那不知名的失落语言的召唤的时候——
他退缩了,畏惧了,毫不犹豫地逃跑了。但是这无济于事,因为阴影中的那家伙——那些家伙,已经锁定了他,想要把他拖进只有迷失在阴影中的人才能知道的彼岸。
“塔尔塔斯在下……”刺客轻轻抚摸自己手中的银色匕首,这把拥有神奇力量的武器是他生存与暗杀的保障。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自己不在战斗状态,它就能带着自己跃迁到一定距离内的某一地点。而另一把匕首则能在任何时候感受到所有可能的危险,并在危及自己生命的时候用不同的颜色和响声主动示警,让他逃离危险。
然而,刺客记得,直到他感受到危险并将这把匕首拔出来观看的时候,它都没有一点动静。当然,也可能是匕首已经在积极地报警,然而自己却因为什么东西被扭曲了感知,从而没能第一时间察觉到怀里的异样。
“那种东西……那种在阴影中漂浮的东西,它们可以干扰我的感知,它们可以组成杀戮的军队……”刺客终于站起了身,“如果、如果连游荡者都没办法躲避敌人的偷袭,那又有谁能阻止它们的扩张?”
答案是没有人。
人们可以防备一时,但永远不能防备一世。只要人们有一刹那的破绽,这些无孔不入的怪物就会瞬间抓住并且趁虚而入,然后……
刺客挪动到废墟的后面,悄悄抬头看向场地中央。刚才还在对峙的双方似乎已经结束了战斗,只剩下那名百夫长还站在原地,其他人已经全体倒在地上,身下的鲜红浸染了地面。
一场死斗?
不,刺客敢用自己良好的视力发誓,这根本就是单方面的屠杀。他看的很清楚,所有倒在地上的亲卫们的脖子都被人划开了一个漂亮的口子,胸口也破开一个大洞,从洞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缺失的心脏——至少有三分之二的部分被什么力量抹除了。
这属于暗杀者的手法实在是相当干净利落,以至于刺客本人都能还原出他们的动手轨迹:先是一把匕首抹过脖子,再是一把长刀贯穿胸口,最后同时抽出两样武器,任由敌人的身体慢慢滑落。
高效、必杀、无可阻挡。
模模糊糊的,刺客觉得杀死这些士兵的东西其实和那些阴影中的怪物是同一种存在。它们可能也对自己起过动手的心思,但不知不觉间,因为自己身上的某些特质,它们最终改变了主意,将杀戮变为生擒,这才有了那个怪物企图引诱自己的举动。
“它们”在招募人手,“它们”在制造同类,“它们”盯上了和刺客一样,有价值成为它们同伙甚至让它们本身更进一步的优秀游荡者。
“它们”在期盼有更多的人在阴影中迷路,然后加入它们的行列!
“传说就要变成真实了……”刺客苦笑起来,接着,他向前一个翻滚,来到了开阔地带。
没有敌人的踪迹,但刺客明白,现在的他不需要畏惧看得见的敌人,他需要畏惧的是看不见的、始终潜伏在阴影中的狡猾敌人。往日里见到一片阴影都要钻进去的刺客,此时却恨不得距离阴影十万八千里才好。
“说不定自己晚上要拿根蜡烛?或者向拉姆斯那个把法杖与权杖混合使用的半吊子法师兼烂尾牧师学习一下光照术或者圣光术?再或者,问问多阿斯她有没有什么永恒夜明珠之类的玩具?呵……或许,接下来自己还能……”
心思繁杂,但刺客的脚步并没有停下,他很快就摸到了百夫长的身边,此时这个一脸倔强的中年人已经再也没有力量支撑自己的身体,脸朝下地倒在地上喘着粗气。
刺客本以为他是在扮猪吃虎,但是下一秒,他就看到了这个士兵腰间那条狭长的伤口,鲜血正不断喷涌而出。按照这个出血量与伤口的位置来判断,他的肾脏恐怕已经被斩断。能撑到这个时候只能说明他的意志坚强,信仰坚定,因此得到了卡尔萨帝国冥冥之中的护佑。当然,玄学的力量再怎么强大,也无法逆转生老病死,换句话说这位苦苦坚持的百人长已经命不久矣了。
刺客站在这个不久前还在给自己设计陷阱,甚至将自己所在的队伍几乎逼上绝境的军官身前,心中却莫名地没有憎恨,也没有愤怒,有的只是对死亡的唏嘘与古井无波的平静。他知道这个世界是生而不平等的,有些人一出生就是为了高高在上,有些人一出生就是为了死亡,在这中间还有一出生……就是为了出生而已的可怜虫。
他自己算是哪一类呢?面前这个垂死的帝国军官又属于哪一类呢?
他不知道,或许只有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才能看清自己。
走到军官身前,他蹲下身子,轻轻地问道: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妻子?你的孩子?”
他发誓,自己只是心血来潮,或者难得地善心大发一下,却从没想过会得到一个令他迷惑不已的答案。
百人长的呼吸突然急促,不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是因为受了什么刺激。他突然间爆发了最后的力量,艰难地支起身子,用尽最后的力气在他的敌人耳边说道:
“我……没有……结婚。那是……假……的……”
“什么?”
刺客微微愣怔,但就在他想要追问的时候,面前的人突然垂下脑袋,眼中最后的生命火焰也消失不见了。
“究竟是什么意思?”
刺客一头雾水,目光却在不经意间瞥见了一个东西,似乎是什么首饰,在百人长的左手无名指上闪闪发光。
“婚戒?”刺客本能地做出了反应,然而百人长的那句话立刻就让他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自己没有结婚,还有什么东西是假的。”刺客望着那枚疑似婚戒的圆环抿了抿嘴,“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结婚,那为什么要在那种地方戴上戒指?如果戒指本身是假的,又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戴着,直到临死的时候才跟我这个外人说呢?”
苦思冥想却毫无结果,最后刺客的视线还是集中在了那枚戒指上。他有种预感,只要拿到了它,其他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于是他伸出手,将戒指从已经有些僵硬的手指上摘下,然后举到面前仔细观察。片刻后,他在戒指内侧发现了什么特殊文字写成的精美图案,或者是……
“一个签名?”精通多国语言与失落语言的刺客很快辨认出了这个名字,“安娜·薇薇安。后面这个符号代表的是忠贞不渝的爱情,再后面应该是某个男人的名字,是她的情侣还是丈夫?”
“这个名字是……”
文字飞旋,逐渐在刺客的大脑里结构、重组,翻译成他耳熟能详的帝国语:“艾森特·卡马……卡马雷斯。一个名叫艾森特·卡马雷斯的男人。”
等等!
刺客的目光中突然流露出一丝惊恐,艾森特·卡马雷斯?
这不是自己在加入刺客兄弟会前的俗世之名吗?
怎么会!
就在他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许多奇怪的记忆突然涌入他的大脑,刺激得他一阵头痛欲裂,再一次直挺挺地栽倒在地。
“呃啊——”
刺客痛呼出声。
“你怎么了,艾森特?”某个女孩的声音在他的脑海深处响起,很是担忧,“这样子很难受,别去抵抗。”
“我不是你的艾森特!”刺客尽最大的力量反击了回去,“我不需要你来担心,我和你甚至都不认识!”
“哦,不,可怜的文森特,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呢?”女孩的声音愈发乖巧,刺客甚至觉得隐隐有种奇怪的愧疚感,好像忘记了她的名字就是最大的罪过——
“滚你的!”他强撑着怒吼,“别随便篡改我的记忆!”
“不,没有人在篡改你的记忆……你想想,文森特,想想父亲、母亲、你的兄弟姐妹,还有你的家……”
“父亲、母亲?”刺客喃喃自语,眼前逐渐出现了两个中年人的形象。男的身材高大但略微有些驼背,两鬓已然斑白,但仍旧身强力壮,身上满是干农活的痕迹。而女人则一头黑发,虽然饱经风霜但气色仍然不错,虽然身材略有发福但并不影响她的针线活。他们和蔼地冲自己笑着,好像无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们都会无条件地予以接受。
“我……”
“你不记得我们了吗,文森特哥哥?”一男一女的童音响起,两个黑发蓝眼,一看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的小孩子手牵手蹦蹦跳跳地来到了他的身旁,“我们还等着你带鱼回来呢。”
男孩眨了眨大眼睛:“虽然妈妈说你做了学徒很忙。”
女孩立刻笑眯眯地接上:“但是你答应过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呀。”
刺客有些迷茫了,他低下头,看到的不再是印象中的冰冷的武器,而是完全的农家小子打扮,右手是一条活鱼,左手是皮匠的用具。
对了,自己是文森特……文森特·卡马雷斯,今天是自己是去皮匠那里做学徒后第一个回家的日子。拉尔和拉尼还等着自己捉的鱼,我一向很擅长水性,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虽然已经记不清上次游泳是什么时候了,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刻在身体里的记忆是不会离去的。
“文森特?”
抬起头,一张熟悉的靓丽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一个名字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薇薇安?你怎么在这里?”
“我担心你又发挥艺术细胞了,”女孩步履轻快地来到他身边,驾轻就熟地接过了文森特手中的工具,接着把空着的手伸到他体侧,“那么,一起回家?”
“……”文森特盯着那只光滑无痕的手愣了一会,然后露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温暖笑容,“好啊。”
他的手慢慢伸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