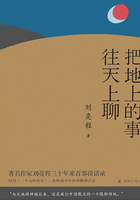我不知道那晚吹奏萨克斯的人是谁,只知道这个人在那一刻可能怀有和我同样的心情。一夜然后消逝,好像道路的存在不是为了住下来而是为了经过。今年的春天,我一直没有听见它的声音。也许这个人是个离乡的游子,已经流落远方。可是,我的耳朵抓住了那只深情的萨克斯,思绪也愿意随它去流浪。
听觉中,涌来嘈杂的市嚣。可是,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它们不在我的道路上,不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住在城东,因为办事去城西。走在那条街道上,恍如置身陌生的城市。小城不大,何以产生这般感受?一想,已近十年没有走过这条街了。这本来是我一双脚就可以抵达的地方,从需要考虑,或者屈从于习惯,我竟然将城西的地理空间,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
单位、家庭、书店、菜市场、邮电局,这是我整体生活之下的几个部分。好像我从不轻易越出这些空间的边缘。以一种画地为牢的方式自愿囚禁了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如果长时间固定在某个地方,他就获得了类似一个国家地理区域的疆界。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感觉犹如出国访问,新鲜,自矜。在自己疆界里生活,安全、熟悉、自由、闲适;长久囿于一隅,又可能心生狭隘。
秋风凉了,生活退守内心。因此常常反抗般地走向郊外。越过一片土地和建筑物,视野变得辽阔。闻到了泥土的气息,看见了云朵在天空舒展。通常走一条路,于是有了猜想,这条路在何处和另一条路交汇,它是不是通到没有尽头的天边。一条路的沿途经过了哪些村庄,哪些人和哪些故事?这些总让人怅惘又入迷。
一只鸟盘旋着从头顶飞过,目光追随它的踪影走了很远。鸟用翅膀在天空划定疆界,恣肆纵横,那是没有边际的庞大“帝国”。云谲波诡的天庭,牛羊放牧在山坡,风驱赶着红马群浪迹天涯。而鸟,无所不至,吹着口哨远征。一个人往往会羡慕一只鸟。羡慕一只鸟抵达的无限疆界。《古诗源》里有一首《悲愁歌》,这歌就是由一位愿意变成鸟的乌孙公主唱出来:“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常思汉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由不得憎恨和哀怨,命运犹如一颗政治弹弓射出的泥丸,固定在蛮荒的大漠。那一射,就再也找不到回家那条青草返青的路。
夜晚,头顶是亘古的星光。翻看手中的《时间简史》,理解这本书,需要非凡的想象能力。据说,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读懂它。物理学家霍金,高度残障深陷轮椅的霍金,某个夜晚的某个时刻,一样的仰望星空,大脑中轰然一声,从这个天启般的声音开始,思维的触角抵达茫茫星海浩浩宇宙的所有细微部分。一个足不出户的人洞知了宇宙的奥秘,他对时间的理解,比爱因斯坦还要深邃。就是这个人,他不能用双脚划定疆界,可是心灵比宇宙还要辽阔。
一个人怀揣一本书去远方寻找一个传奇,这是很年轻的想法。香榭丽舍大街与普罗斯旺小村,尼罗河与金字塔,可能都成为远足的理由。如果我对所有时间和空间的某种存在,真的那么真挚地眷恋,心灵也可以在瞬间抵达。爱与被爱,思想能够攫取的事物和开拓的疆界,今夜,让我的心灵如此豁达和丰富。我已接近中年,我想到了我的心灵应该对这个世界负有的责任。
我想给我母亲打个电话;想给远方久违的朋友写一封长长的信;想捐给那些失学的孩子一份小小的心意;想思考一个复杂又简单的问题。对于他们,可能觉得突然。而在我,是蓄谋已久。
我奶奶有一个问题想了一生没想明白:她去菜园摘菜,路边有棵树,去的时候在反手(左手)边,回来的时候,怎么就跑到顺手(右手)边。我爷爷想的问题比我奶奶的要深奥得多,他读过书,也知道地球是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地球上到处都有人,那肯定有一部分人头朝下生活。我跟他解释,地球非常非常大,他顺手取过一只南瓜,你伢看着,咱们是在北半球头朝上,那下面南半球不就是头朝下,南瓜被我爷爷颠来倒去,最后掉地上摔成了八瓣,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爷爷临终前还在牵挂头朝下生活着的人们:那多难受啊,比我现在还难受。
现在,我想起爷爷奶奶,感到最痛心的是,他们究其一生没想通一个问题,这是他们人生最大的悲哀。往往,在某些人看来是不言而喻的道理,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却成了认知的瓶颈。
最近,我的一位画家朋友经历了类似的事情。他去山区写生,为当地的一位老大爷画了一张画。临走时,老大爷拽住他不放,老人家责备画家画丢了他一只耳朵,他拽着两只耳朵给画家看,瞧!这不是两只,画上却只有一只。画家朋友反反复复解释,这是张侧面像,一个人的侧面只能看见一只耳朵。可是,当老大爷侧过身去,他摸到的还是两只耳朵。最后,他要求画家无论如何要把另一只耳朵给添上。
有时,对一些人智识上的障碍,另一群人看了会发笑。可是,往深处想,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比如,对于时间的理解,我们在霍金面前;对于“相对论”,我们在爱因斯坦面前;对于“万有引力”,我们在牛顿面前,都会一一露拙,败露出我爷爷奶奶和那位老大爷般言行的可笑和智识的浅陋。自然与社会,像深邃的星空,浩瀚博大,时时让人自卑。在自卑中寻找途径,突破局限,无形中涵纳了求知的意义。仰望浩瀚的星空,心底油然为人生的局限而生悲哀,又会从悲哀中产生执着追求超越的激情。
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有一项愉快的劳动。这位西方圣哲吃饱就去雅典城忒修斯庙的东北角,被称为“宙斯门廊”的地方。他喜欢的是拦住行人,以滔滔的雄辩,诘问行人直至他们哑口无言,最终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他认为,除非一个人自认为无知,否则就学不到任何知识。遗憾的是,我爷爷奶奶和那位老大爷都没有被苏格拉底或者类似苏格拉底的人拦住过,否则,他们的人生状态可能会改写。
“人不会渴慕星星”(歌德语),并不是看不见星星的光亮,而是星星离人太遥远。宇宙的定律、生活的真谛闪亮而又耀眼,人们看到光亮却又觉得它们与自己无关。对于局限,没有自卑和恐惧,在未来未知领域,我们这群自以为是的人,有可能像我爷爷我奶奶和那位老大爷一样,茫然而又固执。
树,是一种习惯于逆来顺受的植物。树木是圣物。树木矮矮地生活着。可是,没有一座山能高过一棵树。
人与动物,还有自然中的风暴,都喜欢拿树来撒气。可你看到的景象是:树默默地忍受,那些受伤的部位流出的泪,很快就结成了痂。“在年轮和各种畸形上,忠实地记录了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幸福与繁荣,瘦削的年头茂盛的岁月,经受过的打击,被挺过去的风暴。”一位诗人这样写道。你铲除不了它的绿意,除非你铲除了它的根。
对付树的工具很多,有刀、斧、锯、刨,甚至一把镰刀,一块石头。我儿时伙伴毛头是个弱智,所有人见了,都想愚弄他一番,或者在他身上测试自己的爆发力。受辱后的毛头,转而疯狂踢打一棵树,要么用镰刀给树身分段,要么那石子给树种“牛痘”。
树能怎样?除了用静穆获取怜悯,它没有一件应对伤害的工具。即便温顺的牛,尚有锋利的角作为威慑,而树没有。难怪黑塞说:“树木对我来说,曾经一直是言词最恳切感人的传教士。当它们结成部落和家庭,形成森林树丛而生活时,我尊敬它们,当它们只身独立时,我更尊敬它们。”大师赋予树木以人格,像爱人一样爱一棵树。
从一条街道看过去,最养眼的莫过于树的亭亭华盖。树干上的那些绿色蝴蝶,没有片刻停息扇动翅膀。在自然和人造自然中,最美的风景都是树。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成排高大的棕榈树渲染亚热征候,棕榈树虽移植而来,但已成此地象征。当州政府嫌高达三十米的棕榈树修剪与管理不便而欲除之,却遭到市民一直反对。州政府始料不及,棕榈树已根植在市民心中。
近几年人们注意到,环境与气候日益恶化,犹如大自然癌症。症结正在于,人为破坏了大自然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主导因素正是树木与森林。当雪白的树木躯干顺江河漂流而下,那种触目惊心的场面,无疑让人目睹了一次屠杀。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的伤口,是它们的墓碑,从中可以读到与其年龄相应的沧桑历史。
几天前散步街头,见一人扳一棵小树,扳出“弯弓射大雕”的模样。我走过去,一脚踢中了他的屁股。那人委屈:我没招你惹你啊?我替树委屈:“树也没招你惹你啊!”
像爱人一样爱树木的人,心中必然藏着树木一样的善良和高贵,或者有着谦逊、隐忍、坚韧的树木精神。而那些虐待树木的人,是对着手无寸铁、永不反抗的对象下手,何等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