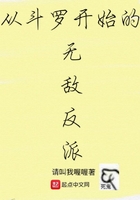7月里,军校的夜晚,一场暴雨骤降,原本闷热的天气和我们溽热的心情一般,陡然晴朗许多。一轮圆月高挂,在这分离的日子里,月亮却是圆的。故乡的歌是清远的笛声,莫非只在有月圆的晚上响起?我们爬上高高的宿舍楼楼顶,找了块儿空地盘腿坐下,一边仰头望月,不断向空中吐着烟圈,一边使劲抽打着叮到身上的蚊子。我们都没有出声,只是沉默地望向那轮圆月,望向,夜色笼罩下的我们的军校。“老廖,这回你可是功德圆满,既回了大首都,又进了不赖的单位,你小子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老弟我啊。”张雪飞感叹着。“啥发达不发达的,我这人你了解,随遇而安,随波逐流惯了,不是个干大事的人。还是你小子这一回大连,绝对是放虎归山啊。大机关坐着,海军制服一穿,回头率保准百分之百。”东北人都喜欢人前整得溜光水滑、人五人六的,张雪飞尤其爱扮英俊青年,我于是这般恭维他道。“不当教员正合了我心意了。教书多累人啊,说是有假期,可是还不得天天备课啊。咱们的那些教材都叫我给扔了。
这往官场的道儿上一奔吧,关键还得脑筋灵活。否则你整得再明白,就是夜夜跟卢梭、黑格尔、叔本华、孟德斯鸠挤一被窝里卧谈都不灵。不过你老廖倒是个做学问的人,发表过不少文章,这教员不当,有点可惜了。”张雪飞挺掏心。“啥可惜不可惜的,服从组织分配呗。穿了这身军装,就得跟颗螺丝钉似的,党把你装哪儿就得待哪儿。”我有点得便宜卖乖,却故作感伤。“老廖,你说奇怪不?平时在军校里头吧,这也被管那也被禁的,心里头经常有股子火,想骂娘,盼着早点毕业。可眼前这真要走了吧,心里头还真有点酸溜溜的,真有点百感交集呢。你跟我说句实话,老廖,上军校,你后悔不?”张雪飞问道。这样的一个问题显然有些大了,譬如叶小米经常挂嘴边的,“生存还是死亡”一样,让人有点下不去嘴。我迟疑着又点上一根烟,也给张雪飞点上,半天没有回答。我们沉默着,把目光放远。不远处的长江一派迷蒙,一两声悠长的汽笛声穿过茫茫夜色,传到了我们耳边。我们的目光移到我们的军校,不自觉地,粘在了对面的女生宿舍楼上。
我们目光炯炯,对着一个个窗口不怀好意地上下盘桓着,像两只死不要脸的苍蝇。女生宿舍的小楼隐藏在一片暗影里,神圣纯洁,傲然不可侵犯。我俩同时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也就在我们莫名的叹气声未落之时,一个窗口的灯光忽然一闪,灯亮了。我和张雪飞的目光立马被牢牢地吸引了。那个窗口开得很高,如果从我们住的那一层宿舍看过去,注定只是一个亮着灯的窗口而已,除了灯光别无内容。可如今我们是高处不胜寒了,所以窗下的一派旖旎风光,就意外地落入了我们的视野。当然,这中间隔着不短的距离呢,树影婆娑,只靠肉眼,我们望见的也就只是几个影影绰绰的身影而已。但那身影明显跟往日不同,不是绿军装下的娘子军们了,而是白花花的一片,水雾轻盈,娇影晃动。隐约的笑闹声传来,甚至水流到地上的哗哗声我们都能听到。“给我守住!我去取望远镜!”张雪飞的声音毫不掩饰地颤抖着,一边命令着我,一边飞身下楼。他妈的这怎么守?我又不能用遥控器把她们一个个都给定住。一等就是半天,张雪飞总算呼哧带喘地上楼来了。
灯光已经熄灭,沐浴刚刚结束,曼妙的身姿,美丽的仙女,瞬间消失了。“人呢?怎么没了?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守着,你小子他妈的怎么守的?”月光下,张雪飞红着一双兔子一样的大红眼,高声吼叫着,显然已经进入迷狂状态。“他妈的,老子就是背。四年一觉江城梦,赢得军校薄幸名。这本来都出了门了,偏遇见老洪,审我半天,问我大半夜的举着个望远镜干吗。这他妈都毕业了,连哨兵见咱们都不带拦的了,他咋就那么大的劲儿呢。我说是舍不得军校,舍不得江城,想用望远镜,再望一望美丽的星空。我连眼泪都给逼出来了啊,生是给急的啊,就怕美人跑了。你说这老洪吧,也是奇怪,老婆刚随军过来,不回家炕头上热乎去,天天跑咱这儿图个啥吗?”“就是为了代表党和人民,彻底镇压你这样的,满管子雄性荷尔蒙乱窜、随时有可能流氓滋事的不良男生。”我满面严肃。“我流氓,我不良?我都干啥了啊?这军校里,女生总共就那么几个,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连脚指头都不用受累。
总共就那么几朵花,谁敢打她们主意啊?众目睽睽的,别说碰了,多看几眼,发几句小感慨,都有人找你谈话。这把人管的,也太严格了。和外头的女同学们多通通信,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寄个照片啥的那总行吧?咱兔子不吃窝边草,单单就爱把那野花采,可咱那郝书记不答应了。那次还训斥我呢,说我脚踩几只船不道德,我一回击吧,她就跟我急红眼了,骂我流氓。我倒是真想当流氓啊,可是哪有下手的人选呢?”“那说说吧,你准备找个啥样子的小娘子,好把你这只生瓜给破了啊?”我和张雪飞开始探讨人生的实际问题。“这个问题,我还真是没好好想过呢!怎么说呢?只要模样别太碜就成。具体一点?那就脸蛋最好像伊能静,身材跟叶子楣差不多就行。”“天,世界末日啊!”我仰面倒地,受刺激不小。那天夜里,楼顶上,我和张雪飞几乎彻夜未眠,一直胡侃到东方发白日头将出。他始终如一名狙击手一般,保持着举望远镜的姿势一动不动,高度警惕守候着猎物的再次出现。那一场女性裸体的遥远而模糊的观瞻,激发起了我们无穷的想象力。张雪飞彻夜守望,雕塑一般的身影,令人不由感叹信仰的力量之大。
那群仙女里,肯定是早已没有了朱颜的倩影。我的那匹梦中的小母马,早早便不见踪迹,空留月光沁人肌肤。匆匆一别,下一次的相遇,会是在哪一夜皎洁的月光下呢?“快看,快看,有情况!”张雪飞猛踹我。清晨迷茫的曙色里,女生宿舍楼前,梧桐树下,一男一女两个穿学员服的人正紧紧拥抱,难分难舍。两名值班员在门口的椅子上打着瞌睡,全然不知敌情已赫然眼前。望远镜里,我们同时看清了。男的是任天行,已被分配到西藏带兵的我们的区队长;女的是叶小米,昨晚喝闷酒喝高了的我的北京老乡。“真没看出来啊,咱们这区队长大人还是一大情种。夜袭女生宿舍,他可是军校历史上的第一人呢。”望远镜后,张雪飞一脸的狞笑,“你说说看,这叶小米,叶小米这锅生米,究竟被咱们的区队长大人做没做成熟饭呢?哎哟,你踢我干吗……”我一飞腿下去,张雪飞捂住肚子,仰面倒地,望远镜被甩出去老远。“我代表人民镇压你!你这个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老淫棍,你的末日来临了!”我沉着地对军校小流氓张雪飞做出一个枪毙的手势。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军校的第一声起床号即将划开晨曦,迎接一天里的第一道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