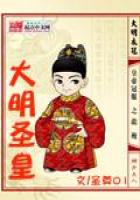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
同党你大爷!
好好睁大你的钛合金狗眼看清楚,我像是与人狼狈为奸的坏银吗?
“像。”
许知南:……
“像是你们二人串通好的,不然她偏巧会逃到这里?”
卧槽,我怎么知道!
我他喵的睡的好好的被人吵醒,现在还被当作坏人,我太难了……
亏得她之前还觉着他为人还不错。
温羡初说的对,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咦,自己怎么会想到那个臭男人?
“我要是和她勾结,我早就把她藏起来了,又怎么会让你们轻易找到。”被人平白无故误解,许知南态度强硬,说话一点也不留情面。
“将军,既然她已受伤,就将她交由圣上处理”朱承颐给出了合理的建议。
一旁的程骁不做声,而是将目光放到了吃瓜群众许知南身上。
许知南倒吸一口凉气,不由打了个激灵。
这位大哥,你瞅我干啥?难道你也想把我抓回去?
她从这道阴冷的目光中确实读出了这层意思。
她反应很快,立即出声为自己辩解。“将军,我真不认识她,和她绝对没有半毛钱关系。”许知南语气诚恳,瞧着倒不像在说谎。不过程骁还是不言不语,被这眼神长时间盯着真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许知南很机智的将目光转移到他旁边的朱承颐,“不信你问朱公子,我是个好人,普普通通的良家妇女。”
要不是为了脱身,打死她也不会这么形容自己。
啊呸,良家妇女…个毛,明明是少女,划重点,少女!
“她确实不认识那女子,这次应该是个意外。”许知南见他一直不发声,本来都不抱什么希望了,这下终于放心下来。
朱兄,我记住你了!
许知南没再说什么多余的话,以她的猜测,他们应该不会再怀疑她,就此放她一马了。
果然,包围了她整个院子的军队有序的撤离。她这里总算又重归平静。
她的视线落在被无情拖走的女子身上,不免心中感叹,可惜了,这么高颜值的小姐姐。
不过她很快就收起这份心思,因为她终于记起这个女人是谁了。
当初挟持她做人质的就是她!
……
什么世道,亏她差点沦为颜控。
婴儿的啼哭传入许知南的耳中,她这时才惊觉,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房间里。
看怀中的小家伙眼泪直流,哭的不歇气的样子可把许知南心疼坏了。她的脸紧贴着板栗的额头,极力用温柔的声音安抚它的情绪。
渐渐地哭声小了,她赶紧给它喂奶好让它安心睡去。
被那么一闹,许知南彻底没了睡意。突发奇想的坐到院子里撸狗赏月去了。
“今晚的月亮可真亮啊。”许知南摸着笨笨柔顺的狗毛感慨道。
“叮,您的管家助手小南南已上线。”
卧槽?!
谁在说话?
许知南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南大的记性可真差,我是小南南啊。”带有一些俏皮的电脑音再次强调。
小…南南?
好像有点印象……
许知南在记忆库里搜索了半天才想起这是个什么东东,不过她的语气很平缓,倒也听不出来是喜悦还是生气。
“你一般在什么时候出现?”许知南觉得她很有必要知道这一点,免得到时候又吓她一跳。
“必要时候。”
说的和没说一样,许知南忍不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小南南这次是想提醒南大,你一定要去救嫚珠。”这回它竟一本正经起来。
“嫚珠是谁?”为什么要去救她?
“嫚珠是主线里的重要人物,用南大的思维方式理解,也就是剧本里的女二号。”
WTF?
女二号?
这么快就交代了?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呀。
见许知南还是一头雾水的模样,小南南继续解释。“就是今晚掉在院子里的那个女人。”
是她?许知南又骂了句脏话,实在是太震撼她的三观了。
“她是乱党,我救她不等于自寻死路?”许知南可没有这个把握。
“你如果不救她你就完成不了任务。”嗯?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
“她将成为温羡初的妻子,南大的任务便会失败。”
许知南的眉头越皱越紧,怎么听着像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
“这是小南南给的提示哦。”噗,我好像只能接受的样子。
许知南把整件事情串在一起反反复复想了一遍,也没想出个救人的方法。
如果她被判了死罪,那她有什么办法。
救不了她,就完成不了任务。这个问题困扰的许知南整夜失眠,好不容易凌晨有了点睡意。
她是被一阵吵闹声惊醒的,快晌午了,太阳高高挂着,照的地面暖烘烘的。
想起昨天小南南的话,她脸也没洗就跑向了大门口。
外面果然乱糟糟的,但见他们急急忙忙的样子,许知南抓住个路人就问。
这一问才得知,今日午时便要处死那个乱党。
许知南当下就蒙了,她要是晚一步,女二岂不是就要死了?
那不对呀,死了怎么会嫁给温羡初?就非要她充当炮灰吗?
眼下她也顾不得那么多,抱起熟睡中的板栗就往刑场赶。
以前古装剧看多了,这种场面也是见怪不怪了。
那女人一身脏乱的囚衣跪在正中央,凌乱的头发挡住了她的正脸。看得出她虚弱不堪,瘦小的身板如同纸片一样,风一吹就倒。
“行刑。”随着监斩官的一声高喊,早已就位的刽子手举起手中的长刀。
这时候,一定会有个人阻止这一切。
“住手!”许知南用尽全力在喊,果然,所有人的注意放在了她身上。
她早就习惯了那些个异样的眼光,所以也没放在心上,她现在只有一个目的。
“你是何人?”监斩官发问,态度并不友好。
“她,你们杀不得。”许知南正对上那双被发丝遮住,快要看不清楚的眼眸。
她的眼睛很漂亮,又黑又亮。此时看向她,仍旧不见半分柔软,平白又揉进了一些看不清楚的情绪,令人好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