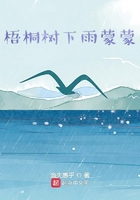现在谈陶侃的政治态度,从而对陶渊明的政治态度也作一臆测。
首先,我们要记得陶侃是一个跋扈的军人,更恰当地说,是一个跋扈的军阀。他带兵四十年,有曹操那样的机智和勇敢,他在东晋的地位是在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和刘裕这一个行列里。从王敦起,到刘裕为止,都是想学曹操、司马懿那种夺取政权的方式的。
当时的晋室很微弱,所谓皇帝不过是天天受那些有名的士族和跋扈的军阀的气的可怜虫。在最初,军阀与军阀间有些牵制,那些出身士族的政治家又有些手腕,就利用军阀间的矛盾,维持了小朝廷的局面。后来这些士族的势力衰弱了,军阀们就自相吞灭,所以在士族出身的大政治家谢安一死(公元三八五年),桓玄就几乎成功(公元四〇三年),刘裕就完全成功(公元四二〇年)了。王敦(公元三二四年)、苏峻(公元三二八年)、桓温(公元三七三年)等的失败,不过是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而已。
这些军阀夺取政权的步骤,几乎有一个一般的公式:一是握有军事大权;二是占有两个军事要地之一,或者是长江上流武昌、江陵和荆州一带;或者是在建业之西京口(镇江)一带;三是对内要有军事上的优胜的表现,先是平“造反”,取得更高的军事地位,自己就慢慢也对“造反”垂涎起来;四是对外也要立功,因为这时一般人所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收复北方失地,在这一方面如果没有表现,是不容易受人拥护的,这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本;最后是五,就是取得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的“阿衡”的地位以后,就请皇帝“禅让”。刘裕就是完成了这些步骤的一个典型,其他的军阀或者完成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具体而微。
陶侃也是属于这个类型的。他是一个活了将近八十岁的老军阀(他在临死时上表说:“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时为公元三三四年)。他在西晋末年已经崭露头角,他已是荆州刺史,打败过王真,打败过杜弢。平了王敦以后,他是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的征西大将军;平了苏峻,他被封为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他镇守的地方,正是江陵、巴陵、武昌等地。这就是,他已有了上面所说的夺取政权的三个步骤:握军事大权,居军事要地,平内乱有大功。那么,下一步呢,那就是他在最后所上的表中所说的:“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毋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可惜的是,这一步已经布置了,却没有完成就死了。
就他的身份和地位看,就他处的环境看,就他前前后后的同样身份和地位的像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刘裕等的榜样看,他如果是例外,那倒不可思议了。
陶渊明在《命子》诗里说他“天子畴我”。注家虽然在“畴”字上费了许多事,绕了许多弯儿,不肯说那就是和天子相等的意思,然而就当时的情势看,就下文“孰谓斯心,而近可得”看,并且注家已经知道是指桓玄、刘裕了,那么那句话的实质意义乃是:“彼可取而代也。”
如果我们根据当时历史的情况加以理解的话,陶侃是不可能完全忠于晋室的。他可以夺取政权,一旦条件成熟。历史的记载也就是如此。《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记他平苏峻之役时说道:
暨苏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为贼所害,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因推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而又追回。峤以峻杀其子,重遗书以激怒之。
《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就记得更明确:
(峤)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国难,侃恨不受顾命,不许。……时陶侃虽许自下而未发,复追其督护龚登。峤重与侃书曰:“仆谓军有进而无退,宜增而不可减。……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恐惑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假令此州不守,(祖)约、(苏)峻树置长官于此,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义言之,则社稷颠覆,主辱臣死,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义,开国承家,铭之天府,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今出军既缓,复召兵还,人心乖离,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以孚三军之望!”峻时杀侃子瞻,由是侃激励,遂率所统,与(温)峤、(庾)亮同赴京师。
可见陶侃本来不想出兵,出了兵又后悔,只因想到爱子被杀,但也是别人借此激怒,才去打仗的。他对于晋室是多么冷淡,不但冷淡,想到“不在顾命之列”,还“深以为恨”呢。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传说:
(侃)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晋书》卷六十六
清丁国钧《晋书校文》对于这种传说很不以为然,说:“曰潜有,曰每思,曰自抑,皆非本人不知,作史者从何探得?桓公东晋第一名臣,而传文多微词,于无可捉摸之中,构坐以不臣之罪,尤可骇怪。”其实是没有什么可骇怪的,如果从当时大势上去理解的话。而且上面这一段传说也并非《晋书》的创作,而是王隐的《晋书》和刘敬叔的《异苑》中已经记录了的。我们说过,陶侃是一个精细而有打算的人。他想夺取政权,但他不会不考虑到现实的条件。他也一定觉得当时条件还没成熟,例如对外立功,就还只有布置而没完成,如果猛进,便会失败。他有这种意识之后,所以在梦中,就变为折翼堕地了。他大概并非因为有过这个梦,才自抑而止,恰恰相反,正因为自抑而止,才有了这个梦的吧。
除了由于以前的人对于梦的科学知识不足,记录梦和现实的先后关系上有所颠倒之外,这个梦的传说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也完全是有真实性的。
陶侃不是一个完全忠于晋室的人,而是一个有野心夺取政权的人,乃是正如桓玄、刘裕的类型一样的人,只是还没布置就绪,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以前的一部分历史家不肯这样认识他,那只是由于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怕给这种人以鼓励,同时也是怕见“叛逆”的字样,有些触目惊心就是了。后来又由于陶渊明的地位之提高,统治阶级的学者既认定陶渊明是忠于晋室的,于是也助长了粉饰陶渊明的先辈陶侃的政治态度的风气。但也有折中的意见,以为陶渊明虽是忠于晋室的,陶侃却有问题,那就像蒋薰在评《命子》诗中所说:“长沙公侃,前史多议其非纯臣,而此心有不可问者,陶翁为祖讳也。”[4]多少看见了真理的一半。
陶侃的政治态度显明如此,陶渊明对于他既只有赞扬而没有批评,加之陶渊明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又受陶侃的影响那样大。陶渊明对于晋室是什么感情,还不很容易推断了么?但这个结论且不忙着下,再看他的外祖孟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