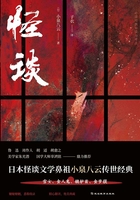孙萌 译
亲爱的×先生,
我邀请您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待戏剧,那是因为我希望社会学将成为我们现存戏剧的死亡时刻。正如您很快看到的那样,社会学有一个简单而激进的任务:去证实这种戏剧的继续存在没有正当的理由,而任何(现在或将来)基于曾经令戏剧成为可能的设定都没有未来。引用一个社会学家的话,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接受他的措辞——即戏剧没有它的社会空间。您的学说是可以享受足够的思想自由的知识的唯一分支。其余的一切都太过拘泥于保持我们时代的普通文明水平。
您对惯常的迷信有了免疫,即认为一出戏剧要满足人的永恒的欲望,而这唯一的试图满足的永恒欲望就是去看戏的欲望。您知道其他的欲望在改变,您知道原因。由于您没有感觉到一种欲望的消失意味着人性的流逝,您,一位社会学者,孤单地准备去接受:作为我们戏剧基础的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再也没有效力了。这些作品之后的三百多年,个体发展为资本家,而杀死他们的不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后果,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再提后莎士比亚戏剧也没什么意义,因为它惯常地更虚弱了,而且在德国因拉丁情结而走向堕落。在地方爱国主义之外,它仍然得到支持。
一旦我们接受了社会学的观点,我们就认识到只要牵扯到文学,我们就身处沼泽。我们也许能说服唯美主义者去接受社会学家的看法——目前的戏剧不好——但是,我们不能使其放弃“它可以转好”的信念。(唯美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只能设想戏剧通过此行业的陈旧的技艺来达成“改善”:对于旧意识更好地重建,或者更好地调动那些习惯老式戏剧动机的观众等。)显然,只有当我们说这种戏剧已经是朽木不可雕并请求把它废除之时,社会学家才会支持我们。社会学家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况:无论做多少改善改良都于事无补。他的评价标准不是好与坏,而是对与错。如果一出戏剧是错的,那么他不会因为它是好的(或美的)而赞美它。他对于一个“虚假”作品的审美诉求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只有他知道什么是错的,他不以相关性行事,他以重要利益作为自己行为的基础;证明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没什么意思,他只想发现那个值得证明的东西。他对什么都不负责,但是只对一件事情负责,社会学家对我们负责。
美学观念并不适合当前写作的戏剧,即使获得赞誉的作品也一样。您只要看看支持新剧作家的任何一个运动就可知道。批评家的直觉引导他们纠正其美学词汇,即便如此也没有给他们积极的态度提供多少值得信服的论据和适宜的公之于众的方法。更有甚者,在鼓励出品新作的同时,剧院根本没给出实际的指导。最终新剧目只能在老剧院上演,延迟了老剧院的坍塌,而这正是它们未来得以存在的前提。如果忽视当前这代人对之前发生的事所采取的反抗态度,并且持普遍观点,认为那也只不过是吵闹着想要被接受以及受重视的表现,那么是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作品的。这一代人不想俘获剧院、观众和一切,不想在同样的剧院为同一群观众上演好的或者纯粹当代戏剧;他们也没有机会这么做;为不同类型的观众而占领剧院,这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机遇。现在所作的剧本正在越来越多地通向与社会形势相适应的伟大的史诗剧;除了少数人可以理解人之外,没人能够理解这些剧本的内容和形式。他们不再满足旧的审美,他们要摧毁它。
与你一同希望
布莱希特
——摘自《柏林信使报》(Berliner B?rsen-Courier)1927年6月2日
注:X先生是后来的弗里茨·施坦恩贝格(Fritz Sternberg)教授,他在同一份报纸的5月12日发表了一封信。两人在来年冬天一个创作《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的计划里涉及皮斯卡托(Piscator)。[1]施坦恩贝格的信和回信附于其《诗人与理性》(Der Dichter und die Ratio)之中(哥廷根:Sachse und Pohl出版社,1963年版),其中对于二者的关系做了简短介绍。回信评论道:“不是马克思引导你提及戏剧的没落以及谈论史诗剧。是你自己。因为,文雅点儿说,就是‘史诗剧’——是你,布莱希特先生。”
布莱希特自己第一次在刊物上使用此词是在5月16日的《新道路》杂志(柏林),其中他指出“伟大的史诗剧和纪实剧的创造适合我们的时代”。7月一篇未署名的《马哈哥尼城的兴衰》的首版演出笔记(很有可能为布莱希特所作)称其为“一部小型史诗剧,从我们所存在的阶级结构不可避免的崩溃中做出了逻辑上的总结”,并说道,作曲家库特·魏勒“开始转向一种去剧院纯粹找乐的观众”。
注释
[1] 见《戏剧选1》,第153页,布莱希特与施坦恩伯格和耶林(Ihering)的电台谈话,同上书,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