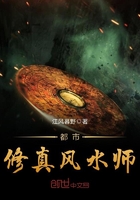回到护理病房后,他一直半躺在沙发上,眼睛微张,呼吸平缓,一句话也不说。直到当晚十点多,他悄悄从护理病房溜了出来。他走在空旷的大街上,行人稀稀落落,秋风骤起,路边的法桐每一次随风摇动身子,都会掉下来几片枯黄的叶子。他的身体仍然难受,但是痛苦感已大大降低,心灵和脚步都变得很轻松,与从前痛苦的日子比起来,现在仿佛身在天堂。李叶意识到这是身体发出的极其糟糕的信号,预示着他大限将至。所以,他身着正装,打扮得十分体面,他已经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了。
“先生,进来喝杯咖啡吧。”一家咖啡馆门前站着一位侍者,他在招揽顾客,见到李叶在大街上信步闲游,于是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侍者见到李叶正盯着他看,像是犹豫不决,于是赶紧补充道:“人生的味道全在咖啡中,有苦有涩也有香甜,不是吗?”
这句话打动了李叶,他走了进去。
“你用这句话招揽了多少客人?”李叶边走边问侍者。
“只有您一位。”侍者诚恳地回答道。
“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李叶问。
“李白,他文风飘逸,豪迈奔放,意境奇妙,潇洒不羁,令人叹服。”
“当代诗人呢?”
“叶子女士。”
“如果见到她,你最想对她说一句什么话。”
“我想问她一个问题。”侍者边引路边说,“她还未婚,或许会终身不婚,她是在期待着完美的爱情,还是已经享受过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爱情了呢?”
“您认识叶子女士吗?”见李叶不语,似乎是陷入了回忆,侍者问道。
“不,我不认识。”
“您读过她的诗吗?”
“不曾读过。”
“那太遗憾了。”
李叶选择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此时咖啡厅只有他一个客人。不一会,一行五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在离他几米处的空位处坐下。那五个人有四个魁梧健硕,一个又瘦又高;他们一坐下就对侍者吆五喝六,十分无礼。五支香烟一起点燃,咖啡馆里很快就烟雾缭绕起来。李叶抬头瞟了他们一眼,收回了目光后又突然射了出去,他的目光落在了瘦高个的身上;瘦高个脖子上有一片倒三角大红斑,红斑中间长着一颗指甲盖大小的黑痣,黑痣中心生出一根黄毛。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瘦高半躺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大声地问。
“人命的事儿无非就是钱的事儿。”其中一个双臂布满纹身的平头大汉回复道,“我们的渣土车撞死人,只要这件事别传到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一切都能压下来。”
“一定要赚快钱。”瘦高个用手比划着说,“不要因为这件事耽搁了工程的进展,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那么以后再接工程就会很困难,合作方会认为我们没有解决事情的能力。渣土车晚上该拉几车还拉几车,一切照旧。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为好,千万别让那帮记者把此事给捅出去,要不然就麻烦了。”
“这件事您放心。”另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说,“司机是按趟拿钱的,他们巴不得能再多拉几趟。交警方面已经打过招呼,闯红灯、超速、超载的事儿不用担心,有专门吃这碗饭的人,但这碗饭太大了,一个人肯定吃不下,哈哈哈,谁都有好处,哈哈哈,谁会跟眼前的好处过去不呢?父母们嘱托孩子们第一个道理就是知好歹、识抬举,识时务者为俊杰嘛,都睁只眼闭只眼,哈哈哈……”
李叶目露凶光,他心里想:“恶性未改。”
事实上,那个瘦高个的确是多年前抢劫过李叶的人,不过现在他已成为百万富翁。早年间,他凭借好勇斗狠、手段残忍,很快就集结一群臭味相投的社会闲杂人员。刚开始,控制女人做皮肉生意,让他赚了第一桶金。随后,浩浩荡荡的城镇化建设大潮席卷中国大地,这是一块大蛋糕,让参与拆迁和建设工程的每一个人都迅速富有。瘦高个看准时机,买通政府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开始插手、解决抗拆家庭的事务。他极度无耻,无所不用,平息过数次群体性事件。几年后,他用巨额贿赂获得了改造区残垣断壁的清理工作,第一个项目做完,他就得到了上百万的收入。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了临近县市。在此期间,他赌博成性、挥霍无度,名下有数套房产和数辆豪车。光鲜亮丽的外表和富足惬意的生活让三个女人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并毫不犹豫地为他生下五个子女。更令人惊异的是,那三位经常见面的女人一点也不会因他生性喜欢拈花惹草、朝三暮四而对他有任何失望,反而觉得他对别人吆五喝六、大声嚷嚷是精明能干、气度不凡表现,她们喜欢自己的男人颐指气使、蛮横凶恶的样子。她们在他面前表现得像亲姐妹一样亲密无间、通情达理,而在饱受争风吃醋的烦扰后,往往会通过购物、旅游、美食、酒精等方式重新点燃欢乐心情。
李叶起身走到不远处的工作柜旁,拉开抽屉,拿出两把西餐小刀揣进口袋里;然后他重新坐回原位,默默地盯着那伙人,酝酿着情绪。五分钟后,正当那五个人谈得眉飞色舞、忘乎所以的时候,一个马克杯从李叶手中飞向那几人的桌子上,桌子板的材质是大理石,马克杯砸在上面瞬间支离破碎,伴随着一声骇人声响,那几个人吓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们立刻就发现了杯子是从何处来,从李叶不善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是有意为之;仅仅用了一秒钟时间,他们就想到了一万种能给这位瘦弱的陌生人带去痛苦的方法。五个人高声地咒骂,一起向李叶围了过去;但是很快,李叶两手中露出了明晃晃的尖刀,暂时阻止了他们向前迈进的脚步。李叶怒目而视,身上散发出危险的气息,但他身体虚弱,使他的气势大打折扣。
“兄弟,我们难道有仇?”瘦高个耸耸肩、摊摊手,满脸疑问。
“只有这样,我才有资格跟您讲话,不是吗?”李叶面若冰霜,指着瘦高个说,“我很想跟您聊聊天。”
咖啡馆里的值班经理带着两位服务生赶来,他们正要阻止,就被李叶凶狠的目光定在原地。
瘦高个并非胆小怕事的人,他慢慢地走向李叶,小心翼翼地坐下,随时做好回击的准备。
“你知道我们的差距吗?”李叶死死地看着瘦高个冷冷地说,“你残忍歹毒,是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吃肉、喝酒、玩女人,但是我并不想过好日子,因为我早就不想活了。”
“仇有头债有主,这位先生,恐怕您认错人了,也骂错人了。”瘦高个表情恢复了轻松,语气也显得很轻松。
“官商勾结,祸害民众,破坏司法,赚一些脏钱,气焰嚣张,丢人现眼,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会做这样的勾当吗?蛀虫、苍蝇和垃圾。你所认识的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官员,沐猴而冠,一群墙头草,像个妓女一样廉价,给点钱就能买通,背叛誓言与人民的信任,是国家的耻辱和败类。我知道说这些没有任何用,喝酒、吃肉、搞女人,这样的人生就足够了。但你应该清楚,如果你失去了残忍歹毒,失去了麻木无情,那么你就是个实打实的废物!”话音刚落,李叶举刀就向瘦高个刺去。但是他的举动太慢了,他刚伸手,刀具就被打落在地,紧接着,他的头部被瘦高个的拳头猛击一下,他重重地摔倒桌子上,昏死过去了。
直到三天后,李叶从昏迷中醒来。此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就连睁眼对于他来说,都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仿佛所有力气都用在了维持呼吸和心脏跳动上。随后,他见到许多张再熟悉不过的面孔,每一双眼睛中都饱含泪水。他看到父亲急得在病房里团团转,面色铁青,惊恐万状;这是李叶第一次看到父亲变成这样子,祖母死的时候,他也不曾如此。事实上,李树已经暗地里痛哭过几次,就在昨天晚上,他上床后和妻子四目相对,两人抑制不住感情,抱头痛哭起来。吴霞早就察觉到儿子消瘦得厉害,李叶总敷衍说是因为胃病加剧,等忙完工作后再悉心治疗;她虽然心疼,但她知道胃病不好治,所以已经做好长足准备,等儿子闲下来后专心地照顾他,保障他一日三餐吃到清淡健康的膳食,从根源上杜绝病情的蔓延,再加上药物的治疗,对缓解儿子的胃病一定有事半功倍的疗效。她打电话给李叶,让他回家休养一段时间,他总推辞说自己很忙,忙很重要的事情,这些事对家庭和他的未来至关重要。年轻人事业心重是件好事,吴霞甚至还有些欣慰。当她收到儿子病危的消息后赶到医院,看到瘦成皮包骨的奄奄一息的儿子,立刻就昏倒在地。方菲听到李叶苏醒后,小跑着过来,嘴里喊着:“怎么变成了这样呢?怎么变会这样呢?”她眼睛刚转了两圈,大滴大滴的泪水就滚了出来,随后趴着李叶胸膛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李果站在一旁显得手足无措,可怜而又无助,当他握着父亲的手直视着父亲,很快就哽咽起来,为了显示自己的不服输与坚强,他不想让父亲看到自己软弱的一面,于是扭过头去抽泣起来。李叶欣慰极了,他对自己说:“果果长大了,知道用眼泪去爱别人了。”他突然回想到祖父去世时的眼神,想到了当时自己并未流下一滴眼泪,他曾长久地迷惑不解,现在,他想通了:“对一个人寄托了多少感情,就有多少泪水。”方烛和王美也来了,方烛哀伤而又认真地说:“尽管在这个时候提到死亡是非常不合适,但有些话不说便再也没机会说了。愿我们来世还做一家人。”李悦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回来了。外甥和外甥女手里捧着李叶的书,诚恳地说道:“我们会以舅舅为荣耀,并且会向异国的朋友们讲述您的故事。”
李叶体内健康的链条如同多骨诺米牌倒塌的速度一样断裂了。当天晚上,神志尚且清醒的李叶整晚都在做噩梦。又过了一个晚上,同样的噩梦仍然纠缠着他。他恢复意识后的第三天,在黎明来临时,奇迹降临在他身上。他能小声地说话了。
毫无疑问,他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肯定是白发苍苍的母亲。他握紧母亲的手,在这一刻,
他断定,他此生从未握过如此柔软的手。吴霞看到儿子嘴唇在动,于是把耳朵凑到李叶嘴边。
“妈妈,我……我连续两晚都在做同一个梦。”李叶气若游丝,“我……我梦见一个尚
未成型的婴儿——她虽然尚未成型,但是我内心却清楚的知道她是的女孩。一整夜,她都在我身上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像是要张口吃我的肉……”李叶忽然睁大眼睛,布满血丝的眼球充满恐惧:“她……她是一个魔鬼!我问她,‘我是坏人吗?’——她说,‘不是’——我问,‘那你为什么害我?’——它说,‘因为你离我最近。’”
吴霞回想到往事,内心突然一惊。她呼吸急促,浑身颤抖,身体僵直,眼睛滚圆,瞬间,泪水就布满了她满是皱纹的苍老的脸上。
“对不起,我的儿子,都是妈妈的罪孽。”吴霞痛哭着说,“当年我跟你祖母关系很不好,我认为原因在于第一胎生的是个女儿,这才让他们全家都瞧不起我、苛责我、刁难我。母凭子贵,我一心想要个儿子。等到怀第二胎时,我天天拉肚子。因为怀你姐姐的时候,我就是天天拉肚子,所以我认为,第二胎肯定还是个女儿。于是,仅凭这一个现象,我就自作主张把孩子打掉了……作孽啊,都是妈妈作的孽啊……”
“妈妈——”李叶同样失声痛哭起来,往昔的岁月如同电影快镜头一样在眼前浮现,他嘴里不断念叨着,“妈妈——我不想死——妈妈——我……我害怕……”
李叶在母亲怀里再次陷入昏迷。这次,他再也没能醒来。这是李叶的第二次死亡,第一次,他死在刘芳的怀里;从那以后,他不再害怕,不再奢求,不再祈祷,他再也没有了理想、信仰和欲望。第二次,他死在了母亲的怀里;从这一刻起,他没有了知觉,没有了感情,没有了力量。我们知道,他还会迎来第三次死亡,那时候他的墓志铭将会模糊不清,他的一切都化作尘土,世界上再也没有认识他的人,他的画,他的书,他曾经激励人们前进的言论,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渐渐遗忘。我数次进藏,也许数次与李叶先生擦肩而过,也许我们有过匆匆一瞥甚至是简单交谈,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人生中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许我俩不曾有过交谈也素未谋面,但这并不影响我时常怀念他,毫无疑问他已经成了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我把李叶的故事讲给妻子听,她听完为之动容,她从不允许我饮酒,但如果李叶突然登门拜访,她一定会亲自煮酒斟满,让我俩痛快畅饮,喝个酩酊大醉……
五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