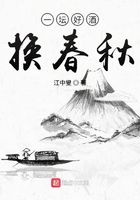作为一名公共社会学家,我很想让大家了解我的所想所思和所作所为。众所周知,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在这个信息发达的年代,我们可以很轻松从网络上找到关于每一个民族的详细信息。但是每一个民族中单一个人的情感世界呢?大多数人知之甚少。我想充分了解每一个民族,并把所了解到的通过图片和文字记录下来,出版成书,供同行参考研究,授课教学,也供大众读者阅读消遣。为了使冷冰的文字更耐人寻味,在准备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再然后,就是跋山涉水的探访交流,研究编纂;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倒不是因为奔波劳顿——因为很多人并不具备系统性的表达能力,而且,由于学识、见识和生活上的差异,很多时候,在交流时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在讲些什么。
真诚和耐心总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回报,即使是在我国西藏地区,虽然有着语言上的障碍,但经过了数月的考察调研后,我仍然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学术资料,解决了心中诸多悬而未果的疑惑,弄懂了藏民在面对现代文明时的坚守与改变,以及他们是如何思考问题和理解这个世界的。看着桌面上厚厚一沓访谈笔记,本已到了该凯旋而归的时刻,然而我一方面贪恋高原美景,另一方面又希望能深入更加闭塞的乡村,探听到更为神秘古怪的见闻,即使再不济也能散散心嘛,毕竟无限风光在险峰,于是我独身一人驱车向着远方绵延无尽的山峦间驶去了。
很快,手机完全失去了信号,但还好前方有路。虽然路烂得快把我骨头颠散架了,但我的心态一直保持得很好,我有充足的食物、燃油和水,还有厚厚的被褥御寒。而路的存在时刻都在说明着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直走,肯定会遇到人。这就是我在与外界完全断开联系而又能保持好心情的重要的一个原因。
车辆在经过一个垭口时底盘忽然发出一声巨响,紧接着车身猛地一跳。我急忙下车查看情况,发现油底壳正在不断漏油,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一块从山上滚落下来的尖石头。正是这块石头,使我差点殒命此地。
车子丧失了动力,此时太阳的光芒已变成了橘黄色,有了日薄西山的迹象。我想起了妻子的忠告,她说:“无论行程有多紧急都不要走夜路,看不见的危险靠谨慎也无法避免。”于是我决定在此地住宿,打算明天破晓时分步行寻找救援。吃了一份自加热盒饭和一份还算美味的火腿片,补充了水分和水果,我拿起相机开始拍摄这里日落时的壮美自然景观——天太干净了,是那种沁人心脾的纯粹原始的干净——整个天空可以分为三部分,西方的三分之一沾染了晚霞的颜色,像少女脸上的绯红;头顶的三分之一是湛蓝色,蓝得像一块碧玉;东方的三分之一已经变成黑色,上面点缀着点点星光。刚入夜,我斜躺在山坡上看着满天熠熠生辉的星斗,此时万籁俱寂,虽然我置身于寒苦之地,但我并不感觉到寂寞和恐惧,一丁点也不,反而不住地感慨人生的奇妙。
当晚,我大概在十点钟左右进入梦乡,入睡前并不觉得身体有任何异样的表现,只是稍微有些呼吸困难,每呼吸四五次就得深呼吸一次,仅此而已。凌晨一点多,我忽然惊醒,发现自己浑身都在颤抖,指甲和嘴唇都变成了紫色。尽管我拼命呼吸,但仍觉得出气多进气少。我的心脏在疯狂地跳动着,伴随着强烈的心悸,仿佛心脏随时会蹦出来似的,而且根本不受控制,不是深呼几口气或者捋一捋胸口就能平息下来的。我意识很模糊,几乎不能心算十位数加减法,我的体力尽失,身子仿佛被一头猛兽迅速扑倒并死死压住,移动一下都很困难,。
情况似乎越来越糟,身体的不适感逐渐加强,我的鼻子里慢慢涌出粉红色的鼻涕,头痛得像扎了一万根针似的——这是典型的肺水肿的病理现象。我半睡半醒,听到雪花打在车玻璃上的漱漱声,这种声音告诉我此地的昼夜温差超过三十度。
太阳刚探出头不久我就睁开了眼睛,只不过眼神中已经对这个世界没有了好奇,只有惊恐和绝望。我看着地上被风吹得稀稀落落的白雪,看着远处被迷迷蒙蒙雾气半遮半掩的绵延无尽的群山,它们的身形显得那么的柔美,像成熟女人凹凸有致的身形曲线。我看到一朵乌云遮住了太阳,不知是乌云太过轻薄亦或是烈日太过毒辣,乌云即将被完全晒透,变得很像正在熊熊燃烧的炭块。太阳从乌云后面射出万道光芒,光芒进入晨雾之中,经过折射形成万道彩虹。多么壮观的“丁达尔现象”啊,这种美打动了我,甚至令我生出“长眠于此,死而无憾”的感叹来。但没有人会因为一种自然美而心甘情愿的死去,稍加思索后我改变了判断,眼前这种美对于我而言不过是一种悲凉的凄美罢了。睁着眼太累了,就在我合上眼的一刹那,紧接着就投入了回忆的怀抱里。
当我驾车走了半个多月的山路,放眼远眺仍能看到前方有绵延无尽的群山时,我对地理课本上“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翻开地图可以看到有些山脉像一根头发丝那样纤弱,但身临其境后会感慨它是那么的巍峨挺拔。西藏考察结束后,也就是前几天,我听说附近有个村子的寺庙里存放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因为我此次进藏的目的正是研究民俗与文化,于是我便赶忙驱车前往。驻村扶贫干部热情的接待了我,他一面当向导,一面又当翻译,使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第二天,驻村干部带我去拜访一位远近闻名的藏族老人,所有认识这位老人的人都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勇士。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每当从老人家门口经过时都会脱帽致敬。令人惋惜的是此时他已身患绝症,我见到他时第一眼就看得出他被病痛折磨得够呛。随后我看了他年轻时候的照片——黢黑的肌肤、健硕的臂膀、坚毅的眼神和魁梧的身形——如果与现在的形态做个冒昧的比较的话,就像是葡萄和葡萄干的区别那么大。我很想听听一个勇士是如何蔑视死亡和病痛的,于是就以此为话题同他展开了交流。
“我脸上有无数道皱纹,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哪一道是被忧愁刻出来的,哪一道是被岁月刻出来。”老人说:“孩子们能看到前方的路上有弥漫着爱情香味的玫瑰等着自己,二十郎当岁的人能看到前方有幸福的家庭等待着自己,当然了,还有拼搏、汗水、眼泪和后悔等着自己……我年少时,有个老和尚说到最后只有死神在等着你,我知道他说的很对,但我总觉得死亡与我无关,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这句话忘得干干净净。直到我罹患绝症时,我放眼望去突然就看到了死神,时间化作一双有力的手,不住地把我推向它。刚开始,我有些时候会浑身颤抖,我不知道是因为愤怒还是因为恐惧而颤抖,我总是会感到忿忿不平,脾气变得很糟,甚至会迁怒家人。不过疾病很快就狠狠地教训了我,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学会了一生都没有学会的处事诀窍:坦然面对。你知道病痛的滋味吗?试想,一场感冒发烧就会让你浑身难受得要命,而那只是一场感冒发烧的小病而已。绝症是什么滋味呢?每一寸肌肤、每一根神经、每一块骨头都是痛苦的,而更要命的是这些痛苦将会是生活的常态。你大把大把地吃药,而那些药物并不能祛除疾病,只是能让你再多撑一段时间而已;你的嘴巴告诉你它不想吃任何东西,哪怕是山珍海味,舌头与它心照不宣,除了苦味,它品不出任何味道。你只想吃药,不,是渴望吃药,就像饥饿的人渴望吃饭一样;你的四肢会罢工,你哪都去不了,它们将不再为你服务,甚至成为累赘;你的眼睛似乎会把任何东西都变成灰色,哪怕遇到了最鲜艳夺目的花儿……你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永远离你而去,再也没有人和你情投意合、畅叙衷肠了,而你已经过了交朋友的年龄了,你不想和任何人成为朋友。你的心老了,开始对任何新鲜事物都失去兴趣,也失去探索的欲望,世界变得陈旧无趣……这时候,您还会眷恋生命吗?”
大多数老人都对年轻时候的经历念念不忘,他也是如此。他的思维依旧敏捷,能轻松回忆起很多往事,尽管劲头上来时明显有些夸大的成分,但从程度上去讲并不属于欺骗。他讲述的故事内容很能吸引我,我全都相信。最后他指着远处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群山略显自豪地说道:“年轻时,我有胆量只身攀上那座最高的山峰并捧下来一块石头,为的是换来心仪的姑娘对我嫣然一笑。尽管我知道路途凶险,必然是九死一生。直到如今,我仍不知道当时的自己是勇敢还是鲁莽。”
拜别老人走出院子,我怔怔地望着远处的雪山良久,我知道那里寸草不生、阒无人迹,但却不能用“荒凉”二字去形容它们,那些山时刻展示着圣洁、高贵、雄壮的姿态,能释放出让人安静、深思和敬畏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绝非是我为了应景而杜撰出来的,我相信自己的奇妙感受应该有普遍性,山在这里作为信仰的载体而大多被冠以“神山”的称号,千百年来无人质疑它们的神圣性。这种感受也帮助我更好的理解了关于喇嘛们对山的固执崇拜和信仰。现代教育把我变成了坚定的无神论者,若非如此,我定然不相信那些山上没有神仙居住,或者说无论有人宣称在山上看到什么,我都相信。
正是因为如此,当晚我便决定第二天朝着大山深处进发——也就有了后来的遇险经历。毫无疑问我获救了,救我的是一个同样迷了路的旅行者,他发现我时我已气若游丝昏迷不醒——他也是从那个村子出发,一路上遇到的五条分叉路口,他与我做了同样的选择,这个巧合使他成了我的救命恩人。他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并不是急着找工作,而是出去旅行,见识一下大千世界。在当地医院,我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更幸运的是没有留下后遗症。至于我的身体为何会那么快速地垮掉,后来我才知道,我夜宿之地正处于一个断氧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