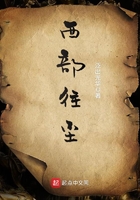西风烈!是个酒名,更是个噱头。
最近一段时间,每逢刘小乙返回塬地时,张涯便让他低价购置酒糟。除了蒸馏简易医用酒精,多余部分便蒸馏、净化、勾兑出一烈酒。
虽无法精确测定酒精度。
但凭口感而言,这玩意至少五十度!壮硕如徐平山、孟谷丰都经不住,何况是喝低度劣酒的文人。
绝对能让此少监爽歪歪!
手中白条都抖了出去,徐平山脸色瞬变急道:“西风烈?少东家,少东家!这酒、这酒太厉害……这些大官人能吃吗?”
“无妨,且如此吧。”张涯淡笑道。
他回返客厅,进门瞬间就眼晕起来。
秦翌半伏在茶几上,披头散发观看书卷,还手持银质发簪,在一旁划动着,好像在计算着什么。
主宾座上的林三福,双眼满是无奈之色,频频微幅摇头中,端在茶水放在嘴边,掩饰此时此刻的窘境。
其余四位宾客,也都神色游移,坐卧不安。见张涯进门,林三福急忙轻咳一声,示意旁若无人的秦翌。
与此同时,他起身招呼道:“唉!张宣奉辛苦,某等叨扰了……”
张涯上前数步,还未客套时,秦翌急速回身,一把拉住他。
“宣奉郎!宣奉郎!请留步。”
发簪急促点着书卷,秦翌脸颊微红,激动地说道,“贵师得道高人啊,卷中所述计量之言,愚收益良多,多谢教诲。只是……”
书卷所记之长度单位、面积单位、体积单位等等,都是数百年之后,经过人们数次更迭,淬炼出的精华。
受制于现有条件,张涯无法还原细节,定义之言满是漏洞。
但用来给宋人搞个精神冲击,他亦是有所肯定的。
只是秦翌的反应太大,出乎他的意料。此大宋技术官员欲言又止,貌似要请教什么,张涯只能不计前嫌,微笑淡然面对。
若是能折服其人,他所倡导的度量衡改革,才有可能更快推行出去。
“秦少监!莫要客套,在下无碍,有话当讲。”拱手示意林三福,张涯拉把椅子,在秦翌身旁坐下。
“张宣奉英气勃勃、大气非凡,日后必贵不可言……愚兄蠢笨,读懂寥寥,还望贤弟,不吝赐教!”
秦翌陪笑恭维起来,后指着书卷问道,“愚兄多处不解。其一,九陵水起坝之上游,降水量为何与库容不等?”
面对如此专业的问题,张涯心中便放下一半。从此旁证可得,秦翌的技术素养不错,倒是看懂、接受了新度量衡体系。
这已是一半之成功。
过于专业的知识,张涯也不甚了解。
譬如:江河流域内的年均径流量的核算;水土流失地区的泥沙计算;如何校核十年一遇、百年一遇之洪水……等等细节。
“秦少监!每次降雨大小不等。”
他斟酌片刻,徐徐说道,“只有大雨之时,才有汇水出现。换句话说,拦洪库容量,并不和降水量相等。”
“此言极对!不过,降水多少、汇水几何,怎么分布,贤弟规划之库容,又是如何计量、判定?”
“唉!其中之道深远无尽,需仁人志士,长年观察研判。”
专业细节要避重就轻,张涯转移焦点道,“先师曾言:他只知皮毛。此土坝及小水库,乃先师多年推演而来。”
“这个……如何推演,可否告知一二。”
“此事易尔!此地常年降水六十三厘米,八成降雨密集于盛夏,其中八成为急暴雨,估算其中两成汇水入河……”
听着张涯的解释,秦翌手中急速计算着。
未几,他瞪着迷糊的双眼,再次问道:“贤弟!莫要糊弄愚兄,如此计算之结果,不足以库容五成啊?”
“秦少监!核算库容之时,只是年均降水。”
张涯保持淡定,再次徐徐说道,“然则,偶有灾年,暴雨连天,须加避险库容,否则土坝溃决,后果不堪设想。”
“此法大善!请受愚兄一拜。”
秦翌越发恭维起来,之后再次问道,“土坝计画卷中所云:溢洪道,可否为更大洪水所备?”
“当是如此!天地之威,甚是难测。”
伸手按下秦翌,张涯严肃道,“此营造耗费甚多,若干年后,良田作物整齐,却大雨如注,土坝瞬间倾覆,必损失惨重,须小心谨慎。”
那个时代的工科男,都是差不多滴。
接下来,秦翌化身好奇宝宝,问题也越发深入,更涉及专业细节,张涯一时间亚历山大,只能避重就轻、左躲右闪。
就算如此,二人讨论之题,早已过于专业。
林三福迎来送往还成,对此两眼一抹黑,只能在一旁静静呆坐,看着侃侃而谈的张涯,眼神中越发钦佩。
其余四位宾客虽亦是技术官员,但都是城池房屋营造方面的,身份地位更低,对水力也不甚了解,默默然听个似懂非懂。
和秦翌谈论时间很长,精神更处于紧绷,张涯便忘记‘西风烈’之事。
等酒席布置上后,他看着这坛烈酒,一双眼皮急速跳动。
此时若撤下去,显然非常失礼。
“三福叔、秦少监……”
长长嘘出一口气,张涯保持淡然道,“除了购酒坊之大酒,在下还从薄酒中,提炼出一种新酒。贵客若是赏脸,当可品尝一二。”
“新酒!贤弟所炼?甚好、甚好!”
盘好发髻的秦翌,掀动鼻翼之中,满眼惊喜道,“愚兄乃是酒虫,此酒香气迫人,必痛饮三碗……祝小娘子,赶紧满上、满上!”
“秦少监!还是慢慢来。”
张涯暗中叹息着,只能略加提示到,“此酒名唤——西风烈,味道甚是爆烈,辛辣可冲鼻梁。”
他这个不喝酒的货,岂知酒中豪客之喜。
秦翌进士出身,还是技术宅,身体并不健壮,然则确是好酒之人。除了头一口被呛到,引发一连串的咳嗽。
之后,便是连喝一碗。
“西风烈?果真!清烈浓香,好酒哇!林书办,当需盛饮。”
重重的蹲下酒碗,此人扯松衣衫,毫无形象道,“哈哈哈!贤弟真是大才,单凭炼酒之道,若在京城售卖,当日进斗金。”
金色的油炸白条鱼,五十度的‘西风烈’,秦翌完全吃美了。
“少监过誉!”
张涯稍稍放心,笑着说道,“国法有云,私自卖酒,刑罪加身。在下岂能枉法,有空弄上几坛,招待贵客为上。”
酒过三巡。
秦翌微醺之中,拉住张涯,声音拔高道:“贤弟啊!一窍通则百窍通,咱们莫要小家子气,要建就建个大土坝!”
“大土坝?少监,你这……其中牵扯更多,还需从长计议。”张涯微微一怔,以为此人醉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