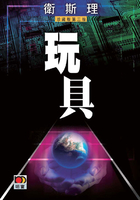他最担心鞋子。鞋子和粮食。永远都在担心没东西吃。他们在老旧的泥板烟熏房找到一条火腿,就着铁钩高高挂在角落,干皱、枯瘪,像坟里取出来的东西。他拿刀一切,里层是暗红带咸味的肉,味道丰厚美妙。当晚,他俩把火腿在火上煎,肥厚的好几片,之后再混上罐装青豆炖煮。其后,他在暗夜醒来,以为听见魆黑的山丘低处传来牛皮鼓声,然而仅有风在飘移,四周一片寂静。
梦里,面色惨白的新娘从绿叶茂密的树篷下向他走来,乳尖灰白,肋骨也敷着白漆。她穿薄纱礼服,黑发以象牙排梳和贝壳排梳盘起固定。她微笑着,双眼低垂。早晨又下起雪,成串的冰珠细小灰白,沿头顶的电线垂挂。
他梦见的,他并不相信。他说,涉险之人,当做涉险之梦,其余都属困倦与死亡的召唤。他睡得少,睡得浅。他梦见走在遍地开花的树林,有鸟在他俩眼前飞越,他和孩子眼前,天空蓝得刺眼,但他正学着自此等诱人的世界中将自己唤醒。仰躺黑夜里,不可思议的蜜桃滋味在口中逐渐散去,那桃来自幻见的果园。他想,若自己活得够久,眼下的世界终将全然颓落,像在初盲者寄居之地,一切都将缓缓从记忆中抹去。
但旅途中做的白日梦唤不醒。他的脚步沉重。他记得她的一切,却不记得她的气味。剧院里,她坐在他旁边,倾身向前听着音乐。黄金螺旋壁饰,墙上嵌着烛台,舞台两侧呈褶裥状的帘幕瘦高如圆柱。她握着他的手,搁在自己大腿上,他透过她夏季洋装的轻薄材质,感觉到了丝袜的袜头。定格这一刻。现在,尽管降下黑夜、降下寒天吧,我诅咒你。
他捡来两支旧扫把做成刷子,绑在购物车轮前,清理路上的残枝。然后,他让孩子坐进购物篮,自己像驾狗雪橇一样站上推车后端的横杆,两人滑行下山,学滑雪选手摆动身体,操控推车行进的路线。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见孩子笑。
山巅上,大路绕了个弯,画出一片路肩,有年头的小径向树林延展。他俩走上路肩,坐在长凳上眺望峡谷,谷中起伏的地势没入尘雾。山下有一片湖,冰冷,灰蒙,沉重,躺卧在郊区万物掏净的洼地里。
那是什么呀,爸爸?
那是大坝。
大坝做什么用?
造湖。盖大坝之前,下面本来是河。流过大坝的水推动一种叫涡轮机的大风扇,就能发电。
就能点灯。
对,能点灯。
我们可以下去看看吗?
我觉得太远了。
大坝会在那里很久吗?
会吧。大坝是水泥做的,应该会留存几百年,甚至几千年。
你觉得湖里有鱼吗?
没有,湖里什么也没有。
许久以前,他曾在距此不远处,看猎鹰循着绵长青蓝的山壁往下俯冲,挺直胸骨中线,攫走鹤群里位置最核心的一只。鹰带它飞降河畔,那鹤清瘦且伤残,鹰拖拽着它蓬松凌乱的毛羽,周遭是凝滞的秋日气息。
空中尘埃满布,张口一尝,滋味永难忘记。他俩先站着淋雨,像庄园里的牲畜,之后才披防雨布在蒙蒙细雨中前行。两双脚又湿又寒,两双鞋渐渐毁坏。长年固守山边的作物枯死、倾颓了,阴雨中,棱线上不结果的树木更显得裸秃、霉黑。
而梦竟如此多姿多彩,死神还能怎么向人召唤?冰冻晨光里醒来,万事瞬间成灰,状似尘封几世纪的上古壁画突地重见天日。
天放晴了,寒气消散,两人终于走进谷底开阔的低地。片片相连的农田依旧清晰可见,沿着荒废谷地向前,见到万物连根败坏。他俩顺柏油马路漫步前行,途经围有高高的护墙板的房屋,屋顶是机器锻压的金属。田野上有原木搭建的谷仓,屋顶斜面上有十英尺大的字,写着褪了色的广告标语:体验岩石城。
路旁的矮树篱都化成了连串枯黑曲折的干刺藤,了无生气。他让孩子持枪站在路中央,自己爬上石灰岩阶梯,走入农舍前廊,手护在眼旁遮蔽光线,探看窗户里边。他由厨房走进去,屋里垃圾、旧报纸随地乱丢,瓷器收在橱柜,茶杯挂在挂钩上。他穿过走廊,走到起居室门口。一架古董簧风琴安置一角,一部电视机,廉价的家具,还有一个古旧的手工樱桃木衣柜。他上楼巡视卧室,所见之物都挂着尘灰,儿童房有棉布小狗从窗台眺望庭院。他检视每一座衣橱,一一拉开床褥,最后拣了两条不错的羊毛毯,下楼。食物储藏柜有三罐自制的番茄罐头。他吹开瓶盖上的灰,细细查看,早他一步路过的人不敢轻易尝试,他最后也决定不冒这个险。他肩上挂着两条毛毯,走出农舍,两人重新上路。
在城郊路过超级市场,停车场上垃圾四散,还有几部旧车停在那里。他俩将购物车留在停车场,走进乱七八糟的过道。农产区的储物箱底有一把颇有年头的荷兰豆、一些看似杏的东西,早已干得像布满皱褶的雕刻。孩子跟在后面,他们推开后门走出去,在屋后巷道发现几部购物车,全都锈得厉害。两人又走回店里找其他推车,但一部也没找到。门边两部冷饮贩卖机翻倒在地,早被铁棍撬开,钱币四处散落灰土中。他坐下来,伸手往捣坏的贩卖机内部搜寻,在第二部机器里,触到了冰凉的金属柱体。他慢慢收回手,保持坐姿,看那罐可口可乐。
那是什么啊,爸爸?
好东西,给你的。
什么好东西?
来,坐这里。
他调松孩子的背包肩带,卸下背包,放在身后的地板上,拇指指甲伸进罐顶的铝制拉环,打开了饮料罐。他凑近鼻子感受罐底升起的气体的轻微撞击,然后递给孩子。尝尝看,他说。
孩子接过饮料罐。有泡泡,他说。
尝尝看。
他望向父亲,微微倾倒罐身喝了一口,坐着想了想,说:真的很不错。
是啊,还不错。
你也喝一点吧,爸爸。
你喝。
喝一点嘛。
他接过铝罐,啜饮一口,还了回去。你喝吧,我们在这坐一会儿。
因为我以后永远喝不到了,对不对?
永远是很长一段时间喔。
好吧,孩子说。
隔日黄昏,两人进城。州际公路交错,绵长的水泥路曲线衬着远处阴郁的天光,犹如废弃的巨型主题乐园。他拉开大衣拉链,枪系腰上,安在身体正面。风化干尸四处可见:皮肉脱骨,筋络干枯如绳,紧绷似弦,形体枯槁歪曲,仿若现代沼泽尸[1],脸色苍白像烧煮过的被单,齿色蜡黄惨淡。他们全打赤脚,犹如同个教派的朝圣团,鞋早被偷走了。
两人继续向前走。透过后视镜,他不断留意身后的动静,但飞扬的尘土是路上唯一的骚动。他们渡越高架的水泥桥,桥身横跨河面,桥下有码头,小游艇半陷在灰寒河水中,耸立的烟囱因煤灰而朦胧。
隔天,在城南几英里处的弯路,他俩在枯瘠的灌木林间有些迷路,遇上一幢老木屋,有烟囱、三角墙和一面石砖壁。男人停下脚步,推着购物车滑上车道。
这是哪里啊,爸爸?
这是我长大的地方。
孩子站着注视那房子。护墙板下半部剥落的部分多被拿去做了柴火,露出墙内的立柱和隔热材料,本是后门沿廊的磨损纱窗正横躺于水泥露台。
我们要进去吗?
为什么不进去?
我怕。
你不想看看我以前住的地方?
不想。
不会有事的。
说不定屋里有人。
我觉得没有。
要是有呢?
他站定,抬头望向三角墙内自己的旧房间,然后看着孩子:你要在这里等吗?
不要。你每次都这样。
我很抱歉。
我知道,可是你每次都这么说。
他们把背包放在露台上,在前廊的垃圾中踢开一条路,推门进了厨房。孩子抓着他的手。多半还是他记忆中的模样。房厅是空的,通往饭厅的小隔间里摆了一个空的铁床架、一张金属折叠桌,小巧的壁炉里还放着同样的铸铁制炉架。壁上的镶框消失了,余下框边痕积攒灰尘。他站着,拇指拂过壁炉台,沿漆过的木板触碰一个个裂孔。四十年前,他们在这板上扎图钉、挂圣诞袜。我小时候在这里过圣诞节。他转身望向庭院,院里荒芜一片,枯槁的紫丁香枝叶纠结,状似树篱连延。冬天寒冷的夜晚,要是有暴风雨造成停电,我们会坐在这儿,在炉火边,我跟我姐姐,在这儿做功课。孩子望着他,看幻影攫住他,而他并不自知。我们该走了,爸爸。好,男人说。但他并没有动身。
他们穿过饭厅,饭厅壁炉底的耐火砖颜色如新铺当日一样鲜黄,因为他母亲见不得地砖熏黑。雨水让地板变了形。有只小动物的骨骸在客厅里崩散了,落置成一堆,可能是猫。一只平底杯立在门边。孩子紧握住他的手。两人上楼,拐弯,步入廊道。地上一小团一小团积着发潮的灰泥,天花板里层的木条暴露出来。他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屋檐下的一方小空间。这是我以前睡觉的地方,我的床倚靠这面墙;千百个依童稚奇想织梦的夜,梦里呈露的世界或色彩缤纷或可怖骇人,没有一个像真实的世界。他推开衣橱,多少期待着发现儿时的物品。生冷的天光穿越房顶洒落,色泽与他的心同样灰蒙。
我们该走了,爸爸,可以走了吗?
可以,我们可以走了。
我怕。
我知道,对不起。
我真的很怕。
不要紧。我们不该进来的。
三晚后,在东方山脉的丘陵地,他在暗夜里醒来,听见有东西靠近。他仰躺着,双手摆放在身体两侧。地面颤动,那东西向他们逼近。
爸爸?爸爸?
嘘,不要紧。
怎么回事啊,爸爸?
它越靠越近,越近越响,万物同步颤抖。它像地下列车从他们身下经过,朝暗夜驶去,最后消失无踪。孩子紧依着他哭,小脑袋埋到他胸膛里。嘘,不要紧。
我好害怕。
我知道。没事的。过去了。
怎么回事啊,爸爸?
地震。过去了,没事的,嘘。
最初几年,道路上难民充塞,个个裹着层层衣物。他们戴着面具和护目镜,披挂着破布,坐在马路边,像受伤的飞行员。单轮推车堆满劣质品,人人拖拉着四轮车或购物车。头颅上,双眼闪亮。失却信念的躯壳沿公路蹒跚,犹如流徙蛮荒之地。万物弱点终被突显,古老而烦扰的争议消化为虚空与黑夜。最终一件保有尊严的情物就此毁灭,消解。顾盼四周,永远,是很长一段时间。然而他心里明白,孩子与他同样清楚:永远,是连一刻也不存续。
天色将晚,一栋废弃的屋子里,孩子还睡着,他坐在灰乎乎的窗边,就着灰茫的光线读一份旧报纸。诡异的新闻,不可思议的关怀:樱草花在晨间八点闭合。他看着孩子睡。做得到吗?那一刻来临时,你能不能做到?
他们蹲在路中间吃冷饭配冷豆子,都是几天前煮的,已经微微发酵。找不到能隐蔽生火的地点,夜里暗黑阴冷,他们在发臭的被褥下依偎着睡。他紧抱孩子,那么清瘦的身体。我的心肝,我的宝贝。然而他知道,即便自己能做称职的父亲,情势或仍如她所料:孩子,是存立于他与死神之间的全部。
岁末了,他几乎无法测知现下是哪个月份。他认为目前的存粮足供两人翻越山岭,但实际情况谁也无法确知。穿越分水岭的隘口长达五千英尺,届时势必非常寒冷。他说过,一旦进入沿海区,凡事迎刃而解,然而夜里醒来,他了悟这想法既空洞也不切实际。他俩很可能困死山中,这也许就是最后的结果。
穿越度假村废墟,走上南向的道路。沿坡,焚毁的林木绵延数英里,他没想到雪下得这么早。沿途不见人迹,四处不见生气,大火熏黑的熊形巨石兀立草木稀疏的山坡,他凝伫石桥上,其下流水低吟着汇入塘坳,缓缓地旋出一处灰蒙的水沫。他曾在这里看鳟鱼随水流摆动,循砾石河床追索鱼群的曼妙暗影。他们继续向前,孩子跟在他身后,艰难行进。他屈身倾向购物车,顺Z形山路迂回上坡。山区高处仍有篝火燃烧,深夜,煤灰落尘间透见深橘色火光。天越来越冷,他们生营火整夜漫烧,清早启程还在身后遗下未燃尽的火堆。他拿麻布袋包覆着两人的双脚,用软绳系紧。目前积雪仅有几英寸深,他心里明白,雪再积深,他们就得丢下购物车。眼下前行已不轻松,他经常停下脚步休息,艰难地走到路边,背对孩子,两手扶膝,弯腰咳嗽,起身后泪流满面,灰蒙雪地余留着幽微的血雾。
他俩倚附一方巨石扎营,他取杆子撑起防雨布,造了一棚避难所。生火后,两人拖过一大束断枝来支应当夜的柴火。他们捡枯死的铁杉枝铺在雪上,裹着毯子正对营火坐下,喝完最后一份几周前搜刮来的可可饮料。又下雪了,轻软的雪花自浓黑的夜色散落,他在舒适的暖意中迷糊着瞌睡,孩子怀抱柴火的身影盖在他身上,他注视着孩子喂养那火焰。神派的火龙,引点点星火向上飞冲,然后迫散于杳无星辰的夜空。临终遗言并非全真,一如此刻不踏实的幸福并不虚无。
清晨醒来,柴火已烧尽成炭。他走向大路,万物灿烂,仿若失落的阳光终回大地,染橘的雪地有微光闪烁。高处,山脊如火绒,森林大火映着暗郁的天色沿路漫烧,华美闪亮,犹如北极光。天寒如此,他却驻足良久,那色彩触动了他心中某个遗忘许久的东西。逐一记下,或诵经祝祷。记住这个时刻。
天更冷了,高地里万物静寂。大路上飘浮着燃烟的浓浓气息。他在雪地上推着购物车前进,一天数英里,无从得知山顶的距离。两人吃得俭省,因此无时不在挨饿。他停步眺望整片郊土,低远处有条河。他们究竟走了多远?
梦里她病了,由他来照护。梦的场景虽似献祭,他却有不同的诠释。他并未照料她,她在黑暗中孤独死去。再没有梦了,再没有清醒的时空,再没有故事可说。
在这条路上,再没有人言称上帝。那些人离开了,我留下了,整个世界被他们一并带走。疑问在于:“永不可能”和“从未发生”有什么不同?
暗黑隐匿了月。如今,夜微微抹淡魆黑;向晓,遭流放的太阳环地球运转,像忧伤的母亲手里捧着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