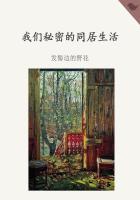离姜一副头疼的模样,“现在改还来得及么?”
“来不及了。”秦颜月挪移的看着他,思考了一会儿才慢悠悠的道:“或许……你可以试试‘巴结’一些士子、文人?!”
离姜深以为然的点点头,“我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那就先巴结巴结我家夫人吧!秦家秦将军嫡女呢!”说着就凑了上去。
京中已是风云迭起,江钦剿灭江匪归来,有人就要倒霉了。
“殿下,这江钦还真是有些本事,这么快就抓住了花家的把柄。”靳王下手位一白面书生笑了笑。
靳王皱了皱眉头,脸上的笑意都浅淡了一些,“他若办事妥当稳重一些,我会更高兴。”
虽他们已经抓住了花家的把柄,但他却知道这把柄来得太容易,分明是青州背后搅事之人松了手,这让他隐有不安。
此前,这人分明是与花家站在一边,与他们争锋相对,如今却突然放了手,怕是有后招等着他们。
“草民瞧着,殿下的担心是多余了。”白面书生笑了笑,这笑容看上去很假,说话也很不客气,“我的人查到青州背后的军师突然抽身离去,怕是与花家闹掰了。”
虽然他不曾知道那位与花家因何事闹翻,又是怎么闹翻的,但他的人传来的消息不会错,在背后支撑江匪的人不再做他们的靠山了。
靳王丝毫不在意他这轻慢的态度,习以为常的接着话,“花家那旁支虽行事糊涂些,却不至于此。”
花家是一根难啃的骨头,对下面的人自然也管束得紧,花家能让这一支旁系自由行事就是认可他们的能力,如此,就不会做出得罪靠山的糊涂事。
“殿下,这世上但凡有些才华、能力之人皆是有气性的,花家那旁支保不准是无意招了他脾气,才被他扔了。”白面书生对靳王的担心不以为意。
“先生那边得到了什么消息?”
既然他如此笃定,应该是得到了更准确的消息,才能如此放心。
白面书生勾着嘴角一笑,“得到了花家旁支急得团团转,却死死捂住的消息,那位在江钦抵达青州之前就离去了。”
若是做戏可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何况他对自己安插的人很有信心,不会误传消息。
“而且……殿下这算不算是多管闲事?”白面书生琉璃色的眼珠子一转,唇角的笑更大了一点儿,“江大人揭发了花家旁支之事,花家若计较起来也是他首当其冲,咱们跟着操什么心呢?”
“千灯楼这块肥肉本王不打算便宜了别人。”
江钦此人自然不值得他费这样的心思,但千灯楼就不同了,那可能是将来唯一能够与门阀世家相对抗的力量。
这股力量很重要,会成为将来稳固朝纲的关键,他不能允许千灯楼出事,所以他必须护着他,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为他扫除一切障碍,由他长成参天大树。
白面书生嗤笑一声,“所以才说殿下是多管闲事了,在其位谋其事,稳固朝纲是皇帝陛下的事情,殿下一个皇子,怎么就开始操皇帝的心了。”
靳王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脸色是少有的严肃,冷冷的看着她,沉声道:“慎言!本王只是想为父皇分忧。”
白面书生却好似没有看到他严肃的脸色,没有听到他带着低斥的话,自顾自的笑道:“草民劝殿下一句,离千灯楼远一些。”
靳王紧皱着眉头看着他,不满的道:“这话你以前就曾说过,我只当你忌惮边老先生,如今这又是为何?”
以前边老先生执掌千灯楼,父皇护着他,不允许他人染指千灯楼,他自然避其锋芒,如今边老先生已经仙逝,一个不成气候的江钦执掌着千灯楼,还有什么可忌惮的。
只要抓住了千灯楼就是抓住了洛国千万寒门士子,这在将来会成为他最重要的助力。
白面书生不答,琉璃色的眼眸在他脸上扫了一眼,还是那句话,“离千灯楼远一些于殿下而言是好事。”
见靳王面露不快,白面书生提醒道:“难道殿下以为,圣上会让殿下或者任何一个皇子染指千灯楼?”
千灯楼每年能为朝廷送多少人才,多么要紧!谁都能够看出来它对朝廷的作用,圣上哪里会让他人染指,架空自己,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儿么?
“上一次二哥闹出来那样的事情,父皇都没有插手!”
觊觎千灯楼的人不仅仅只有他,其他皇子也都在打它的主意。
半年前边老仙逝,黎王就已经试探过一次,那一次闹出了好大的风波,所有人都以为皇帝会出手,但最终皇帝却没有出手,只是坐山观虎斗,像是默许皇子们争夺千灯楼。
自此之后争斗千灯楼便成为了皇子心中皇帝给的考验,开始明目张胆的争夺,这也是他敢掺和争夺的原因。
白面书生皱了皱眉头,也很疑惑皇帝的行事,琉璃色的眼睛有片刻的迷惑,片刻后又清醒目光定在靳王身上,“此事在下也想不透,不过在下仍旧觉得殿下不该太过冒进。”
听了他这没根据的话,靳王最后的耐心都没有了,留下一句顾好你自己这个孤魂野鬼,便拂袖而去。
靳王身后,白面书生脸上的笑容消失,显出讥诮,许久才重复了一遍他的话,“孤魂野鬼……么?”他的声音低哑得像是说不出话来,满是苍凉又带着嘲笑,在这华贵的暖阁里头显的那么格格不入。
靳王这边为江钦操心,时时刻刻想要护着他,自然也有人为花家操心,想要在此事中保住花家旁支。
在江钦返回京中之前黎王就已经得知了消息,花家旁支也被召回来,这些日子一直被本家压在府中,并未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出来,倒是让花家少受了一些闲话。
黎王妃伴在黎王身边,听着自己父亲说着青州事情始末,慢慢喝茶。
“殿下,如今江钦已经将事情查明白,皇帝那里也知道了,这支旁支怕是保不得。”花父愁得脸上的褶子都深刻了些,但还是狠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