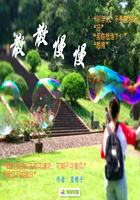建泽十五年的最后一天,楼故没有如往年一样,在长信宫参加除夕宫宴,也没有陪在齐王身边守岁,而是一个人在书房里,守着一根孤烛,枯坐了一夜。
第二日辰时以后,女使来书房服侍他梳洗。楼故才站了起来,活动了一下酸痛的双腿。
“太子和太子妃殿下呢?”他从女使手上接过漱口的青盐,随口问了一句。
“卯时刚解宵禁,两位殿下就走了。走的时候说不必惊动公子,小厮们便没来禀报。”
“夫人起了吗?”
“藏锋堂刚刚叫了人进去,夫人应该刚醒不久。”
楼故点点头,漱了口,让人给他重新梳拢了头发,就去了藏锋堂。
傅雨笙正在朝食,见他进来,慢慢起身,向楼故一拜:“妾见过郎君。郎君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我来找夫人商议些事情。”楼故走进屋内,在傅雨笙对面坐下,“都出去吧,这里不必伺候了。”
“诺。”
屋子里的女使都走了,傅雨笙也就不再拘礼,随意在原处坐下,自己拾起了木箸,为自己布菜:“阙陵君有什么事,要这样神神秘秘的?”
楼故盯着她看了半晌,手指在袖子里,慢慢摩挲着衣服上的布料,思索着该如何开口。
“你这样一直看着我,倒让人觉得阙陵君是……”傅雨笙说到这儿,顿了一下,冲着楼故轻笑,“动情了。”
楼故转开头,淡淡开口:“我眼睛还没瞎,你不必自作多情。我来找你是有别的事。”
“什么事?”
“你被人下毒的事,我已经查明了,是容姬下的手。”
“哦。”傅雨笙点点头。
“你不惊讶?”
“有什么好惊讶的?我的陪嫁都被阙陵君安排走了,藏锋堂便有了空子。而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善待过你的姬妾,这个时候自会有人想要落井下石。梁姬深居简出,是个谨慎之人,又从未与我有过恩怨,不会轻易动手。谢姬看似恶毒,实则心软单纯,又没什么心机城府,不会暗箭伤人。有理由下手,又能想出这种计策的,只有容姬。”
“夫人还真是好心机。该不会,连容姬会动手,都早在你的算计之中吧?”
傅雨笙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他的问题:“既然阙陵君已经查到了真凶是谁,是不是该给朕和西蜀一个交代了?”
交代?什么交代?如何交代?
自是要杀了容姬,向傅雨笙和西蜀的蜀王傅明煜谢罪。
“是容姬指使的不假,但替换木箸的女使曾受过谢姬恩惠,将毒带进府内的小厮也是谢姬的亲戚。容姬一开始,就打算杀了你,然后嫁祸给谢姬。”
“阙陵君想说什么?容姬怎么动手的我不感兴趣,也不想知道她想嫁祸谁。我只想知道,对于要下毒害我的容姬,阙陵君打算如何处置?”
“容宓儿不能死,我会把谢姬送到父王面前,并以谋害西蜀长公主的罪名,诛杀谢氏满门。”
傅雨笙大惊:“你疯了吗?谢氏是你的母族!”
“一个只会拖累我的母族,不要也罢。”
的确,谢氏出身低微,在朝堂上没有实权不说,还子孙不肖。楼故的几个表兄表弟,都是青都有名的纨绔子,整日里斗鸡走狗,打着楼故的旗号到处惹祸。
可即便如此,那也是他的血亲,是谢昭仪的父母兄弟啊。说灭满门就灭满门,这人的心,是铁石打的不成?
傅雨笙只觉得脊背发凉,看着楼故那张平静的脸,突然有些畏惧。
“既然连母族都可以牺牲,阙陵君又为什么要留下容姬?”她可不信,楼故会对什么人一往情深。
楼故盯着她的眼睛,说道:“她有了我的孩子。”
屋子里静了一霎。
“你说什么?”
“昨夜容姬在二门上吐血晕厥,婆子怕她出事,找了府里供养的府医为她诊脉,结果查出她已经有了近四个月的身孕。”
怪不得,怪不得她敢对主母下毒,原来是有恃无恐。
“所以,为了你的子嗣,谢氏可以牺牲,谋害我的人,你也可以轻易放过是吗?”傅雨笙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滋味,只是有种发苦的感觉。
“对不起,笙儿。我必须有一个儿子。”
是啊,她这个夫人常年服用避子汤,又能上哪儿去给他变个儿子出来呢?日后他夺了王位,自然要姬妾生的庶子来传承。
可是阙陵君府的后院里,谢姬出身谢氏,谢家要是又做了楼故世子的母族,只会变本加厉。梁姬为求自保,早给自己用了大量红花,绝了生育的能力。能生育世子的,只有容姬了。
“阙陵君不用说对不起,我心里明白的。”傅雨笙笑道,“还有,‘笙儿’这个称呼,从小只有我母后叫过,在妾心里,与母亲是一样的。请阙陵君以后不要再叫了。”
楼故垂眸,说了一声“好”。见她低头继续吃饭,没有丝毫想说话的意思,就站了起来:“该说的我都说完了,笙……夫人慢慢用膳,我不打扰了。”
他离开藏锋堂,又回到书房。将方延叫到了身边:“一个女子,听到另一个女人怀了她丈夫的孩子,还能若无其事地与她的丈夫说话饮茶,这是为什么?”
“公子?”
“方延,你说她究竟是怎么想的?”楼故无力地倚在柱子上,“昨夜我想了一宿,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容姬和她的孩子,我怕她会不高兴,又盼着她能不高兴。所以刚刚,我故意拿这事去试她。如果她不高兴我留下容姬,我便立马将容姬推出去。”
“可她说,她心里明白。”
方延站在旁边,一直听着。等楼故说完了,才开口问道:“公子早知道,元吉长公主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她嫁给公子也是别有用心的。臣也早劝过公子不要心软,可您一听说她中了毒,连吉礼都不参加了,直接跑了回来,还为她罚了容姬。公子,您又是怎么想的?”
楼故默了片刻,低声道:“方延你说,我会像楼政对顾鸣筝那样,心悦一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