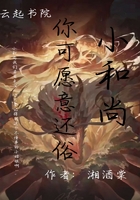魅翎和惑均下午外出后,就一直在大厅喝茶。
肖四和肖六去街上采买过天堑需要的绳索和马匹。他们带来的马匹不能带上天堑,万一被马匪抢去,马匹识归途,会暴露他们藏身的位子。
伍叔要了些瓜果,坐在砚冬的房间里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着砚冬修炼。
大约半个时辰,砚冬睁开眼睛。
“今日份的完成了?”伍叔随口问了句。
“完成了。”
“吃些甜瓜吧,苗疆别的不说,这瓜是真的甜。”伍叔将盘子推给砚冬。
砚冬下了床,捡了块甜瓜放进嘴里。
“确实甜。”
“你修炼的功法真的有用吗?”伍叔问。
“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是我离开寻香谷前,师祖给我的。说这个功法最主要的还是锻炼心智,分辨虚实。”砚冬回答,“我是着实不害怕那些真刀真枪的,但是那些迷惑人心的招式,稍有不慎,就会中招,我是有几分害怕的。”
伍叔知道砚冬之前的经历,倒也有几分理解。
砚冬第一次修炼这个功法的时候,差点崩溃。这个功法简单又粗暴,在半个时辰内,类似于心魔的考验,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幻境。他第一个就遇到了师父,浑身是血,朝他走过去,厉声问道,你为何要杀我,为何要背叛我!
他浑身发颤,连剑都拿不住,只能连连后退。
“肖四和肖六出去了,魅翎和惑均在做什么?”砚冬定定神,问。
“她们下午也出去了,肖四和肖六出门的时候已经回来了,一直在大厅里喝茶。”伍叔说,“这两个女人,从不摘面纱,浑身都透着诡异。”
“既然肖四和肖六他们敢雇佣她们,想来她们是值得信任的。我们多加小心就是了。”砚冬说。
伍叔觉得这样可行。
又一个时辰过去,肖四和肖六回来了,带了服饰回来。
“这是浸泡过药水的衣物,大家明日出发前换上,多少是一道保障。”
伍叔去督促大家换衣服了,肖四和肖六进了门,向砚冬讨口茶喝。
“你们倒是好兴致。”肖四喝完了一杯茶,尤觉得不解渴,“这儿可真热啊。”
“这儿的白天也比中原长。”肖六说,“在这儿可得小心些,据说苗疆人还会下蛊,有一种应声蛊,喊你一声你要是应了,就会被蛊虫寄生了。”
“这也太不可信了。”
“还有说,在这儿最好不要用真名,有人会施诅咒。”
砚冬虽然觉得有些耸人听闻了,但是还是捧场地说:“不如我们改个假名?”
“我觉得小兄弟这个主意不错。”肖四说“不过我们本来就没有名字,四、六只是因为排行,叫久了,也就这样叫了。”
“我觉得小兄弟你改一个吧?”肖六怂恿道。
“……”砚冬哭笑不得,只好说,“那就叫殊迟。”
“殊迟?”
“塞外征人殊未还,取殊,迟迟钟鼓初长夜,取迟。”砚冬笑着说,“随意取的,大概就是,等待的人迟迟未归的意思。”
“……兄弟好文化。”
三人开了一会儿玩笑,等伍叔回来,一道用了晚膳,就各自去休息了。
天亮之后,纸春换上那套苗疆的服饰。方知有选了一套浅紫色的,基本是纱制,配着面纱。纸春还是觉得,方知有眼光还是不错的。
方知有已经在门口等她了。两人一人一马,就离开了客栈。
正午时分在天堑不宜赶路。瘴气正是最毒的时候,所以一般过天堑的时候,都会选在清早出发,正午寻一处休息。
纸春刚走出客栈,砚冬就出来结帐。他心有所感的回头,见一男一女骑马离开的背影,女子穿着典型的苗疆女子的服饰,他又转回了头。
纸春和方知有一道出了边城。出了边城,大约半个时辰,就会进入天堑的范围。所谓天堑,不仅仅是山高,这一带降雨频繁,雨季天天下雨,天堑的石头松动,经过经常踩着碎石、极容易跌落山崖。这会儿雨季过了,积攒了一整个雨季的瘴气会开始散发,万一中了瘴气,没能及时施针,便会浑身溃烂而亡。更别说隐藏在草丛中伺机而动的毒蛇、毒虫了,不论哪种,都是有着剧毒。除了这些,天堑上还常年活动着马匪,打劫过往的商户。那些马匪也是有脾气的,有些商旅,往来十几年,从未遇见过,有些商户,几乎次次遇见,次次需要大出血。落月教曾经派人去剿匪,但是剿匪剿了几次,每次都连马匪的影儿都没见到。而那些见过马匪的商户,也都说不清马匪长什么样。
“你见过马匪吗?”纸春问方知有。
“没有见过。”方知有回答,“你那么厉害,不会怕吧?”
“呵。”纸春白了方知有一眼。
两人到了天堑边沿,下了马,牵着马前行。许是方知有那些浸泡过药汁的衣服起了作用,一路上,也并没有什么毒虫毒蛇来骚扰他们。两人轻功都不错,顺利上了山,进了平缓的地带。
这里的景观十分奇特,以正中一条河为界,一边生长着茂盛的林木,幽暗不见光,一边草木稀疏,以荒漠为主。
“这景观真奇怪,像是被人生生劈开了一样。”纸春感叹。
方知有说:“苗疆有传说,这里是被神仙劈开的。”
“神仙为什么要这样做?”
“据说是当地人不敬神,所以他恼怒了。”方知有说,“我只是听人说过,知道的不是很清楚。”
“当地人不敬神,那必定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值得被尊敬的事情。看来也不是什么好神仙呢。”纸春说。
“哦?姑娘的这番理论倒是让人新鲜。”方知有说,挑了挑眉。
纸春说:“人们会畏惧一切比自己强大的力量,这是人的本能。但是,要想人们信仰,那这个力量不仅要强大,也要会保护他人。”
“姑娘的意思是,强者要保护弱小?”
“不。”纸春说,“保护弱者不是强者的义务,而是情谊。”
两人说着话,在荒漠烈日下往前走。
“我们为何不走另一侧阴凉处。”
方知有说:“那一侧没人去过,这条河过不去。”
“水很深吗?”纸春看着有些岩石裸露在空气中。
“不深,”方知有说,“不过那边没人能上去。一直都是这样。有人靠近就会被弹回来。像这样。”方知有说着捡了块石头,往对岸扔去。
石头像是撞上了柔软的东西,又回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