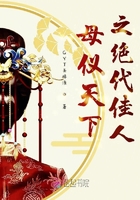更深露重,夜凉如水。
小楼下,却是一如既往的喧嚣如昨,只不过,这会子喧嚣中又夹杂着一丝宁静。
窗外,传来阵阵箫声,从与她房间窗户所对的另一座小楼上。
“你可识得这个曲子?”荼蘼紧紧地攥着手中的木雕,攥得有些咯咯直响。
“似曾相识。”
“当然,今日在望风崖,听到的就是这首曲子。”
“是他?”
忍冬直到现在才知道,今日藏在暗处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刚刚在后厨听到荼蘼与胡阎争执的那个人又是谁。
“寒山僧踪,寒山僧踪……”
“寒山……僧踪?”
“这个曲子,有一段唱词,你且来听听。”
看着忍冬的一脸不解,荼蘼想起了当年听到重华君吹奏这首曲子时同样茫然的自己,只可惜,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夜客访禅登峦峰,山间只一片雾朦胧,水月镜花,心念浮动,空不异色,色不异空。
回眸处灵犀不过一点通,天地有醍醐在其中,寒山鸣钟,声声苦乐皆随风,君莫要逐云追梦,拾得落红,叶叶来去都从容,君何须寻觅僧踪。”
“他……他这时候吹这个曲子,是什么意思?”
“他是在告诫我呢,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可不甚解,又如何得脱。”
荼蘼阖了阖眼,长舒了一口气,
“他和我不一样,他所循的,是拾得之道。
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
拾得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忍冬已紧紧皱起了眉,“那他倒还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嚯,怎么讲?”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不是菩萨,没那么慈悲,我只知道投我以桃,我必报之以琼瑶,投我以刀,我必还之以千万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债换债。”
“戾气有余,心念不足。”
“你不是也不认可他曲中之意么?”
“我?”
荼蘼轻笑,却并没有再去看她,
“我并非不认,而是不能。
纵然他自比拾得,我却不是寒山。
太迟了,停不下来了,像我这般,不人不鬼,不死不活,又岂是他能渡得了的?”
“这便是了。”
“是什么?”
“是我认定要追随的人。”
“你这丫头好生奇怪,不择善良明主,却要剑走偏锋。”
“明主是圣人,会原谅所有不公,我可不是,我跟着你,是要学有债必偿。”
“我欠你的债么?”
忍冬被她这样冷不丁地一问怔了一下,似是慎重思考了一会儿,她要对自己说的每一个字都完全负责,“没有。”
荼蘼叹了一口气,“真希望你的人能和你的眼神看起来一样诚实。”
“我是。”
荼蘼听过,已不再说什么,因为不论她再说什么,都只是多余,她不做无用的事。
箫声已然渐隐,随之而来的却是一阵风,带着清甜的花香吹开了窗子。
窗沿上,是一株新鲜采摘的荼蘼花,带着泥土的腥香。
她发现,自从对面小楼上住了人,她每天都会在这个地方收到同样的一株花。
荼蘼轻轻走过去,轻轻拾起了花,抬头就看到那个伫倚栏杆的萧瑟身影。
“你说,他是真瞎呢,还是装瞎呢?”
“大家都这么说,应该是真的了吧。”
“他要是真瞎,为什么站在窗外的时候,总是要抬头望着天上的明月,他能看到什么?”
听到荼蘼这样问,忍冬也忍不住好奇心走到窗边抬头望去,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竹叶青。
从前,都是只闻其音,只闻其名,却从不见其人。
然而不论是黄金屋,还是知鱼,从他们口中听到的这个人,都只有君子两字评价。
当时,她也一直都嗤之以鼻,这世上敢妄称君子的,本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直到,她看到了这个侧影。
“他可真好看。”
这话,是忍冬说的,她甚至不敢相信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
皎皎若高天之孤月,飘摇若回风之流雪,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难怪古人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现在她居然觉得,这曲寒山僧踪的告诫非但一点都不古板,而且听起来是这般的有道理。
原来长得好看的人,真的可以说什么都对。
可是她马上又意识到自己这话语的不合时宜,继而又搪塞道,“只可惜,是个瞎子。”
“不,他看得比我们清明。”荼蘼否认。
有时候,她也不得不承认,他比自己更清明。
好看么?
荼蘼也抬头细细地琢磨,不就是重华君的模样?
她从来不敢把重华君与好看这样的词联想到一起,他是不可品评的,不可论断的,不可亵渎的。
也许是那些年看得太过习惯,所以只有她才会全无意识。
忍冬突然注意到荼蘼手中握着的木雕,有些吃惊,“你雕的,居然是他?”
荼蘼也有些奇怪的将这木像举起来放到眼前,和小楼对面的那个人比对了一下,“像他?”
“至少九分像。”
“好像是比他消瘦了些。”
相比于重华君,竹叶青无疑是消瘦的,消瘦得更添几分憔悴。
重华君,比他生得更加伟岸,是她眼前心中永远都逾越不了的一座大山。
“不止如此,还多了一双眼睛。”忍冬看着木雕上的人,那双明眸里似是装着星辰大海,又怎么会是对面小楼上的那个盲公子呢?
荼靡不自觉地一声轻笑,她本想着刻一尊重华君的,只是多年不见,连记忆都有些模糊了,怎么刻着刻着,更像起了眼前人,“你说是他,那便是他吧。”
自从那天她在竹里馆匆匆溜走,就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人。
所以那个地方,她也从来都没有想过再去夜探第二次。
远处,竹叶青却突然转过身来,朝着窗户的方向点了点头。
忍冬有些惊慌,竟一时羞红了脸,她刚刚说的话,怕是这竹公子已然听到,“他看得见?”
“是风中有我们的味道。”
荼蘼却转过身去不再看他,走远了些,
“把窗子关起来。”
忍冬再回头时,刚想要再问什么,却看到荼蘼把手中的木刻人像捏成了两半,从头而断,遂也闭上了嘴。
她知道,她不该误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这个女人,从始至终都像她曾经探听的那般冷漠绝情。
“今夜,还要有的忙呢。”
“这么晚了,还有客人要来?”
“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三更天酒馆?”
“既在三更天打烊,也在三更天开张。”忍冬自是早已经打听得清楚明白,“那咱们现在要做些什么?”
“你去打一桶热水送到我房里来,现在,我只想好好地泡个澡。”
忍冬一阵皱眉,“就让我做这个?”
“怎么,让你打杂,委屈你了?”
“不是,我只是觉得……”
“年轻人初涉江湖,别的不会,就会空谈大话,口口声声还说什么要让酒馆的入账翻上一番,若是连人人都会的打杂你都干不了,我还能指望你学会什么?
我可不是黄金屋,不是什么女人在我面前脱个衣服就可以上位的,在我这儿,就得踏实下来,从最粗鄙的活计做起。”
“这个活儿,从前都是谁在做?”
荼蘼闻言只是笑笑,可忍冬却突然脸红了去。
她当然知道,在这个酒馆里常住的,就只有那三个大老爷们儿,而最有可能做这件事的人,她已想到了是谁。
“你想取代他么?”
“我这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