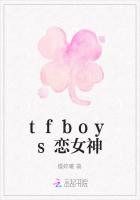长巷外,张子虚正朝着离一言堂越来越远地方向一路跑去,一刻不敢停歇。
掌柜的让他走,他就得马上走,他向来听话得要命。
可荼蘼只是让他走,却没有说走去哪,所以他也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三更天酒馆,这个让他能够安心的名字。
同样,也是能让所有人都安心的名字。
不论是谁,似乎只要进了酒馆里,就完完全全进入到一个外人永远无法沾染的圣地,那里是他们所有人的避风港,只要掌柜的还没有死,谁也不敢进去找死。
那里,是他们不必相约就可以相合的地方。
更何况,这次他要保护的,不止他自己,还有另一个人。
他的肩上,还扛着一个人。
香屏的腰横搭在他的左肩,整个人倒垂了下去,腿在前,头在后,当年荼蘼抓他上山时,也正是这样子单手扛着他。
他,学得惯了。
女人的呼吸温和而细腻,呵出来的气一直在他指间游走,像一池春水不断泛起涟漪,女人的裙摆还带着海棠花的清香,在他身侧若有若无地四散着,像涟漪下游走嬉戏的小鱼。
她睡得真沉。
张子虚也不由得加快了呼吸,可萦绕在他指尖这均匀的呼吸之间,似是有了什么微妙的变化。
他突然顿住了脚步,转头瞥了一眼肩上的女人,微笑着拈起她的襟口,又微笑着将她从肩上一把摔了出去,像丢抹布一样。
“你做什么?”
香屏扑倒在地上,不可思议地回头看着他,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明明刚才那个对他万分痴迷的男人怎么能这样在一夕之间就变得如此不懂得怜香惜玉。
“我才要问你做什么。”张子虚抻了抻自己的臂膀,扛着她时间久了,也的确有些酸麻了,歪着头看着地上的人儿,“你既然早就已经醒了,为什么还要装睡?”
“你一直都知道?”
“不敢不知道。”张子虚哂笑,“掌柜的说过,一个人最让你觉得放心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自己最危险的时候,这种时候,才要更加小心,而世上绝大多数自作聪明的人,都会栽在这里。”
“你这么听她的话。”
“是。”
“你要是真的相信她的这番话,那你就更不该相信她。”
“我当然相信她。”张子虚回答得很果决,完全没有丝毫的犹豫,仿佛这本就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除了她,我不会完全相信任何一个人。”
“她要你去死,你也死么?”
“是。”
这一次,他回答得更加肯定。
这根本就不该算作一个问题,她不会让他去死,永远都不会。
如果会的话,那他听话就是。
“你对她?”
“不,是她对我,恩重如山。”
“恩情,恩情,又是恩情,攥着这么多人的命,她不嫌沉么?”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还以为……”香屏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她以为自己早已经吃定了张子虚,却没曾想,她的戏只不过是张子虚配合了她的逢场作戏,“倒是我自作多情了。”
“你以为,我喜欢你?”张子虚倒是很大方也很乐意回答她的话,他从不遮掩,“当然,如果你还能像一个时辰前一样对我温柔一点的话,我还是会那么喜欢你。”
“登徒子。”
“哟,这么文绉绉的词儿我还真有点消受不起。”张子虚微微一笑,他还是觉得,被叫成兔崽子更好听一些。
香屏慢慢从地上站起身来,有些踉跄地转过身去,“你既然不信我,那你又何必救我呢。”
“不是我救的你。”张子虚上前一步拦住了她的去路,“你虽然中了毒,可眼睛却没瞎,应该看得很清楚,那致命一针是她替你挡下的,衣服也是她帮你穿好的,人是她托我带出来的,只因她想救你,我不得不跟着。”
香屏一把挣开了他的手,又朝着一言堂的方向往回走去,“那我就不用跟你道谢了。”
“我既然把你带了出来,就不会再让你回去。”
“是因为她不让我回去?”
“是。”
“人道是薄情寡义赤链郎,前些日子我还不信,今日一见,倒还真是名不虚传。”
张子虚的脸色突然泛起一阵殷红,这个名字,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听到过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莫忘了我这些日子都在哪,黄金屋知道的,我一样都不会少。”
“你不能再往前走了。”张子虚夺步挡在了她的前面,一字一句地说着,“那里的人,要你的命。”
他话说得很慢,所以很认真。
虽然这个女人和黄金屋究竟有什么恩怨他并不知道,可他却绝对看得出来,刚才金总管的确是往死里下杀手的,若非荼蘼出手阻拦,她早已必死无疑。
“我爹的命,还在他们手上。”
张子虚微微怔了一下,他想起来了,第一次见到香屏的时候,她就是去酒馆卖身替父还债的,“他还在一言堂?”
“不,他在千金赌坊。”
香屏冷笑一声,因为这实在是可笑。
他又去赌了。
是有人替他还好了债,无债一身轻的时候,想去翻本的。
这两个地方,当然有所不同。
在一言堂的,都是被讨债人冷着脸抓进去的,而在千金赌坊的,却是被同样的人笑眯眯请进去的,这世上从来没有人囚禁过他,只是他自己囚禁了自己。
张子虚不知道为什么已经跟着香屏走进了千金赌坊的大门,赌博是恶臭的,他一直是最讨厌这个地方的,就像讨厌黄金屋一样。
他讨厌赌,因为十赌九输,滥赌成瘾,只会毁人于无形。
他更讨厌黄金屋,因为黄金屋从来都不赌,一个深谙赌博之恶劣的人,却还是笑着将别人一把把往火坑里推,这样的人,比赌本身还要可恨十倍。
可他还是来了,他不放心,他要保证把掌柜的想救的那个人平平安安带回三更天。
千金赌坊里,安静得像个棺材铺。
方才大赦天下的盛景还没有过去几个时辰,可这里却已经冷清得不见一人。
金总管,也不在了。
这里只有吴老三,还在那仔细地擦拭着筛盅子,小心翼翼。
他是庄家,是赚钱的耙耙,然而却做着一个本该下人去做的事情。
这些骰子可是吃饭的家伙,光会用还不够,还得会护。
毕竟,像黄金屋这样精明的老板可绝不会多花一文钱去请一个专门负责清理打扫的小厮,而是把这些琐碎繁杂的事情都人尽其用,他的手下,也许一个人能够拿到两个人的工钱,可却一定还在做着三个人的活计。
“哟,今儿倒是邪了,有些人,偏偏喜欢在赌运旺的时候走,又赶在没盘口儿的时候来。”
吴老三眼都没有抬一下,毕竟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手里的家伙事儿。
“金算盘呢?”张子虚抢先一步问道,他实在想不通金算盘怎么可能不在这里。
“他在他应该在的地方。”
“应该?”
张子虚默默低下了头,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一言堂那个……”
“我是来找人的。”香屏四下张望了一圈,最后目光又落回到了吴老三的身上。
“姑娘又说笑了,赌坊里的自然都是赌鬼,又哪里来的人?”
“人活乱世终日形如炼狱,恶鬼横行倒是逍遥人间,人也好,鬼也罢,又有哪个是你这千金赌坊吃不下的?”
“这话倒是讲几分道理。”
吴老三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算这里是阴曹地府,在下怎么也能算是那牛头马面,想要找个人出来也是费不了多大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