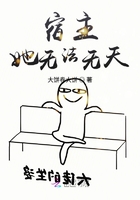“小荼蘼的礼,可从来都不轻啊。”
一旁的百无先生轻轻咳了两声,又抖了抖手中的烟袋子,
“老夫还记得上次做寿,你送来了一个奇巧匣子,匣子上是失传已久的八卦玲珑锁,到现在还没能破解开,也不知道匣子中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那个啊,我也不清楚呢,只是偶然得到,想着您老喜欢倒腾这些古物就送去了。也许啊,到了该打开的时候,它自然就能打开了,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也罢,老夫活了这把年纪,已经没什么事是不能等上一等的了。”
“您老人家的能等,可有些人的,却是万万等不得的。”荼蘼说话间,眼睛已经瞟向了黄金屋。
百无先生顺着她的方向望去,看到了谢乌有肩上的东西,嘬了两口烟,“倒还真是份厚礼。”
“您别说,这次的礼啊,它还真有个既古老又好听的名字。”
“你这小丫头片子,怎么总是爱卖关子,倒是说来听听,也让我们都长长见识。”
“我这个礼,叫做‘清君侧’。”
“这我怎么好像听不明白呢。”
“您老是老狐狸,当然听不明白了,只有我们这些俗人,才难得糊涂呢。”
“这样说来,我好像又有点明白了。”
荼蘼只是笑笑,不再理会,而是转头对谢乌有使了个眼色。
谢乌有将肩上的麻袋扔到了地上,只听细细碎碎一阵声响,麻袋中便探出了个被打肿的脑袋来。
这里面装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不见了踪影的李管家。
“这我们刚还说宅子里好像少了个人,原来是在你这儿装着呢。”
“哪儿能啊。”
荼蘼摆了摆手,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
“规矩我懂,不乱了章法。
要是黄大人自己个儿的家事,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哪里有咱们这些外人说话的份儿。
好巧不巧,大清早的时候嘴馋了城东家的糖饼铺子,便差了子虚去买两张糕饼过早,谁道不巧就碰到了个鬼祟东西。
子虚那孩子的小暴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抓起来不问是非就是一顿暴打,打完就扔城边上了。
后来跟我提了一嘴子,我再去一认,您猜怎么着?
这不是一言堂的宝贝疙瘩李管家么,哎哟喂,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给我吓了个好歹出来,这不赶忙的给您送了过来。
本想赔罪不是,又怕路人看见说三道四的不好解释,这才蒙头盖脸,却没想到刚进了门就听到满院子的人在找他。
再一打听啊,得,这回子赔罪也免了,算是权当礼物给送了吧。”
“你说早上?!”黄金屋的瞳孔突然收缩,好像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扭头便看向李管家,“你打早上起便一直在她那里?”
“我……我是被人算计的……”
再往后的话,黄金屋没有听进去,他确定的是,按照这几人的说法,他自天亮起回到江陵后,就应该再没见过李管家才是的。
那刚刚,他在院子里见到的李管家是谁,再早些时候,他天亮时刚回到宅子里见到的李管家又是谁?
一想到这里,他不觉得身上有些发冷,朝夕相处这么多年的人,他居然也没能够看出一点破绽,他已没有办法冷静下来去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耳畔,传来一阵清幽的箫声,余音袅袅,丝丝缠绕。
奇怪的是,但凡听过这箫声的人,都顿觉得心旷神怡,豁然开朗。
箫声,传到黄金屋的耳朵里,他突然觉得身上涌起了一股暖流,将方才的寒意尽数驱散,他已冷静了下来。
普庵咒,他自是识得,远方传来的这一曲便是普庵咒,此咒可普安十方,消灾解厄,是清心静气的曲子。
他看到,来的不仅有这不俗之音,更有那不速之客。
两个白衣女子翩然而至,一个袖映寒梅,一个发别兰簪,像是九重天上的仙子误入了凡尘。
佩兰的姑娘温文尔雅,举手投足间尽显清幽之气,绣梅的姑娘颖慧灵俏,一颦一笑间皆是万种风情。
她们却只是恭恭敬敬地对着黄金屋一拜,再拜,三拜。
“黄大人拜帖邀约,盛情难却,固所愿也,不敢请耳。只是我家主人旧疾在身,出行不便,只好遥遥聊奏一曲以谢知音,命梅兰侍婢二人前来拜谢。”
黄金屋侧目,以往这种时候,李管家总是在他身边做些应做的事,可这次,他却差点忘了。
他相信自己绝不会走了眼,也同样确认他从未认识这两位女子和她们的主人。
他,什么时候请过他们?
难道,又是那个莫名其妙多出来的李管家?
黄金屋虽有迟疑,却依旧回礼,他在女人的面前,向来都很客气。
“方闻一曲普庵,已是天籁之音,今观两位姑娘,一如天外飞仙,想必主人更是不凡之士,然遗憾不得相见,可否告知名姓,改日在下登门拜访?”
绣梅的女子凑到佩兰的女子耳旁小声嘀咕了起来,“兰姐姐,他在说什么?”
另一个女子小声地回着,“他呀,他说你是个女神仙。”
两个白衣女子相视一眼,突然鼻子一皱,没憋住笑了出来,又把这笑意强憋了回去。
黄金屋却也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只好跟着尴尬地笑了起来。
“神仙姐姐,住的莫不是神仙居么,所以不好告知我们这些俗人。”
佩兰女子敛起了笑容,又变成之前那清冷的模样,“那倒不至于,只是我家主人说,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汤汤川流,中有行舟。何必追名逐姓,不过天涯多情子,人间苦行客。”
“那究竟是旧时堂燕老客新知,还是淡然若水君子相惜?”
“萍水之交,素昧蒙面。人只道是不知茶舍,竹公子。”
“哦?”黄金屋细细地打量着她们,他在回想整个永安巷,甚至整个江陵城,“咱们这里,什么时候有了个不知茶舍?”
“今晚就有了。”
两个白衣女子又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像这周围的一切在她们眼里都异常的新鲜,这些人的问题也异常的奇怪。
荼蘼的胳膊肘轻轻怼了怼谢乌有,轻声凑到他耳旁,“死猫,你消息广,这个不知茶舍,是个什么路子?”
谢乌有眯起了双眼想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还记得咱们酒馆旁边那座空置的小楼么?”
“记得,说来也是晦气,去年我这酒馆刚开张,对面的铺子和旁边的铺子就不知怎的全都卷铺盖走了人,至今也没人接手,弄得别人还以为是咱这酒馆风水不好,煞了邻里。”
“近几日我看那小楼里边好像有人在折腾,对,那几个丫鬟跟这两个姑娘的装扮差不多。”
荼蘼轻轻咬着嘴唇,也开始有些不安起来,这本不是在她意料中的事情,“敢开在三更天的旁边,冲咱们来的?”
“不见得。”谢乌有捋了捋嘴边上卷翘的小胡子,“那家的主人我见过,是个瞎子,没什么打紧。”
“我看你才是个瞎子!”
荼蘼的语气突然严厉了起来,弄得谢乌有也猛地一个激灵醒了神,睁开了双眼,“怎……怎么讲?”
“你刚刚说,不知茶舍就在三更天酒馆的旁边?”
“是。”
“千金赌坊在永安巷首,三更天酒馆可在永安巷尾?”
“是。”
“永安巷有多长?”
谢乌有的眉头突然紧锁了起来,“我知道了,是我错了。”
“咱们在巷首,便能听到三里之外巷尾传来的箫声,你还觉得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打紧?”
“那明儿个我就去拜他个开张大吉,试试深浅。”
“不必。”她也望向了箫声传来的地方,轻攥着手心,“本分做生意的,咱们不去招惹,想找不自在的,老子等他上门。”
箫声已尽,白衣归去。
两个白衣女子一声告辞便已翩然而去,像她们来时一样匆忙而神秘。
观望的人意犹未尽,这才将目光从白衣女子的身上重新挪回了麻袋中的人。
有的人,还在等着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