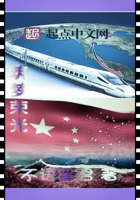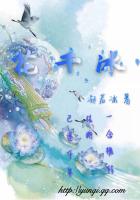屋外,依旧黑漆漆的一片,近处几户人家早早熄了蜡烛,远处只有一两家微弱的灯光闪烁着,似乎那是有炊烟的证明,可大多数人都面临着黑夜的翻来覆去。
沿着枣树那条石子路,路上蛙声一片,似乎想要冲破天际。我叩响了木门,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爷爷,饭我给你放门口了。”正当我准备起身离开时,“是逢春?进来吧。”
七年了,自从爷爷腿瘸后,他便把自己锁了起来,他把外界所有的一切都隔离了起来,这是他第一次邀请我进他屋,可与此同时,更多的不安与语塞涌上心头。
推开了门,一股浓重的潮湿烟草味向我袭来,其中还夹杂着痱子粉、中药、以及翻涌而上扑来的灰尘气味,空气冷冰冰的,一点人的气息也没有,黑红的柜子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本该透明的小窗户口灰蒙蒙的,蜘蛛结的网从柜子上延伸到桌下,在庸暗的照射下泛着银色的微光。
他坐在床榻上,用力咳嗽着,他瘦的像一张纸片儿,他黑色衣服上补满的花布丁把他的大肚子衬托的异常显眼,穿着一双发烂的草鞋,一头稀疏的白发。手里满是茧子,他努力打量着我,他那微微下陷的眼窝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那一刹那,我仿佛看到了我爸。
我站在了床榻前,那句“爷爷”不知道如何说出口。
他的茅草房空空荡荡,一张又臭又脏的毛毯上放着一个破枕头和发黄的烟草,毛毯旁放着一张已破出好几个洞的木桌,上边放着麻绳与中药,还有两只沾满了残渣的盘和一双又短又细的筷子。木桌右边有一大圈毛绳。门后挂着编制好的长绳,整个茅草屋就是这样一片寂静。
“长大了。”他几乎是颤动的嘴唇。
我用力点着头。
“没读书的日子难熬吧?”他似乎叹着气。接着他又问道:“还想去读书吗?”
“还好。是我自己不愿意读的。”我几乎是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
他没有说话,只见他艰难地起身往柜子那走去,我本想去扶住他的,但他好像没有要我帮忙的意愿,我便默默站在一旁。又露出那幅白痴一样怔怔的表情。
柜子发出令人厌恶的吱吱声,只见他摸索了好一会,才见他抱着一个绿到发亮的陶罐慢慢走到桌前,他一副骄傲轻松的表情:“给你。”
我看着陶罐,犹豫了几秒,陶罐盖子是木头塞包着白布做成的,木塞很难拔开,里面堆积了许多怨气,它们像在责备主人般发着脾气。最后,我用力转了几圈,木塞蹦的一声,那堆怨气遇到久违的空气也就都慌了神,四处逃窜着。我勾直了眼伸向罐子里,里面全是一分两分,一角两角的硬币,足足一罐子。
“这里有二十块,应该够你交学费的。”他又抽起了烟,烟雾在空气中腾起,弹落的烟灰看起来如此的寂寞。
“学费要两三百呢。”我拧紧了罐子。
“可你爸读书那会,学费才5元呐。”
“那都三十多年前了。”
“是啊,时间真快,那时候,我也不肯让你爸读书,还把他的书扔到屋瓦上,他跺着脚叫着骂着,说我像只老公鸡。”这时,他眼里有一道光,我知道他回忆起了以前的事情。
“听奶奶说,我应该姓章?”
他点了点头,“张,弓长张。”
“那为什么后来改姓了。”我急切的想知道。
“你坐。”他说道。
在这个充满黑暗、异味的屋子里,他向我讲述了自己。
四十六年前,我爹总是穿着西装坐在大堂,每日给我娘上香完后,便把双手背在身后,他出门前总和我说:
“臭小子,死后财产一分都不留给你!老是和我作对。”
你太爷爷是个体面人,那时,村里人都敬畏他三分,我经常惹他生气,其中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信不信我离家出走。我让你断子绝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