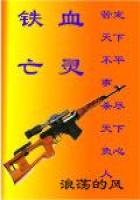女护士最终把话咽回了肚子里,呆呆的发愣了一会儿就到一边忙活去了。
陈域过来时果然看到何预整个人瘫睡在地板上,一旁的苑子安欲言又止,脸上满是惊愕,看到陈域眼睛一瞪蓦地用力推了何预一把,一双黑亮的大眼睛下挂着一道道泪痕,长长的睫毛颤动着,对着陈域呵斥道:“你们都是一路人,自明清高的小白脸!真是可笑!自以为是!”
陈域脸色一黑,说:“你什么意思?你们在干什么?”
苑子安忽而一笑,笑得拨凉拨凉的,露出一口整齐的大白牙:“还能干什么!推了他气了自己呗!”觉得自己十分可悲,十足是个笑话,真是小丑在演可笑可怜的剧本,接到了还一个劲儿地傻笑得意,自以为捡到了宝实际是个垃圾,以为是最好的,结婚反手给自己抹黑,深入到心脾的感情都是狗屁。苑子安猛地站起来,跌跌撞撞,不管不顾,心一狠,高仰着头,十足是个正在高歌跳舞的白天鹅,毫不留恋地走了。
“心真狠。”陈域扶起何预,眉头快揪成一团一座小山峰,说道:“还能走吗?你和她怎么了?我看她挺喜欢你的,是不是你说话太过分了?”他从苑子安进房门的那刻就看见何预的脸色如猪肝般青黑,似不喜欢苑子安的到来,现在俩人闹这么一出,让人家女孩子的脸面忘哪搁,他记得以前自己在学校谈恋爱的时候就被女朋友狠狠教训了一顿,说他对女孩子从来不留情面,情商特别低!为此他纠结了好一阵,直到和那个一笑就露出酒窝的女孩分手了。
“只是陈述了事实,我对感情的事不是特别开窍,就只交了一任女朋友而已!”何预挠挠头皮,心烦躁的很,试着慢慢走了几步,又来回蹦跶,低着头拍拍屁股后面的灰尘,道:“还好还好,看来我还能走动,刚才差点被她赌死。”
“怎么说?”
“正在气头上她差点我整个人打飞,我话都说不过她又被她真摔在地面上,没办法只好假装自己摔得骨架都散架起不来的那种。”
“演技不错!”
“呵呵!你来试试!”
“傻蛋!”陈域讥讽一句,恍觉如猴子被耍得团团转,佯装要走,何预嘴一扬,赔笑道:“不要生气嘛!我这是为她好,我对她没感情,答应了她就是害了人家姑娘,何况我……”何况他心里还留有萧潇一席之地,他希望看到萧潇幸福,但没法接受已分手的事实,他一直在试探痛苦的边缘挣扎,人都是贪心的,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失去的永远想夺回。他就是这么自私的一个人,一个不敢面对自己内心的男人!脚一迈,与陈域相反方向走,闹腾了这么久得去看何女士了。何女士依然是那副无精打采病恹恹的样子,以不变的躺姿待在病床上,脸色越来越差。
原本有着一头黑亮厚实头发,发量以肉眼看见的速度随住院天数渐渐变小,大有尼姑方向发展的趋势。而眼角的皱纹越发成粗深的沟壑,一道连着一道,凹进去的肉皮一层又一层。住院几天而已,她竟憔悴成这样了!和八九十岁的奶奶没什么外貌的区别。
“化疗不继续做了吗?”何预目光不移,透过反光的玻璃镜面瞥见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自己身后的陈域,视线开始游离涣散,“我妈……”话一出,又改口:“何女士……咳,我妈还能坚持多久?”
“你应该有个心里准备了。”不点明,但意思已足够清楚。陈域不忍心打破何预心中所支撑的幻想,“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你妈意愿,她想要什么希望看到什么,你应该清楚。”
“连你也要逼我吗?”何预语气变得生硬了起来,“这是我的家事,我自己会处理。原本以为你真是我小时的好朋友,现在……不尽然,你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更不知我能容忍的底线。知道我内心的渴求只有王南。”是的,只有王南会劝自己自私点,劝自己不要轻易原谅从几乎从生命中消失了的人!
“我没有强迫你必须接受自己弟弟的意思,更没有强制你原谅你的父亲。只是,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了这么久的母亲,连见一下亲人都不可以吗?或许可以给这个机会,我知道你从来没有怪过你妈,她从医院检查出来那天起,默默地,独自一人承受病痛,你懂!”
“你不要说了!”何预态度强硬,他原本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意思,只要何女士能安心养病,如今被陈域这么一挑明,他反而不想那么做了,他从来都是遵照何女士的方式去活,去做事,去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但现在,清醒了许多,他有些自己的判断。
“她好像醒了,我可以进去看她了吗?”
“可以。”何预出奇地平静,慢慢走了进去,他在等着何女士的答案。走进去,何女士目光在他身上锁定,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似要透光薄薄的眼角膜刺透他眼里藏不住的淡然。何预走过去帮何女士垫高了点枕头,让她好起身一点。何女士嘴一张脸颊露出一抹笑容,头靠在床头微微仰了起来,强撑着身体,摘了氧气罩,依然是一脸宠溺儿子的标志性笑容:“阿预……”说话吃力,语句断断续续了好几次,扫到何预嘴角没擦干的血渍,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担忧地问:“你……怎么……受伤了?”
“不小心擦破了。”试图轻描淡写地一掠而过,何预自然道,“我已经把一依送回了蓝二爷家,她很好,你不用担心!”定是刚才被苑子安巴掌一扬,给扇出血丝的!不在意的一擦,擦干了最后的那点血渍,径直走到了落地窗前,窗帘一拉,房内明亮了不少,又返回床边坐了下来,眼睛紧紧盯着何女士,目光柔和起来。陈域在门外站着觉得突兀,悄悄迈开小脚步走了。
“还是那么倔强!”何女士伸出一直颤抖着的手,枯瘦,如树皮的沟壑横生,慢慢地抚上何预的脸,一下一下摩擦着,目光爱怜,“我昏睡不醒的这几天是你在梦中呼唤我吗?”
“妈!”沉重的一声,何预顿时所有的委屈不甘示弱无助的情绪全涌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