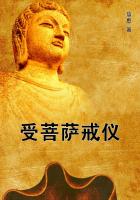楚娇娇皱着眉头,端坐在正殿里,下头跪了不少人,“皇上的事自有后宫的人料理,诸位大人不必忧心。我们当务之急必须处理好运河之事,否则雨水倒灌,这长安城就得淹死不少人。”
“难办,”楚和长叹,“这事不好处理。”
“娘娘,我们户部也难,这都是费钱的大事儿,春耕刚过,国库金银补贴不少,现已亏空,是在分身乏术难以支付拆迁的巨额费用,这是其一,”楚势弯腰作揖,回过身忧虑重重看着外头的雨,“户部也已经粗略估计了这笔帐,发现了几笔工部先前的旧账,实在蹊跷,正要上报,这是其二。至于其三,就在这望月楼底下其实有不少风月场所,都是各位朝中大人的相好住处,房子外头看破旧普通,里头可是别有洞天,拆了,只怕大人们不愿意。”
“你放屁。”首当其充的工部尚书,要不是看着皇后娘娘的面子,几乎就要破口大骂了,接着几名朝中有头有脸的大官也开始七嘴八舌的指着他,“你血口喷人。”
“胡说八道。”
“娘娘,你明察秋毫啊,这是陷害啊。”
楚娇娇本就一直缩在后宫,近期阴雨连绵,她病了好几场了,今日又战战兢兢,气血攻心,此时就是握着衣摆强撑在这里。此刻下头乱成一团,她更是头疼的厉害。
“吵什么,闹什么,娘娘不知道你们在外瞎搞的事吗?”左丞跺脚,上了年纪的人火气也大的很,伸出手,一个个指着骂,“皇上现在还躺在后头,你们都是朝中的老人了,能不能处理好这点小事?”
“娘娘,我有办法。”殿外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此人未到,声音倒是先他一步。
楚娇娇直起身,朝外看了一眼,既而重新回归正位。
她微微偏头抿了唇。
那心思是浸在心里的,面上只浮现了一点。
许晏和陈喜一同单膝下跪,双手握拳,向她行礼。方才两人急急入宫,也是刚刚换下湿透的衣服,此时面带倦容,平时刚毅勇猛的两人,此时身着青白官袍,倒是文弱的很,像是两个执笔的书生,而非战场上万夫莫敌的武士。
陈喜接着说,“圣上三年前曾为贵妃娘娘在长安祈福,大赦天下,这一赦免费了不少苛税杂费。长安周边不少小城都是连年丰收,国库虽然亏空,但不妨向这些富有乡绅借款买粮,日后再给予一定好处,他们未必不肯卖朝廷这么个大人请,官家与商家有个人情,是他们最想看见的结果。不如让管事的大人亲自书信一封,表示我们的诚意批下一批银子,正好用于现在的拆屋补贴。”
楚娇娇又四处环视了几个面色露难的大人,“只怕有些大人不满意。”
许晏侧头看了一眼陈喜,看陈喜虽是面色一顿,却并不有异,便说,“商家将这钱补出去就是莫大的恩情,此事由工部李大人去办最合适不过,再者说,皇后娘娘的娘家户部楚康大人经验丰富,人脉打点自然不错,他账算的清楚,钱就能到位。”
楚娇娇环视一圈,看大家都没有异议,便说,“便依两位大人所说的去办吧。”
陈喜头发还是潮的,裹在官帽里,濡湿了一片。
楚娇娇已经起身,走了几步,又停下身来,回头看了一眼,正对上许晏的目光。她的眼神又再次暗淡下去,喉咙已经漫上了腥甜的滋味。
陈喜依旧保持着跪着行礼的姿势,待她走远,才抬头。
小杏扶着她,慢慢走在那似乎没有尽头的长廊里,楚娇娇屏退了左右,只留着家中唯一带来的陪嫁丫头。
“娘娘,你脸上吹着了雨,我给你擦擦。”小杏小心翼翼地打量四周,用帕子拂了拂娘娘的眼帘。
楚娇娇嘴角含笑,倒是比刚才笑得更加开怀自然,“这雨可真是不通人情,居然一下就这么久,一吹就这么冷。小杏,我们回寝宫吧。”
许晏进了屋,正在思量着是何方的大人物一并招来了他和陈喜,按道理,他们中来一方就够了,如今一同盘于长安,天子又昏睡不醒,有理也说不清。
此刻内寝的灯已经燃了大半,星星点点就冒着一点火光,他摸着黑,就要歇息。
突然点起了一盏水璃煤油灯。
“皇叔。”小姑娘举着灯,奉上一碗汤水。
许晏起热的厉害,一碗姜汤下肚,居然舒服不少。他白日还好,其实静下心来反而身体沉得厉害。
这水怪的很,浸的人发昏。
月初用食指弯曲揉着许晏的头穴,她指间还攥着他的发,许晏极累的模样,一个恍惚就睡了下去,竟睡得十分平稳。月初将他扶在榻上,细细打量他,想起了许多事。
欲望是原罪。
薛先生说的。
月初将先生请来长安,实际上只是想再问一嘴。
这种欲望能破吗,但这后半句堵在喉咙里,她问不出口。
她想这个问题也许先生也答不上来,解铃还须系铃人。
她不想回宫,宫中人都想她走;她也不想回古兰,密密麻麻都是秘密身世;甚至她开始看不懂皇叔,他似乎有那么多说不出的事情藏在心里。
许晏救她回来,她就不再是个活死人了,月初想着,她终于可以活的像一个人,可以有喜怒哀乐,可以有人在乎。
还有属于她的感情,那份说不出,做不到的欲望。
心心念念放在心里,叫作许晏。
他与月初的世界完全不同,但他眼中偶尔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月初却感受的真切。这个世上能够不靠一言一语就明白这种感情的,其实只有月初,在他以皇叔的身份掀起帘子的时候,月初就了然了。
原来这么久以来,她都太害怕了,害怕到感觉不到害怕本身了。
直到许晏掀开了属于她的半分天地。
她想,你怎么来的这么迟啊。我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月初俯身用手尖指着许晏的眉心,后又下移到他的鼻尖,居然有些发烫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