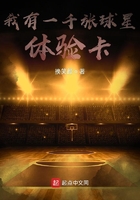俩个人刚走不久,朱淑真的父亲就带着人赶到了树林,一看没人,便返回去了,
林岳与朱淑真,大步流星地走了有七八个时辰,来到一个叫蒲城县的地方,俩人回过头望了望,一看后面没人追,这才安下心来。林岳给朱淑真擦了擦脸上的汗,很是疼惜地说道:“淑真,此行路途遥远,要是就这么走着,恐怕还得走几天,我怕你身体受不了,”朱淑真拉着林岳的手,微笑道:“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再苦再累也甘心。”林岳叹了口气说道:“哎,我怎么能忍心看你,跟我吃苦遭罪!”咱先不走,找个地方吃点饭再说。”
林岳带着朱淑真来到了蒲城街上,四下看看,还挺热闹,小县城不大,各种铺子却不少,人来人往的,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男女老少穿的整整洁洁,街头巷尾都是小孩的追逐嬉戏的笑声,街道又宽又干净,林岳仔细一瞧,两旁卖盐的居多,有人扛的,马拉的,还有不少挑着担子的,拿筐的拿筐,取口袋的取口袋,生意个个兴隆。
林岳与朱淑真,在一家盐铺旁边的饭馆坐了下来,本来已是下午时分,饭馆里的人却不见少,店里的伙计还挺忙乎,林岳要了两碗面,正吃着,就听饭馆里的人,一顿议论,有的说:“哎哟喂,这两月,赶上我十几年赚的银子了,”有的说:“可不是吗,不过这说来说去,还是这方国珍,为我们老百姓做主啊,要不这盐到了咱手里,还能赚几个大子儿。”店伙计,抹布往肩上一甩说道:“说的对,要不是方国珍,我们店里这生意那能这么火。”
林岳心中一惊,问道:“伙计,这方国珍是什么人?”伙计转过身来,看了看林岳回道:“这位客官是外乡人吧?要是本地人,不知道方国珍是谁的,恐怕真难找,就连大街上的小孩子,也都知道,这方国珍呀,原本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小时候到处乞讨打劫,也不知受什么高人指点,前几年回到海宁拉起一干人马,在海上管理来往的盐船,老百姓都受他的庇护,日子才好过一点。”
林岳筷子往桌子上,啪,一放,瞪着伙计问道:“你可知这方国珍现在哪里?”伙计吓了一跳,连忙行礼回道:“客,客官,据听方国珍在黄岩洋屿安了家,买了宅子,他是哪里也去啊,不过人们都传说就在两天前,他的小儿子,和小舅子一家,被岳阳城里,一个叫蔡柬的人给杀害了,方国珍定会去岳阳报仇,你若是想见他,就赶快前往岳阳。”
林岳手一拍桌子,啪,大声怒道:“国珍哥,你等着小弟,”店里的人吓的直往桌子下面躲,林岳拉起朱淑真就往外走,这时,店家在屋里说话了,:“小兄弟慢走,”林岳猛一回头问道:“什么人?”店家一掀门帘子,走了出来,只见此人,身高过丈,穿紫色细棉布衣,扎黑色金丝绣边腰带,黑发扎一抓髻,四方红脸,一字粗眉,眉心有颗黑痣,大眼睛,双眼皮,鼻头大,鼻梁低,瘪嘴薄唇,牙白如玉,一瞅就是忠厚老实之人。
店家向林岳使了个眼色,说道:“这位小兄弟,上次在我店里吃完饭没带钱,你忘了吗,瞧你这记性也不好,不信你进屋看看账本,你亲自记得,来,进来看看。”店家转身又回到屋里,林岳和朱淑真点点头,俩人随后跟了进去。
一进屋,店家就关上了房门,把林岳拽到书房,低声说道:“二位可认识方国珍?”林岳看了看店家,好奇地说道:“认识,他是我哥,怎么了?”那店家急忙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一封信,低声说道:“你若见了方国珍,告诉他,原定的起义时间,改为九月初八,一切计划都详细地写在这信中,务必亲手交给他,”说完店家把林岳拽到门口,把门帘揠了个缝,用手指着大厅北角的饭桌,悄悄说道:“你看角上那四人,是奸臣冤儁派来监视我的。你随我过来,我送你俩从后门出去,出了后门,不远处左边拐角,有间竹杆搭的马厩,里面有匹高头黑马,你俩骑马赶往岳阳,噢对了,那马叫黑旋风,你喊它名儿,就会听你的。”
说完,店家就急速从后门把林岳和朱淑真送了出去,转身又回到了店里,林岳和朱淑真出了后门,俩人到马厩骑上马,便飞驰而去。
到了岳阳,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林岳正准备要带着朱淑真回青林古洞,刚走不远,白鹤就迎了上来,拍打着翅膀,围着林岳和朱淑真转了好几圈,像一个小孩,日久没见亲人一样,高兴的不得了,朱淑真下了马,和白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只见白鹤眨巴眨巴眼睛,尽流出两行眼泪。
林岳看着心里不由得难受,他忙上前把朱淑真拉上了马,高兴地说道:“白鹤,咱们回家,”朱淑真此刻感到无比的幸福。林岳把朱淑真送回青林洞,里里外外收拾干净,又把朱淑真带到了,陈一发夫妇身前的卧室,面对真朱淑真说道:“从今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你就是这里的女主人,”朱淑真感动的流下了眼泪,爬到林岳的肩膀上说道:“只要有你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林岳牵着朱淑真的手,说道:“淑真,我带你去个地方,”说完把朱淑真带到了开满杜鹃花的山坡上,跪在花丛中,大声说道:“林岳愿意娶朱淑真为妻,今生今世永不反悔,”朱淑真噗通,跪在林岳的身旁,看着林岳说道:“朱淑真,愿意做林岳的妻子,今生今世,永不反悔!”俩人在花丛中紧紧地相拥着,几只鸟儿与蝴蝶,在他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互相追逐着,此情此景,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这时白鹤跑了过来,嘴巴朝林岳的后背啄了几下,呜哇一顿乱叫,把个朱淑真一下逗乐了,林岳眉毛一横,站起身来,左手指了指白鹤,咧着嘴叫道:“好你个白鹤,敢啄我,看我不打你。”林岳后门追,白鹤转着圈的跑,朱淑真一个劲捂着肚子笑。这也许是他们有生以来,过的最开心的日子!
嬉戏了一会,林岳带着朱淑真回到了洞里,俩盆连续几天,远途跋涉,太累了,就互相依偎在青石上睡着了。一直到天快黑时才醒来,林岳一睁眼猛地想起,店家托咐的事,忙起身说道:“哎呀,坏了,”朱淑真迷迷糊糊地问道:“怎么了?”林岳把朱淑真拉起来,一边去拿剑,一边说道:“淑真,你去床上睡,我骑马去岳阳城里看看,得把信送去。”朱淑真点了点头。上前给林岳把身上的衣服,收拾利索了,叮嘱道:“快去快回,我等着你,一定要小心,”林岳点点头,转身出去,骑着马赶往了岳阳城。
跑了有十几分钟,还没到岳阳城,突然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狂风呼啸,漫天飞舞的残枝落叶,拍打在脸上,犹如刀割一般。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林岳远远望去,就见城内火光冲天,嘶吼声夹杂着惨叫声,不绝于耳。林岳心中一惊,快马扬鞭,飞驰着向城内奔去。
当他来到城门下一看,尸横满地,血流成河,还有缺胳膊,断腿的,靠着城墙,挣扎着,喘息着,林岳下了马,一步步走进城内,眼前的一切,让他感觉到撕心裂肺般疼痛,城内已是一片废墟,地上,墙角下,犄角旮旯里,到处躺着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那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
林岳强忍着眼泪,转过身跃上马,立刻飞奔到喧闹的厮杀中,放眼一瞧,只见一左一右,两队人马,右边的人马穿红衣,胳膊扎黑布条,手持青一色的大砍刀,前面的大将身穿盔甲,手握金枪,脚下一双虎皮靴,坐下一匹黑色,赤血马,是面带杀气,红眼睛,红鼻子,血盆大口,眉毛胡子分不清那个是那个,身后一员随从,手里高举一面黄色大旗,大旗上写着一个字,蔡。
再往左边看,一队人马是老的老小的小,残的残,身穿黑色粗布衣,胳膊上系白色布条,有的穿鞋,还有的光脚。有拿剑的,提刀的,举枪的,还有握着长棍的。前面一员大将,身高过丈,虎背熊腰,青袍裹身,手拎一把九齿八环麒麟刀,紫色西布包头,黑脸,粗眉,大眼睛,大嘴,大鼻子,坐下一匹白色玉锦马,身后随从高举一面红布黑字旗,上写着,方。
林岳催马上前,大叫一声:“国珍哥,”那骑白马的大将,回过头,细细打量一番,大声问道:“你是何人?”林岳跳下马,单腿跪地,行礼道:“岳阳,青林山洞,林岳,国珍哥当真不记得了吗?”方国珍跳下马,走上前去,握着林岳的胳膊,叫道:“兄弟,是你吗?我是不是眼花了?”林岳站起身,看着方国珍,眼含热泪,轻声回道:“哥,是我,我是林岳,”方国珍揪起袖子,揉揉眼睛,面对着林岳,看了又看,激动道:“好兄弟,长大了,哥哥都快认不出你了。”
俩人正说着,对面的大将嘶吼道:“方国珍,小儿,怎么,打不过商量着逃跑啊,也行,留下你的人头。”说是迟那是快,那大将把马缰一勒,那赤血马前腿一跃,朝着方国珍跳了过来,方国珍一把将林岳推开,一个旋风腿从马下扫了过去,赤血马当场倒地,方国珍身子挺,大声喊道:“蔡柬小儿,拿命来,说着提起刀,直对着蔡柬的脑袋砍了下去,”蔡柬一个金蝉脱壳,从刀下转了出去,刚刚停息片刻的厮杀声和哀鸣声,刹那间又震耳欲聋。
林岳看着脚下,一个个狰狞的残体,和恐怖的场面,心痛至极。他跃上马背,双手使劲将马缰提起,横跃到了方国珍面前,大声叫道:“哥哥块停手,”方国珍往后一退,大声回道:“兄弟你幼稚啊,你以为我舍得我那,同风雨同患难的弟兄吗,你往上面看。”
林岳抬头一看,只见四周城墙都挂着笼子,里面全都是老弱妇孺,哭的哭,叫的叫,有的已经被折磨的不成样子,惨不忍睹,方国珍忍泪怒道:“兄弟啊,那城墙上挂着的,都是将士们的,家人和孩子,还你的侄子,景儿!”
林岳倒吸一口凉气,大声怒道:“哥哥,你为何不早说?”方国珍擦擦眼泪,指着蔡柬怒道:“就是那卑鄙无耻的小人,为了自己能升官发财,视人命如草芥,你可看到城里的老百姓,都被他当作盾,堵了枪口,兄弟呀,哥哥若不杀了他,天理何在!”林岳痛心道:“哥哥,你可知这所有的将士,都是爹生娘养的,家中都有妻儿老小,他们身为将士,有令不得不从,横竖都难逃一死,他们能不与你拼命吗,你再回头看看,你看看他们,有的都手无缚鸡之力,不是白白送死吗,哥哥若相信我林岳,听我一言,先退出城去,咱们再行商量。”
方国珍摇摇头,看了看林岳叹道:“兄弟呀,恕哥哥难以从命,”话刚落地,举起麒麟刀就要往上冲,林岳跳下马,噗通跪在了方国珍马下,双手握拳,大声劝道:“哥哥若不听林岳劝告,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对面蔡柬的哪些人马,都看的是清清楚楚,听的也是明明白白,都掉下了眼泪。
方国珍咬着呀,勒住马缰,低头看着林岳说道:“兄弟,你让哥哥如何是好,你看看城门上,你看看你侄儿,我……我……哎……”林岳想了想,灵机一动,站起身来,靠近方国珍,低声说道:“哥哥,我有妙计,咱不动一兵一卒,定将那蔡柬活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