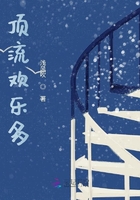清晨的曙光正在悄然显现,在那群山万壑的山垣上,一抹旭阳已经从那波峦相聚的山底挣出,化为千万丝线洒布在那片天空上,将昏暗幽禁的夜色照的支离破碎。
“天就要亮了!”
褪去了燥热的清风袭来,化作万千温凉的手掌,抚慰着这片满遭怆热的土地。风中似乎还能隐隐地察觉到水分的存在,这大概是哪片慷慨的水乡对这沙漠弃儿突发奇想的馈赠。
沙漠中许多未曾见过的虫豸呜呜呼呼地叫了起来,呼朋唤友,倾巢而出,携手相围,踏沙起舞。仙人掌吭哧吭哧地抻长着身子,拉展着尖刺,以便更多地吸收这风中的水分。枯干吱吱地响着,以一种阒灭中带着温灵的声音,表达着自己的喜悦。这大概是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遗愿,将身体多年的残念化作的本能激发了出来。“风动乐起尘沙寂,霞吐山光应有声”,沙漠中的早晨确实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趣味,它不同于水乡江南的那种烂漫、灵润与翠鸣,而有一种万物同寂归的浩瀚,一切事物中都篆刻着生命与挣扎。
不管是舞蹈中的行足踏步也好,歌声中的狂抑悲嚎也罢,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旋律,也是生命的哀歌。
这个早上的没毛鸡一群人却事事缠心、手忙脚乱,根本无暇顾及这沙漠中的微妙变化。
没毛鸡将那小家伙扒的干干净净,拎着他的一条腿将他提在空中,瞪大了双眼,不断地在小家伙身上摸索着什么。在没毛鸡摸索的过程中,小家伙一直在呼呼睡着,鼻子时不时地吹出一个小鼻涕泡。而蛮古天、大红鸡等人则正拿着一种蓝色的药膏给那个驼族人喂,由于药膏粘稠,再加上驼族人的嘴像一个倒放的漏斗,他们两个忙活了半天都没喂进去,而四长老则一如既往地躺在一旁,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他身子下多了一浮床榻。
大红鸡猛拍了蛮古天一下,道:“我有办法了!”
按照以往,在大红鸡这一掌之下蛮古天定要打好几个趔趄,但这次他的身体却稳若磐石,岿然不动。只见他面色红润,气血贯虹地问道:“什么办法?”
“打”,大红鸡兴致冲冲地回答,在此情此景下,她根本就没察觉到蛮古天的异常,或许就连蛮古天自己也没发现这件事。
蛮古天将药膏拧成锥状,将锥尖塞到驼族人嘴里,并用手扶着它。做完后,他将目光扫向大红鸡。
只见她双手合聚,猛喝一声向驼族人腹部砸去,驼族人身体颤了颤,浑身冒汗,直接晕死过去。但在如此强度的振动下,锥尖也往下溜了一小部分,见此,大红鸡直呼道:“好,这个办法有用”,说完她就咣咣地砸了起来。
但就在她砸的兴致昂昂时,蛮古天却伸手拦住了她。
“你干什么?”,她有些不快地说道。
蛮古天指了指那个驼族人,只见他已双眼翻白,从锥尖的缝隙中溢出白沫来……。
他们俩大呼起没毛鸡来,而没毛鸡则是头也不抬地问道:“怎么了?”
他俩急忙说清原委。
只听见没毛鸡淡淡地说道:“哦?可是那药是外敷的呀!内食的蝎尾我早就已经给他喂过了。”
“……”,两人一阵沉默。
在一番搜寻无果之后,没毛鸡心里愈发着急,脑袋愈发涨裂,下手愈发粗暴,惊醒了在睡梦中的小家伙,他一醒来便开始号嚎大哭。
这时,太阳已经微微升起,驱散了晨曦时的凉风,空气又重新干燥起来,那一片炽热的沙漠又再次回到众人眼前。
风声、沙声、众人的嘈杂声、沙味、血味、空气中的药香味夹杂着婴儿的哭叫声一同在没毛鸡的脑海中响了起来,这一切就如同一把把不断撩拨神经的尖刀,在没毛鸡脑袋中横冲直斩,削切刨剜,又如同一个个蒲牢大鼓,震得没毛鸡头晕目眩、眼冒金星。他咬破了自己的舌尖,希望能够以疼痛让自己得到暂时的清醒,但这是徒劳的,一股深深的乏力感正从他脑海深处传来,他双腿发软、脚步虚浮,很快就失去了意识,躺到地上。
在他彻底丧失意识之前,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大红鸡的呼叫声。
是啊!他本就是重伤之身呀!
当没毛鸡清醒过来时,他发现所有人都围着他——包括四长老,他正在舔着自己的脚趾头……大红鸡则一脸担心地看着他,握着他的手,因为两只手长久握攥在一起,没毛鸡感到自己的手心湿答答的。他不动声色地抽回自己的手,扭过头去发现了蛮古天,这老家伙也是哀愁满面,不过他面色红润、精神饱满,哭就像笑似的……
见此一幕,他甚至觉得自己要是一睡不醒也挺好……
待其稍稍恢复,定了定神,问道:“那人怎么样了?”
“哦,大人,我刚准备向你汇报,他醒过来了,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与他之间存在语言障碍,交流不通。”
没毛鸡摇了摇头,道:“无妨,我会讲驼族话,扶我下去吧!”
蛮古天皱了皱眉,道:“你的身体?要不我唤他前来?”
“不,虽说驼族多为禀善之辈,但我们与他并不熟识。现在我在病榻之上,万一他见财起意,突起歹心,这不可不防。同时,既然我们有求于人,更需亲自拜访,不可懈怠。”
“是!”
那驼族人见没毛鸡一行人前来,微微点头,以表示自己的谢意。虽然他们之间无法交流,但那个驼族人也不是傻子,通过前因后果来看,对面那一群人正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没毛鸡看向对方,将自己的双臂交叉,放在两边肩头上,双膝内扣相抵,弯腰道:“鲁西达。”
见此,那个驼族人眼光发亮,急忙站起来,向前走了一步,用驼语问道:“朋友,这是驼族最为古老的问候礼,你是怎么知道它的?”
没毛鸡笑了笑,回道:“朋友,现在我们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还没报答我们的恩情就开始盘问我了,这不属于驼族人的待客之道,也对不起阿古拉。”
听此,那个驼族人正了正身子,脸色严肃起来,只见他将十指环扣,高高举过头顶,一腿弯曲,另一条腿高高跃起,待着地时这条腿回缩,直接半膝破沙入地,喊道:“阿古拉!”
这是驼族最为尊敬的问候礼,以驼族之神阿古拉起誓,非有救命之恩不可发。伸展的双臂代表着驼族人最为崇尚的自由,以举过头顶来表示祝福对方超出世俗,畅游于天地之间。同时,沙子代表对自由的枷锁,以双膝入沙表示自己甘愿被束缚,以便于对方得到真正的解脱,这是驼族最为至高无上的祝福!
这驼族人就这样在沙漠中直直地挺立着,高高地抬起头,眼睛盯着没毛鸡。
没毛鸡急忙上前将这个驼族人扶起,道:“米库土。”
听此,这驼族人才站起来了,笑着说:“布谷什。”
二人双目对视,仰头畅笑。
……
二人促膝欢谈,那驼族人也交代了他的姓名,他叫驼逸。
在交谈中,没毛鸡表示,当年北漠驼族族长驼巽曾邀请自己做供奉长老,不过自己当时有急事,便拒绝了。说完,他感叹道:“驼巽族长与我真是相见畅欢呀!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他。”
“您恐怕见不到了”,驼逸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哀伤。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驼逸略带惊讶地望着他,道:“您不知道?”
没毛鸡摇了摇头。
驼逸咬了咬牙,满脸怒容,道:“北漠灭族了!”
“什么?怎么回事?”,没毛鸡惊讶地站了起来。
“五十年前,北漠横遭杀害,举族灭亡”,驼逸停了一下,又从嘴里吐出四个字:“无人生还!”
“怎么会这样?”
驼逸摇了摇头,道:“北漠在一夜之间凭空死亡,或者可以说凭空消失,原因根本没有人知道。”
“消失?”
“不错,正是消失,据说在事发当天北漠的街道还是嬉闹喧嚷,人声鼎沸,但到第二天那里却全然人寂楼空、全无生机。并且案发当晚,临近的人没有听到一点动静,一丝吵闹。”
没毛鸡皱着眉说道:事发必有因,驼族虽弱,但与其它势力并无矛盾,何仇何恨乃至于灭族之境?况北漠地处荒漠,一无金钱,二无资源,谁又会干这件出力又不讨好的事呢?”
空气中一阵沉默。
过了一会,驼逸继续张口说道:“北漠灭族后,西尘驼族为了自身的安全拒绝与我们交往,他们将自己封闭在函空城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成了狗,成了奴隶”,驼逸咬牙切齿地说道。
没毛鸡眨了眨眼,道:“这么说,你们是——”
“我们是东亘驼族。”
“朋友,我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
“什么事,但说无妨。”
“我想请朋友帮我们走出这片沙漠。”
“你们迷路了?”
没毛鸡有些涨红了脸,道:“是的。”
“现在距我昏迷过了几日?”
“一日,现在是第二天!”
“朋友,不必担心,这次我因有事便超过了驼队一天的路程,按时间来算,想必他们今天下午定会到达此地,到时候,你跟着我们的驼队一定能离开沙漠!”
没毛鸡道:“布谷什,朋友。”
就在这一望无垠的茫茫沙漠之上,丘垣相继浮现,在极目远眺之下,起伏的沙漠极具美感,每一爿沙纹弧线,它比女子的腰肢更妖娆,更具诱惑力,更能使得人性中的狂野得到充足的释放。每一弯沙谷峰崖,它比女子的双峦更加挺傲,更加险峻,更加具有曲线美,它又如一泓深不见底的清泉,将你的目光深深地吸入泉底,使你在其中陶醉,使你在其中沉迷。
没毛鸡等人就在那里等着,待到日光向西山露出第一缕温情时,在那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开始看见第一个黑影,再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他们成群结队地从西边行来,骑着沙驼,唱着那遥远的、古老的、悠久的自由之音:
哟~逸乎群乎,
景与驼。
心自实安不妄夺。
坼传寒,漠扬风,
彼子赳赳。
天似穹盖地为炉。
身得其中哪自由?
路遥遥,铃潇潇,
疏狂放浪藐朝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