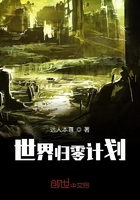光,闪闪,浮动,掠动,淡金的,淡银的。
迷迷中,我感觉我的手指似乎动了一下,随后是头部剧烈的撕痛,在剧痛中,我慢慢恢复了意识。
不远处是连绵的雪山,在暖阳里泛着金光。山底下隐约有条亮而大的带子,大抵是湖。湖边全是密密麻麻的小花,类似格桑。花海延续到这,已稀疏了不少。
我挪动到一块大卵石边,扶着它瘫坐起来,不住地揉着太阳穴。说不出是疲倦还是轻松,我缓了缓神,暗自纳罕,我还没死呢。想想又不对,叹口气言,又或是在天堂了。
迷迷糊糊走了一天,我的白裙底已被挂在草尖上的晚雾珠打湿。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处。但一想到自己连死也许都经历过了,走走又何妨呢。
况且,这里简直是个仙境,花草鲜美,落英缤纷。
我爱看美景。
也许,我真的走到了桃花源境,毕竟,前面正是一片桃林。桃林深处,似乎有人家,几处屋脚在桃花枝下露了出来。
我不禁欣喜,狂也似的朝前奔去。越近,房子的样貌越清晰。渐渐的,我的脚步迟疑了。
那似乎是白家酒庄。
那个噩梦缭绕的地方。
母亲因生我难产而死。父亲悲痛万分,为纪念母亲,用了母亲的瞿姓给我作名。我因此得白蕖这个姓名。
父亲作为酒庄当家人,整日忙的焦头烂额,但他仍是用父爱弥补了母爱,用生命弥补了父爱,给了我一个完满的童年。
可是自从叔叔从国外留学回来,提出要全权继承酒庄开始,一切都变了。
庄丁们不同意叔叔全权继承酒庄,因为酒庄是爷爷死后父亲全力撑起来的,连叔叔海外留学的钱都是父亲一手供应的,他们认为叔叔没有这个资格和能耐来继承酒庄。而父亲日夜忙于生意,又是夹在两头之间,也始终做不出决定。
几个月后,父亲死了。
他到死都不知道,是他一手供起的亲弟弟雇人开车把自己撞死的。
我也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平日里温和有礼的叔叔竟是这样的残暴自私。为了确保酒庄的财产归入自己囊中,他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为了斩除后患,又威胁他的女儿,我的堂妹妹白芜,把我骗到月光崖,推入崖下的月光湖。
我一向反应快,在白芜推我的时候反手抓住了她的手腕。她被我拽倒,惊愕下,她用另一只手勾住了崖边凸起的尖石。而我,已悬在半空。
我的喉咙被这突如其来的背叛堵住了,说不出话了,只能泪光莹莹,满目怨恨的瞪着她。
可她却崩溃的大哭起来,说自己也多么想和我跳下去。他那残酷的父亲,拿他母亲的性命来威胁她,要她杀死她的亲堂姐。她多少次看到父亲在没外人的时候凶相毕露,打得母亲面目全非。
她说她要长大,要保护母亲,她还不能死。
她最终说出了我父亲的死的真相。
我沉思了。我的堂妹妹,她还有母亲要保护,而我呢,我在这世间大概什么也没有了。没了母亲,没了父亲,叔叔背叛,婶婶无能,堂妹无助。我到底还剩下些什么呢。
万念俱灰下,我的手渐渐松开了。我仰头看看月,饮下已涌出喉间的血,滴下眼中最后一滴泪,最终,与泪相继落入湖中。
在水里,我看到水面的月像一张皱了的金色的面饼,把我像馅一样包住。
一片桃花瓣扑到了我的怀里,我这才从回忆中醒来。
我记得白家酒庄前没有桃树林。或者说,这里根本不是白家酒庄。
走进细看,只不过是个简陋版的白家酒庄罢了,倒是和邻家的林家酒庄更为相似些。
扣了扣门,没应。再扣,门上的灰都被我震落了下来。
大抵是没人了,我想。我只好倚坐在庄前的一株桃树下,幻想着兴许人家不久便回来了。百无聊赖之中,我捞了一把又一把的桃花瓣,又一次又一次把它们软软地抛下。
月色渐浓,月光从云雾中滤出水一样轻柔的流波,漫遍大地。我的眼皮打了几回架,撑不住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