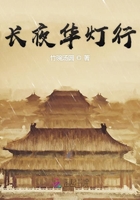萧容有些不可置信的扫了云妨一眼,陈景州则终是抬眼看他,憔悴的面容带着惊愕,讷讷呢喃着:“云妨,你……”
明明错在自己,为何她还要替自己开脱。内心的恐惧的羞愧也更似猛兽吞噬。
“皇上,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负了姜小姐。还请皇上下旨撤了我与姜小姐的婚约。”陈景州说道,像前叩了一首。
云妨心下诧异,这事情怎么来得这么突然,虽然这样的结局早有预料,却没想过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
“侯爷,你在说什么?!”云妨抬眼去看,却见他脸上神情已然恢复平静,看来是下了决心的。
可,为什么要要牺牲至此,为什么要为了她牺牲至此!
“姜小姐,我已变心了,当初许下要同你厮守一生的承诺,恐怕也要食言了,你寻个好人家罢。”陈景州低着脑袋,不愿看任何人,他的心正在一点一点被吞噬,痛到麻木,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了。
萧音的脸色更差,怒意漾满威严的面容:“你瞧瞧你都做了些什么!像话么?!朕的旨意,岂是你能说改就改的?!简直儿戏!你如此作为,是抗旨,是要被砍头的!”
一声撼动殿堂的低吼,让云妨心头泛凉。
“皇上息怒!人世万变乃常事,云妨自知同侯爷无法相配,退婚之事也可接受。之事希望皇上切莫降罪于侯爷!”云妨跟着求情道。
萧容冷眼瞧着一切,面上微妙的神情一点点结出冰霜来。
“皇兄,既然他两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倒不如成全了二人就是。”他低眼侧首道。
萧音飞快瞪向萧容,知道他心里打什么算盘,语气更沉冷了许多:“你们都当朕是什么?!先前的万般恩求,都成过眼云烟了么?!现下说变就变,那朕这皇上,也由得你们来做了!这江山也由你们话事罢了!”
萧音龙颜大怒,一拍惊堂噌的站起身,萧容立刻屈膝跪下。
“这青天白日的,吵吵什么。为何惹得皇上如此生气!”一声严厉且威仪的斥责从殿外传来。
刘嬷嬷搀着太后从外而入。
所有人皆是一愣怔,很快又冲太后请了个安。太后径自走到皇上身边坐下,面容一改以往的慈爱,此刻变得严肃沉稳。
“哀家听说了景州所求之事,也觉儿戏,不知你们几个是怎么说的,竟将皇上激怒成如此模样,可都知罪!”
陈景州趴在地上,脑袋点地道了声:“姑母,侄儿知罪。可侄儿铁了心要同姜小姐取消婚约。”
萧音怒指陈景州:“母后您瞧,他简直是冥顽不灵!”
太后劝下了萧音心中的火,沉声对陈景州道:“你一向做事稳重,怎么这一次却捅出这样大的篓子来?!当初你道要为云妨退了镇南大将军的婚,哀家依你,以为你是认真的,却没想到此刻竟又要胡闹任性一通。你究竟是何意?!”
眼看所有矛头和指责都指向陈景州,而他也情愿这么深深受着,云妨顿感不妙,若自己再不出面为他辩解,恐怕这辈子都要做良心的罪人了。
“太后,皇上,侯爷此举定有他的道理,云妨无怨。若论错责,云妨责无旁贷。”她膝行一步,神色诚恳。
萧容却抢先接过话茬:“景州,你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妨说出来。”
云妨略惊,看了萧容一眼,不知道他此时说这么一句是何用意。眼看陈景州已惹祸上身了,自己这个罪魁祸首却被人当做无辜人来同情,实在不是大义之举。
她偏头怔怔看了眼陈景州,有些事,若再不说,恐怕这辈子都迟了。
“皇上,太后。此事怪不得侯爷。一切都是云妨出的主意。侯爷只不过是被我利用罢了。”
反正这一生也不可能再嫁他人,若就此论处,她至少绝了对陈景州的愧疚。
太后和皇上皆是一愣,陈景州拦下正欲再说的云妨,低吼道:“你疯了?!在此胡说些什么!此事由我一人担着!”
萧容胸口一滞,微微拧眉睨向云妨,他预感,若她再说下去,此事便无法说清了。
“母后,皇兄,不如此事都先冷静几日,若景州依旧决意如此,再做定论也不迟。国事亦繁忙,皇兄实不宜再为旁的事操心。”萧容上前一步道。
太后抿唇忧思片刻,也道:“容儿此言不错,此事也并非绝要大事,尚有余地。哀家看来,咱们都先冷静冷静,也让景州回去好好想想。再做打算。”
皇上的怒意本未消,但见太后都这样说,也不好拂了她老人家的面子。只好铁着脸道:“既然母后都如此规劝,朕也没有反驳的道理。”
出了乾坤殿,萧容送太后回荣庆宫去,陈景州则落寞的独自走在长街上,与云妨前后保持着一短距离。
两下无话,却又好似胜过千言万语。
云妨不忍,追上前去:“侯爷今日之举,实属何意?”
陈景州没有瞒下脚步,只是有些蹒跚,疲惫的面容越发憔悴。他其实已经两夜未眠了,自那日后,他辗转不得成眠,胸口似团了虚无的火,灼烧得他几近窒息。
“你不用理我。那日终是我对你不住。此举亦当是还了欠你的罢。”他没有回头,身量萧瑟,语气却不住的颤抖。
云妨终是拽扯他的衣袖轻轻一拉:“侯爷,那事不怨你。真的。我亦知同你无关,咱们皆是遭人暗算的。你若是如此,我又该如何自处。一切皆因我而起,又怎能独留你一人迎接风浪?!”
陈景州终于驻足,却没有抬眼看他,似乎在努力隐忍:“你别管了,此事我一人解决就是。我想了两夜,已然想得很清楚。你我终是不得正果的,那便早日了断罢。否则他日,我便会无形中成为害你的双手。我怎么能?!”
云妨背脊一僵,才恍然,他原肯为她仁义至此。那自己岂不是冥冥中欠他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