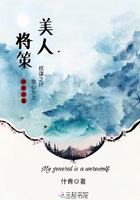窗边的诗情画意,不论在此之前,是喜是悲,可终是成了一双手,将本身毫无交集的两个人推向彼此。
寥寥想起许多日前,时间已过去久远,远到云妨已经记不起是什么时候了,也曾有一定宝蓝的轿从这里路过。
带走她幽幽哀伤。
也曾想,就这样吧,从此山水不相逢,一日过一日,一秋又一秋。可终是在某个落叶寒凉的夜晚,这场殇恸撼动得淋漓尽致。
此后,萧容和白瑾妍大婚的圣旨依旧毫无音讯,也未有一丝迹象可寻。就连陈景州那处,都没了消息。
唯一值得高兴的是,井绫每日晨起于府中给自个儿爹娘请过安后,转身就出府直奔姜家。连井太傅都纳闷儿,这丫头总是不见踪影,究竟干什么去。
井夫人每每听得他小声嘟哝,也只执了帕子摆摆笑道:“女儿家,总豢养在府中也不是个事儿,她也这么大个人了,况且这冬去春来,正是花开的好时节,世家的千金都爱聚在一块儿赏景儿,你总唠叨她做什么。”
井太傅眉头一拧,抹了把胡子就哼道:“都是你,把绫儿给惯坏了。她可是有婚约在身的,要是让长孙家的知道我们对她这般放纵,传出去我这老脸往哪放?!”
他为人十分固执,认定的事,就毫无回转的余地。
本来还只是轻松的揶揄,一提到长孙家,井夫人瞬间就垮了脸:“你还是别提那个长孙了!娶了那么个货色入府,倒是要将我的宝贝女儿置于何地?这事儿,你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你的面子了?”
“你管人家什么货色,绫儿就算进了长孙家的门,也是正室,那不过是个妾罢了,男人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再说了,要是早前绫儿愿嫁,哪还用受这种委屈。”
“那也不能纳个妓女吧!太傅之女与妓女共侍一夫?说出去,恐怕要遗臭万年!”
井夫人性子倔起来,也是九头牛都拉不回的主儿,井太傅被她嚷嚷得头疼,手一拍桌,声量不禁提了些:“行了!就算长孙家落魄成了乞丐,绫儿也得嫁过去!没的商量!”
“你,你这老顽固!没救了你!”井夫人气极,冲着那离去的背影吼道。
可那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哪有不心疼的理,之前听说那桩荒诞事后,他心里头就已经泛了浪涛,可是总觉着,若借故就此毁约,又难免会让人说成是失信。
而被长孙毅骚扰一事,井绫也未曾提过,一来是不想重提平白惹伤怀,二来是不想爹娘担心,又怕解释不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更怕连累云央。
这日,井绫又去姜家,可不巧云央和姜桓进宫去了,原本灿烂的笑脸一下子沉了不少,自以为不易察觉,掩饰得极好,却还是让云妨瞧出来了。又少不了一顿揶揄。
“姐姐,我要去布庄给伙计们发利是,讨个好兆头,你要不要同我一块去?新近来了几匹缎子,我瞧着面料极好,样式颜色都不错,你挑几匹做几件新衣吧?”
井绫将原本要给云央的东西藏在袖中,又用手再往深处送了送,心不在焉点了点头:“好,我随你一道瞧瞧去。”
布庄里,喜气一片,所有伙计不分尊卑,皆聚在堂前,接过云妨派的红利,声声道着祝语。
等红利派完了,伙计们都欢欢喜喜的继续做事去,云妨转身从袖里掏出一张银票,面额是五百两白银。
她将银票递与苏掌事儿,道:“这几年来辛苦你打理生意了,我也不是时时顾得上,你到底比我更费心,这是你应得的,往后有什么苦处,尽管开口就是了。”
苏掌事儿年方五十,膝下有一独子,却莫名得了一种怪病,吃遍了苦药也不见好,为此也花了家中不少积蓄。
这些也都是云妨辗转听来的,苏掌事儿为人老实忠厚,这些事儿,从不见他提。
一下子得了这么多钱,苏掌事儿的手都开始颤抖,连忙推开:“不不,大小姐您这是做什么,方才已经派过红利了,这钱,我不能要。”
云妨不理,径自塞入他手中,语气里是不容拒绝的坚决:“要你拿着便拿着,你做得好我才赏你,也是应当的。行了,做事去吧,我再到别的分号瞧瞧去。”
苏掌事儿嘴里不是滋味,一腔子的感慨感恩之语在喉间来回翻转,一把年纪的人了,还轻易红了眼眶:“嗳,是,是,谢大小姐恩赏。”
眼前这一派和谐之象,倒也将云妨心中阴雾扫走许多。正要唤了在挑选布料的井绫,却被一声急促的喘息打乱了思路。
“大,大,大小姐!不好了,西街的分号出事儿了!”来人正是分号里的小工,一瞧便知是从上赶着从分号那边跑来传信儿的。
云妨皱眉,忙问怎么回事。井绫也被这声音吸引了注意,无心再顾其他,缓缓踱了过来一探究竟。
那小工大口大口喘息着,冒了一头热气,“楚,楚王府上的一位夫人,今日到铺子里买布,可不知怎么就得罪她了,非说咱们以下犯上,硬要找管事儿的去,可刘掌事儿在那好说歹说都不成,闹得简直一发不可收拾。”
云妨听完,脸已煞白到快将透明,连往日无须点缀都自然泛红的唇,此时也失了颜色。她心头被狠狠撞击着,竟说不出话来。
井绫见状,轻轻握了云妨的手,沉声对那小工道:“人走了没。”
小工苦着脸摇头:“没呢,要是走了算好,可现下就在铺子里等着,非要府上管事儿的过去。”
井绫听罢,脸色也不大好了,她窃窃瞧了眼云妨,差点没惊掉下巴。那本来沉鱼落雁的一张容颜,此刻却煞白得无法形容。
默了许久,云妨嘴角动了动,双眸寒凉,道:“姐姐可愿意替我去楚王府将殿下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