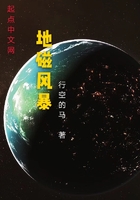那厢,文种还在热切地说着,“咱们不是一直发愁不能接近吴王吗,如今机会来了,只要我们能够找到那位越女,并说服她,那吴王的一举一动就等于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甚至还能将你引荐给吴王。”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法子。”范蠡深以为然地点点头,又道:“关于那位姑娘,你可还打听到什么?”
“知道的都说了,据伯嚭所言,当时情况匆忙,吴王连那位姑娘的名字都来不及问。十天……”文种攥一攥双手,咬牙道:“就算翻遍姑苏城,也要把那位姑娘找出来!”
夷光试探道:“文先生说吴王伐越之时曾经犯病,未知是何病?”
文种想了想,道:“似乎是一种心病,具体……”未等他说完,夷光已是道:“心绞病。”
此言一出,范蠡与文种皆满面诧异地看着她,前者率先回过神来,“你如何知道?”
夷光眼底掠过一丝犹豫,但很快就消失无影,她定定看着范文二人,一字一句道:“因为――我就是吴王要找的那个人!”
若说之前的话令范蠡二人诧异,那么现在就是震惊了,尤其是文种,瞪着夷光的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从见到夷光的第一面起,他就为后者的美貌所惊叹,赞其为世间第一美人;可万万没有想到,她就是吴王夫差苦苦追寻的那位美人,这……这未免也太巧了。
待得回过神来,文种小心翼翼地道:“施姑娘不是在与我们玩笑吧?”
夷光正色道:“这等大事,夷光岂敢玩笑。”
听到这话,文种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落了地,抚掌大笑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太好了!”
相较于文种的欢喜雀跃,范蠡则显得有些沉重,他盯着夷光,“你如何能够肯定?”
“吴王伐越的时候,我随郑姐姐他们逃难经过溪边的时候,曾救了一个年轻人,他当时心绞痛发作,正好我也有这病,一直随身带着父亲所做的葯,便救了他;之后,他送了我一个笛子,那么巧,我前几日正好在城中吹过。所以,我可以肯定,我就是吴王要找的那个越女!”夷光终于知道,为什么那夜她会觉得那位吴王的声音有些耳熟,原来他就是赠笛的那位公子。
文种若有所思地道:“能否让我看看那支笛子?”
“当然可以。”夷光折身自包袱中取出那枝小巧的笛子,此笛非金非玉,是用常见的竹子所制成,唯一稀奇的是,笛声有许多斑斑点点,犹如泪痕一般。
就是这么一枝再普通不过的竹笛,却令文种激动不已,迭声道:“就是这枝,你见的人果然就是吴王。”
听到这话,范蠡本就不怎么好看的面色又沉了几分,“你从哪里看出?”
沉浸在欣喜与激动之中的文种,没有留意到范蠡的神色变化,道:“伯嚭说过,吴王母亲临终时曾留下一支竹笛,吴王一直随身携带,未有片离出身,可从越国回来,此笛却不见了踪影,可不就是这一枝吗?”
“人尚且有相似,追问是区区一支竹笛。”面对范蠡的质疑,文种连连摇头,“绝对不会,先王后留下的那支笛子是用湘妃竹制成,而吴国不产湘妃竹,极少见到,我来了两三年,也就只在过路客商那里见到过一回,必是此笛无疑。”说着,他又道:“听闻伍榕曾问吴王讨要过此笛,被吴王所拒,万万没想到,他竟会赠予你,可见对你的重视。”
说到这里,文种双眼发亮地盯着夷光,“施姑娘可愿为复国,为大王尽一份心力?”
“夷光是越国人,如今越国正值生死存亡之际,夷光理应尽一份心力,而且……”夷光眸光一黯,轻声道:“这也是父亲的遗愿!”
“太好了!”文种拍腿叫好,随即翘起大拇指赞道:“施姑娘真乃巾帼英雄,若能复国,施姑娘居功至首!”
夷光欠一欠身,轻声道:“文先生过奖了。”
“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伯嚭!”文种兴奋地站起身,刚要迈步,耳边响起范蠡的声音,“夷光不能入宫。”
“为何?”文种诧异,从刚才起范蠡就一直没怎么说过话,没想到一张口就是反对。
范蠡起身,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道:“谁都能入宫,唯独夷光不行!”
文种心思一转,已是明白了过来,“你怕夷光有危险?”
范蠡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道:“施公临终之前将夷光托付给我,让我一定要护夷光平安,我不能食言。”
文种一愣,随即叹了口气,“但凡第二个选择,我也不会送夷光入宫,可偏偏她就是吴王要找的那个人,没有人比她更合适。”
“无论怎样,你都不可以迫她入宫。”听到这话,文种不禁有些着急,正要说话,夷光比他先一步道:“范先生误会了,此事是夷光自愿,文先生并无半分逼迫。”
范蠡怜惜地看着她,“你不清楚其中危险,吴宫于你就犹如龙潭虎穴,稍有不甚就会丢了性命,万万去不得!”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你与文先生为了复国大业,孤身犯险,夷光又岂可置身事外,再说……”几丝冷厉如尖针的光芒自夷光眼底射出,“去了吴王身边,亦能打听出杀死父亲的究竟是何许人!”
“我会帮你会找出杀死施公的人,替他报仇,你又何必去犯这个险,万一有什么事,九泉之下,我又要如何向施公交待?”
面对范蠡諄諄劝说,夷光并不为其所动,神情坚定地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若夷光此去真的丢了性命,那也是天意,与先生无关。”
文种亦在一旁道:“夫差痴迷于施姑娘,而她自己又愿意进宫,范兄你又何必苦苦阻挠?难道你忘了来姑苏的目的了吗?”
范蠡面色阴晴不定,半晌,他道:“复国固然重要,可施公的临终托付一样重要,所以夷光一定不能入宫。”不等文种言语,他又道:“我知道这个机会难得,你不想错失,我们可以另寻一位越女,将夷光与吴王相遇的点点滴滴都细叙于她,以假乱真。”
文种怔怔看着他,若非那张脸再熟悉不过,他几乎要怀疑眼前之人究竟是不是范蠡了。
“范兄糊涂了,假的始终是假的,稍有一点问题,就会被戳穿,到时候追查下来,你我都要倒大霉。再说了,另寻一位越女,谁敢保证她不被宫中荣华富贵所迷,从而背叛甚至是将我们供出来?到那时,又怎么办?”
范蠡抿唇不语,他也知道自己这个提议草率了,可要他眼睁睁看着夷光为了复国牺牲自己的清白乃至性命,他做不到。
文种面色也不大好看,见范蠡久久不答,对夷光道:“施姑娘且先歇着,我与范兄单独说几句话。”也不等夷光答应,他一把拉了范蠡出门,一路来到远离小楼的书房,方才松开手,冷着脸道:“此处没有外人,你与我说实话,为什么不肯让夷光入宫?”
“我说过,施公临终嘱托,我不能辜负。”面对范蠡与先前一般无二的回答,文种冷笑道:“到底是真不敢辜负,还是你另有所思?”
范蠡一怔,“这是何意?”
“你这段时间一得空就来此处见夷光,从琴棋谈到书画再到经史,我与你相识多年,从未见你对女子如此上心,你分明就是喜欢上了夷光。”
范蠡万万没想到他会说这样的话来,一时面色大变,拂袖喝斥道:“休得胡说,我是见夷光因为施公之死,心情郁结,怕她想不开,方才多加陪伴开导,并无半分私情。”
文种并不相信他的话,径直道:“夷光貌美无双,倾国倾城,你倾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你别忘了,眼下说的是复国,你身为越国臣子,岂可因儿女私情坏了大事?”
“我说了没有私情,你怎么就是不信。”要说这话时,范蠡心中微微一悸,但他无暇也不敢去细想,正色道:“观鱼大会一事,我会想办法,你不许再打夷光的主意!”
文种对他的话嗤之以鼻,“又想用那以假乱真,移花接木的把戏?”
“出了问题我自会负责……”范蠡话音未落,文种一直积压的怒气瞬间爆了出来,一把揪住范蠡的衣襟,低吼道:“你负责?你负责得起吗?!此事一旦出了纰漏,不止我们俩个要死,大王也难以活命,到时候,越国就真的完了;你口口声声说无颜去见施公,那你就有颜面去见大王,去见千千万万被吴军杀死的越国百姓吗?回答我,说啊!”
见范蠡无言以对,文种又道:“明明有那么好的一枚棋子摆在面前,你却非要去用劣棋,这不是存心和自己为难吗?”
见他将夷光比作一枚棋子,范蠡面色一沉,拉开他的手道:“夷光是人,不是棋子!”顿一顿,他又道:“不错,找人代替夷光,却有可能出现纰漏,可谁敢保证,夷光入宫就一定没有问题,施公是谁杀的,我知道你也知道,夷光入宫,一半是为了越国,一半是为了给施公报仇,一旦她知道杀死施公的是公孙离,绝不会善罢干休。”
文种不以为然地道:“那又如何?”
“公孙离是伍子胥手下,后者又是出了名的护短,若是夷光行事不周,被他发现端倪,必会想方设法杀了夷光。”
“那不是正好可以激化他与夫差的矛盾吗?”文种的话冷酷却没有错,范蠡也知道,所以没有与他争论,而是道:“就怕明枪易躲到时候,一样是前功尽弃!你别忘了,那些送来姑苏的越女是怎么死的。”
听到这话,文种怒气渐消,范蠡的话虽不中听,却有那么几分道理,“那要怎么办?”
“还有十日时间,我们可以细细谋划;你也趁这机会找找有没有合适的越女能够担此重任。”
“好吧,我现在就去安排。”文种无奈地点点头,往外走去,令他没想到的是,刚到门外,就看到了一个纤细柔弱的身影,惊讶地道:“施姑娘?你什么时候来的?”
范蠡一惊,连忙走出去,果见夷光执伞站在门外,眼底不禁漏出一丝慌乱,他刚才提及公孙离杀死施公,万一夷光听去……
“刚到不久。”夷光在伞下微微一笑,犹如百花齐放,就连一向不爱美人只爱钱的文种也不禁有些失神;如此美人,实在是世间罕见,难怪吴王会念念不忘。
“夷光担心二位因我而起争执,便过来瞧瞧,不知二位可曾商定?”
“这个……”文种带着一丝无奈道:“范兄说得不无道理,入宫一事,就算了吧。”
夷光纤长细密的睫毛微垂,在粉面上投下一对细长的影子,“可否让我与范先生说几句话?”
“当然。”文种应了一声,知趣地离开,留下夷光与范蠡二人独处。
夷光拾步走上台阶,合起手中纸伞,搁在门边,随即双手搭腰,屈膝朝范蠡行了一礼,后者诧异道:“这是为何?”
“这一礼,是多谢先生对夷光的照拂。”夷光声音是一向的轻缓动听,如溪水淙淙,又如百灵轻啼。
听得是这么一回事,范蠡心中一松,对维持着屈膝姿态的夷光道:“这是范某应该做的,无需多礼,快快请起。”
夷光依言直起身,一双秋水明眸落在范蠡身上,“先生之情,夷光已然谢过,余下之事,还请让夷光自己做主。”
范蠡一怔,两条英气的眉毛瞬间蜷曲了起来,“你还是想入宫?”
“是。”这个字夷光说得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人比我更适合。”
“不行。”范蠡拒绝道:“复国之事,你无需担心,我与文种兄自会想办法,”
夷光定定看着范蠡,就在后者以为她被说服的时候,夷光忽地道:“先生是怕我因为父亲的仇,而误了大事。”
范蠡没想到她竟能看穿自己这层心思,心中不禁翻起惊涛骇浪,强自镇定道:“你不要多想。”
“公孙离。”听到这三个字,范蠡再也控制不住心中震惊,脱口道:“你听到我与文种兄的话了?”
“是。”夷光美眸中浮上一层稀薄的水光,但只是一瞬间便又压了下去,仿佛从未出现过,静声道:“先生放心,夷光入宫之后,会事事以大局为重,绝不会令先生为难。”
“你……”那着那张精致无双的容颜,范蠡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夷光低眉,又道:“父亲的仇,自是不能忘,但夷光会瞅准时机再动手,绝不会轻举妄动,坏了大事。”说到此处,她抬起眉眼,“说到底,公孙离只是一个刽子手,真正害死父亲的,是整个吴国;只有吴国覆灭,父亲在九泉之下方能瞑目。”
范蠡神色复杂至极,他费尽口舌才拒绝了文种,一转眼,夷光却自尽入宫,还如此坚定,实在是让他犯难。
院中起落不绝的蝉鸣,将时间一点一点带走,风拂过,吹动彼此宽大的衣袖,犹如两只翩翩起飞的蝴蝶,却又怎么都飞不高。
“一旦入了宫门,你就是贪慕虚荣的越国叛徒,就是伍子胥乃至后宫中人的眼中钉;反之,就算我与文种兄复国失败,冬云也会带你离开姑苏,寻一处山青水秀的地方,安然度此一生。”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再说了,那样苟活一生,与行尸有何分别?”说罢,夷光展袖伏身,再次道:“只求先生成全。”
这个回答,彻底浇熄了范蠡心底最后一丝期望,望向夷光的眼里带着深深的无奈,“希望你不悔今日这个决定!”
“不敢有悔!”夷光低头,目光正好落在袖口密密匝匝的刺绣上,每一针落下,对于锦缎来说,都是一次伤害,可即使是如此绵密的针脚,锦缎始终甘之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