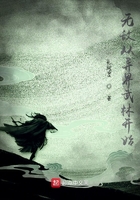在《夜》那首诗里,普希金似乎说明了他同阿玛丽雅的爱得到了满足。
黑影里,
你的大眼睛放着光辉。
你在对我微笑,
在我耳边窃窃私语:
朋友,亲爱的,我爱你,
我将永远属于你……
1823年年底,普希金对阿玛丽雅·李兹尼奇的爱达到高峰,如同“瘟疫般的病态”,像“黑色忧郁症”,似“高烧”,又像“疯癫”。普希金自己也感到有些害怕。但在此时,他心爱的女性却已身怀六甲,很可能是巨商李兹尼奇的孩子。在1824年初,她生下一子,产后就病倒了。吐血不止,只好去意大利休养。普希金的情敌雅勃洛诺夫斯基随她一起走了。
1824年5月,阿玛丽雅离开他时,普希金并没有太忧伤。阿玛丽雅因患结核病在1825年离开了人世。她丈夫生性多疑,弃她而去,她的情人也离开了她。她是一个人在贫困中咽气的。1826年听到她的死讯后,他却显得十分悲哀、痛心。在1823年底,阿玛丽雅已怀有身孕,无疑普希金见到她的机会大大减少了,他只好另寻他欢。她离开敖德萨时,普希金已经习惯了没有她的生活。他诚然还在爱着她,但只能留在记忆中了。另外一位女性马上填补了他心中的空缺。这位女性正是沃龙佐夫的妻子——伊丽莎·沃龙佐娃,她虽比普希金年长7岁,但她富有波兰女性的柔媚和风雅,美丽而且姣艳。加上渥隆佐娃通晓诗文,因而普希金对她大献殷勤,过往甚密。正是她缚住了诗人那一颗忧烦的心,使他在那单调、凝固的敖德萨石岸上留了下来:
你等待过,你呼唤过……而我
却被捆住,我的心徒然地挣扎:
那强力的热情迷住了我,
我又留在了你的岸边……
(《致大海》)
然而,好景不长。普希金又从南方流放到故乡米哈伊洛夫斯克,于是这一多情女子也就与普希金诀别了。
1829年1月15日,普希金回到圣彼得堡,专心于赌牌和重新诱惑女人。
诗人的所有稿酬都流到牌桌上了。莫斯科警察局把普希金列为著名赌客第36号。“第1号费多尔·托尔斯泰伯爵——敏捷的赌客;第22号纳肖金——好惹事生非的赌客,大量有关他的报告材料使他出了名;第36号普希金——莫斯科的著名赌客。”
不长一段时间,“铜色维纳斯”就把普希金从牌桌旁吸引过来,她就是阿格里平·莎克列夫斯基伯爵夫人:一位显赫的美人,黝黑的皮肤,灼热的目光,终日放荡,纵欲无度。对异性的需求折磨着她,她在自己周围激起了灾难性的情欲、诗意和膨胀的嫉妒。她在体力和心理上消耗情夫们,也消耗她自己。她时而嘲弄人,时而又厚颜无耻地表示歉意;时而精心打扮,时而又无精打采,好像她一直在寻求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这种高雅的歇斯底里做法摧婚毁了众多的追求者。一向多情的普希金当然是其中表现最为痴情的一位。一位见证人说:“不久前,普希金在拜访中训斥伯爵夫人,因为她为照顾一位外来人而冷落了普希金。后来,他生气了,用长指甲深深地掐进她的手心里,把血都掐了出来。”
普希金自己写道:
你的坦白,你的抱怨,
你的呼叫,我都贪婪地记在心间。
多情的话语叫我晕眩,
请你嘴边不要这么甜!
你的想法从不同我见面。
我既担心你的欲念,
又不敢了解你的心愿。
一连数月,普希金竭尽全力地爱着这位风流女人,并满足她的要求,忍受她突如其来的哭笑声。她饮酒纵欲,多虑多疑,疲惫倦怠,偶有微恙,还爱嫉妒。普希金有好几首诗都是献给她的,甚至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一诗中也赞美过她,并把她列在唐璜名单里。她是被他完全占有过的女性之一。同她来往使普希金疲惫不堪,他只好离开她,去寻求较为宁静的爱情。在这种消魂消魄的最后日子里,普希金写信给希特罗沃太太说:“标准的女性和伟大的情感是世界上我最害怕的两件东西。轻佻的女子万岁……您愿意我对您开诚布公地谈谈吗?也许我很优雅,如同我的作品一样,但我的内心是很庸俗的,我的爱好同第三等级的人是一样的。偷情、爱情和书信搅得我头昏脑涨……尽管我全心全意地爱着她,但与一位让我生气的女人交往,我感到不幸。”
普希金对之吐露隐情的女子叫埃丽丝·希特罗沃,时年46岁,是库图佐元帅的女儿、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菲格蒙伯爵的岳母。她的客厅如同消息交换场所,在那里相互通报圣彼得堡最新的政治和文学消息。她神态优雅,耐心,面带笑容,十分老练,客人们对她十分尊重。她身体强壮、丰满,自称她的肩膀是全俄国最漂亮的肩。她身穿诱人的袒胸露臂的连衣裙,故意把双肩裸露出来加以炫耀。一个年近半百的女子在众目睽睽下展示自己的上半身,这一奇怪做法为她赢来一个“裸体的丽丝”的绰号。佩罗夫斯基望着这位卖弄风骚的女人说:“应该为自己的过去罩上一层薄纱。”作家索洛古布在谈到她时说,她天天很晚才起床,在卧室里接待第一批客人,并用甜美的声调对他们说:“请坐……不,别坐那把沙发,那是普希金的座位……也别坐那张大沙发,那是茹科夫斯基的座位……就坐在我的床上吧,这是大家的座位……”
事实上,希特罗沃夫人的风流韵事并不比莎克列夫斯基伯爵夫人多,她也不如莎克列夫斯基太太出名。埃丽丝·希特罗沃夫人善良,宽厚,多情而又忠贞。她开始与普希金来往时,就疯狂地爱上了他。她的爱恋使她的肉体和灵魂都无法安宁。她是贵夫人,却高高兴兴地伺候人。她给自己崇拜的人以无限的母爱,对他体贴入微,在他面前卖弄风骚。无疑,对这种强烈的爱,普希金有时也回报一二次,然后他就抛弃了这位袒胸露臂原胖女人。但是,埃丽丝·希特罗沃太太虽然不能再享受短暂的快感,仍继续公开或私下地爱着她心中的偶像。
然而,无论是伯爵夫人还是希特罗沃都不能叫诗人满足,他喜欢另寻新人。他对青年女性的神秘感越来越大。在三山村,他周旋在姬姬和她那些刚刚脱离稚气的女伴周围;在莫斯科,他则迷恋上了亚历山德琳·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娃、乌鲁索娃姐妹、索菲娅·普希金娜(她拒绝了他);还有叶卡特琳娜·乌沙科娃,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与她共命运。在圣彼得堡,被堡中的处女是一位20岁的女郎、美术学院院长的女儿安娜·奥列宁娜。
1928年,普希金发表了《我以前是怎样的》这首诗:
我以前是怎样的,现在还是怎样,
无忧的心,善于钟情。
你们早知道,朋友,
我是否能看到美色
而不神魂荡漾——
我少不了那内心的激动,
怯懦的温柔!
难道爱情还没有和我耍弄得够久?
在维纳斯所编织的欺骗网中,
像一只幼鹰,我挣扎、冲击得
还不够受?
但是,多次痛苦的经验
并没有,并没有使我悔过,
对着新的偶像,
我又奉献了我的恳求……
诗中的偶像原型安娜·奥列尼娜。1928-1929年间,普希金与她全家有过亲密的交往,并狂热追求奥列尼娜,向她求婚。但后来又自动撤销了求婚要求。
女人,女人,总是女人!普希金的生活中充满了女人,这一点为许多人所不屑。然而,我们客观地说,诗人普希金身上所彰显的真正人性化的爱情观,毕竟跟那些专门玩弄女性的登徒子有所不同。应该说,他纷繁而复杂的情感经历,与其辉煌的诗歌创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不幸之爱
1830年,而立之年的普希金在莫斯科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了一位绝色少女。她约莫十六七岁的年纪,容貌端庄,赛过山水芙蓉,她那婀娜轻柔的舞姿更让人倾倒。她就是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冈察洛娃。普希金一见到她,就不能不拜倒在她的脚下。在诗人的眼里,冈察洛娃是一幅名画,是艺术的奇迹。
普希金认识冈察洛娃后,时常上她家去,他完全被她的美貌所迷倒,爱情的烈火不可遏制地燃烧着。可是,冈察洛娃对普希金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而且她的母亲也不太喜欢这个风流才子。在对于宗教和沙皇的看法上,她们母女俩和普希金也完全不一致。因此,普希金觉得与这个家庭来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冷淡和拘束之感。
他终于向冈察洛娃求婚。结果碰了个软钉子,冈察洛娃的母亲婉言相拒,孩子还小,现在还不急于考虑婚事。
一块通红的火炭,投入了冰水之中。
普希金痛苦至极,当天就启程到高加索去,参加了正在和土耳其作战的俄国军队。他企图通过战争的剧烈刺激,来忘却爱情创伤的痛楚。
半年之后,普希金回到了故乡。他正准备到国外去作一次长途旅行,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使得普希金改变了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普希金的一位朋友在莫斯科的一个舞会上,偶尔遇上了冈察洛娃母女俩。他俩向她们谈起了普希金,并介绍了普希金的高加索之行。奇怪的是,这次冈察洛娃母女对普希金不再那么淡漠,而是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关心。
这个消息,真好比天边飞来了一只金翅鸟,把普希金冷却的心重新温热了,枯萎了的爱情幼苗立即复苏了。他马上动身赶到莫斯科。在冈察洛娃家里,他受到了热情款待。冈察洛娃含情脉脉地向诗人流露了爱慕之意。当诗人再次求婚时,终于得到了满意的应允。
1831年3月2日,莫斯科大升天主教堂响起了清脆的钟声,普希金和冈察洛娃在这里举行了婚礼。诗人的脸上流露着幸福的微笑。从此,普希金便开始了新的生活。
同别人一样,蜜月的第一周,他们过得十分幸福。为表明自己的独立性,婚后第二天,普希金就同朋友们外出了。冈察洛娃整整等了他一个晚上。她一个人呆在陌生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孤独寂寞,抽噎不止。但以后几天里,普希金再没有这样残酷地对待妻子。他没有再同妻子分开,而是陪妻子一起参加舞会,分享众人送给妻子的荣誉。他俩经常一起出席化妆舞会,一起到朋友家吃晚饭,一起看戏,一起散步。普希金买了一辆漂亮的四轮马车,冈察洛娃同丈夫形影不离。她身披崭新的蓝色天鹅绒皮大衣,显得十分漂亮。
一位名叫卡希吉娜的女士写道,当普希金站在美丽的冈察洛娃身旁时,她感到普希金很像一只驯服的猴子。
“婚后,他完全变了,庄重稳健,通情达理,十分宠爱妻子……当我看见他同漂亮的妻子站在一起时,我不由得想起那种聪明伶俐的小动物。不用说,你们一定会猜出是什么动物了。”
但是,就在这充满着幸福的阳光的小家庭里,却隐茂着一道不和谐的阴影,一日子一长,它就渐渐显露出来。
普希金很爱自己的妻子冈察洛娃,把她看成是自己生活和事业的志同道合的伴侣。他的创作激情如清泉喷涌,每写好一首诗,就兴致勃勃地跑到冈察洛娃面前朗诵,征求她的意见。可是冈察洛娃根本没有文学修养,不懂诗歌。她的兴趣只在舞会上,她的心思全部用来琢磨如何用最入时的服装来打扮自己,怎样参与上流社会的交际。因此,每当普希金捧着诗稿来到她面前时,她就倍感头痛。
冈察洛娃不知该如何去欣赏丈夫写的那些押韵的句子,她只感到它们在耳边嗡嗡作响,令她头昏脑胀,甚至叫她生厌。难道欣赏这些有节奏感的谎言需要有特殊的脑袋不成?在冈察洛娃的心目中,只有家庭、舞会奉承话、衣裙才至关重要。而对普希金来讲,他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东西,他是在梦幻中生活。要到达这一梦境,路途遥远,困难重重,最好是放弃这种打算。
一天上午,普希金对对两位女性朗读诗歌,冈察洛娃忍无可忍,扭过脸,大声叫道:“天哪,你的诗太叫我厌倦了,普希金!”
普希金说:“请多原谅。可这首诗你根本没听过,我还从来没有对你读过它呢。”
“不论是这首诗,还是别的诗,都是一样地令人厌倦。”
普希金感到为难,耸耸肩头,想笑一笑。
随着在交际圈的频频亮相,她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她“像星斗一样光辉闪烁”,她“如阳光一样明亮”,她“貌压群芳”,是“皇后”……凡是同冈察洛娃在一起呆过的人都这样称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