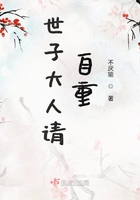启平四年,春。
明帝刘舒曳册立贵妃上官氏为后,封号:嘉元。
(华月宫)
上官月拿着金黄的圣旨,呆呆的立在正殿中央,安明公公宣了旨,道了声恭喜便走了。上官月遣了所有下人,只留贴身婢女锦梦一人陪在身旁。
“锦梦,你看看……”上官月环顾着四周,看着皇帝赐下来的无数锦罗绸缎,珠宝首饰,笑道:“他还是封了我上官月啊……”
“娘娘,您得记住,从现在开始,您便是这大盛王朝的皇后了,”锦梦低着头,轻声道:“这些话,不可叫外人听了去,您背后可是整个上官家……”
“我明白!”上官月将手中的圣旨狠狠地扔在地上,朝着锦梦吼道:“我明白!我明白我是上官家的嫡女,我明白我身后是上官家上上下下六百多口人,我明白皇后的位子很重要……我明白……”上官月抱着头慢慢跪了下来,泪,尽数落在了圣旨上那苍劲有力的字迹上,“可我呢?我想要的呢?他们曾经答应过我的呢?”
“娘娘……”锦梦走上前一步,伸出手,却被她一把推开。
上官月低着头看着被自己的眼泪斑驳的字迹,伸手抹开那一滩墨渍,忽的笑了。
(御书房)
“陛下是要把贵妃娘娘的封后礼选在除夕吗?”安明捧着刚刚切好的茶递到刘舒曳跟前。
“图个喜庆,正好也要办年关宴,让礼部准备准备,一起办了吧。”刘舒曳摆了摆手,让安明把茶端下去,继续批着手里的奏折。
外间的全德轻手轻脚地走进来,跪地道:“陛下,广平王殿下求见。”
刘舒曳停了笔,眉头微皱。一旁的安明见状说道:“陛下,广平王殿下这时候进宫莫不是……”
“闭嘴!”刘舒曳轻呵一声打断安明,“管好你自己的嘴,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该说,自己掂量!”
“陛下恕罪!”
刘舒曳撇了一眼跪下的安明,摆了摆手道:“行了,下去吧,让广平王进来。”
“是。”安明弯着腰慢慢退下,随后广平王刘景阳便进了门。
“臣弟参见陛下。”
“坐吧。”
“臣弟不敢逾矩。”
刘舒曳抬眼望了望阶下恭恭敬敬立着刘景阳,放下了手中正批着的奏章,抬手揉了揉眉心,“什么事?”
“陛下,是立了贵妃娘娘为皇后吗?”
“一个时辰前才下的旨,你的消息倒是得的快。”
“望陛下恕罪,”刘景阳连忙跪下,“臣……”
“你有何不满?”
“臣……”刘景阳张了张嘴,又将话咽了回去,只低着头。
“起来吧,”刘舒曳合起奏章,叹了口气,“你我本一母同胞,不必如此。”
“是。”
“朕若没记错,常至你今年该有二十四了吧?身为大盛的亲王,一直不娶正妃倒也不是个样子,有看上哪家姑娘吗?朕给你赐婚。”
“臣无意娶妻。”
“户部尚书林毅仁的嫡女林婉尚未婚配,前日宴上你也见过,瞧着可顺眼?”
“皇兄……”刘景阳看着刘舒曳喃喃道:“你明明知道的……”
“你希望朕知道什么?”
“霜儿她……”
“放肆!”
外间的全德听着陛下的声音,便凑到安明身边:“师傅,陛下是发火了吧?里面动静可不小啊!”
“你懂什么?”安明闭着眼睛长吁一口气,“广平王倒还真是不知好歹,这立后的旨刚下,便跑进宫来触陛下的霉头。”
“您是说,广平王殿下他……”
“闭嘴!”安明忙喝住全德,用手中的拂尘狠狠地敲了敲他的脑袋,“别搁这瞎猜,有些事情都给咱家烂在肚子里藏好咯!不然明个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是是是,”全德摸着脑门,委屈巴巴的回道:“知道了知道了……”
安明看了看眼前嘟嘟囔囔的全德,又侧耳听了听殿内的动静叹了口气,抱着拂尘闭着眼不说话。
“师傅,怎么啦?”
“今个儿教你个道理,记住了也记牢了!”
“唉!您说。”
“这人啊,一辈子要是能迷迷糊糊,当傻子充楞就能长长久久。”
刘景阳看着面前自己无比敬爱的兄长,心头发涩,“臣弟就问这一句,庆元三十一年,到今日,七年了,你可曾感到过一丝愧疚?”
刘舒曳望着阶下还瞪着自己的弟弟,忽的笑了,慢慢走到刘景阳身旁,“你倒是很在乎,呵,”刘舒曳轻哼一声,“广平王自及冠封王已有四年,正妃位一直未定,你在等什么?”
“臣……”
“刘景阳,你可知觊觎后妃是什么罪?”
“臣知。”
“那就给朕记牢了,有些东西,你最好想都不要想!”刘舒曳说完便抬脚走了出去。
刘景阳看着面前空空的桌子,松开了一直紧攥着的手,一滴鲜血顺着指尖落到了地上。
她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啊?
“陛下,您这是要去哪啊?”安明看了看上了步辇就闭目不语的刘舒曳,试探的问道。
半晌也没有等到步辇上帝王的回话,安明暗自捏了一把汗,又道:“这条路最近的便是贤妃娘娘的碧萧宫了,陛下要去看看吗?”
刘舒曳慢慢睁开了眼睛,“去碧萧宫吧。”
“摆驾碧……”
“罢了,”刘舒曳出声止住了安明,“去,华月宫。”
“摆驾华月宫——”
步辇走了小半柱香,眼看着就要到华月宫门前了,刚停了没一会儿的雪又下起来了。刘舒曳抬手示意步辇停下,走了下来,抬头看着这满天的雪,被风吹的东倒西歪的落下来。
一旁的安明忙撑起伞替刘舒曳遮住,“不必遮了,”刘舒曳让安贤将伞收起来转身便朝着西边去了。
“哎!陛下,您去哪啊?”安明看着忙提着伞跟上。
我记得,她是最爱雪的,这么冷的天可别在外面冻着了。
刘舒曳心中如是想着,脚上的步子便不禁快了些。
“七年了,你可曾感到过一丝愧疚?”耳边突然炸起的声音钉住了刘舒曳往前的步子。
“陛下,怎么又不走了?”
“安明,”刘舒曳问道:“霜嫔的伤可好些了?”
安明愣了愣神,细细斟酌着句子道:“太医说伤口已经开始结痂,没什么大碍了,只是霜嫔娘娘身子虚,又是寒冬腊月的,需要静养,万不可受了风寒。”
刘舒曳抬起脚继续走着,想了想道:“回头将张显明送来的血燕窝给玉霜宫送去。”
“是。”
(玉霜宫)
“娘娘?”秋罗捧着刚做好的梅花糕进了白为霜的卧房,却没看见人,“怎么又不见了?”秋罗想着转身出了屋,穿过回廊便看到披着外衣的白为霜站在那头的小亭中。
“娘娘!太医说了要静养,别整天在外面站着,要是真受了凉,可有的您受的!”秋罗将手中的碟子放到身旁的石桌上,上前替白为霜理了理衣襟。
“好啦,”白为霜笑了笑,“就是觉得这雪下的漂亮的很,想看看。”
“屋里不能看吗?”
“陛下驾到——”安明的声音突然从回廊那头传来,白为霜猛的抬头,便看见那冷俊绝美的帝王朝自己走来,慌忙领着秋罗行礼。
“参见陛下。”
“不知圣驾至此,未曾相迎,望陛下恕罪。”
“你身子还虚着,大冷天的怎么还站在外面。”
白为霜低着头,愣愣地瞧着那双将自己扶起来的手,半天没说出话,一旁的秋罗看了干着急,便轻轻唤了一声:“娘娘!”
白为霜回了神,忙抽出双手回道:“臣妾身子好多了,谢陛下挂念。”
刘舒曳看了看空空的双手,也不甚在意,拉着白为霜坐到石凳上,瞥见桌上的梅花糕笑道:“怎得这些年也不见你换个口味?”
“只是冬天下着雪,觉得吃这梅花糕应景些。”
刘舒曳轻轻拈起一块咬了一口,“甜了,倒是不及你的手艺。”说着便把糕放下,接过白为霜递过来的茶轻抿了一口。
“陛下怕是许久没吃了,这梅花糕一向如此甜呢,再说,臣妾怎会有御厨那般的手艺。”
刘舒曳笑了笑,刚想说些什么,便听见偏门传来几声轻唤。
“娘娘,娘娘!”园福抱着一个不大的锦盒,从偏门小跑进来,“娘娘,广平王……”园福捧着盒子,走进小亭,抬眼便看到刘舒曳坐在白为霜旁边,马上跪地道:“奴婢不知圣驾在此,惊扰了圣驾,奴婢罪该万死!”
“手上的是什么?”刘舒曳也不恼,只是单单问着园福手上的东西,方才分明听到了“广平王”三字,送的什么,竟要让下人从偏门带进来。
“陛下!”白为霜马上起身跪在刘舒曳身侧,“园福无意冒犯,是臣妾刚刚让他去御膳房取些点心。”
“广平王送的?”刘舒曳端起手边的茶,语气平和,不知喜怒。
“许是……”白为霜心中发颤,凉意瞬间传遍全身:“许是回时恰好碰上了……”
“呈上来,给朕看看。”
安明听着便把园福手中的锦盒拿过来递给刘舒曳,打开,是一朵纯白的雪莲。
“这雪莲可是稀罕东西,广平王从西域回来,也不见给朕带些什么,倒是往你这玉霜宫送的勤快。”
“陛下,臣妾……”
“在西域,雪莲代表着最纯洁的爱意……”刘舒曳拿起那雪莲细细看了看,“这广平王对你倒是情深似海啊。”
“陛下,广平王殿下必定不是这个意思……”白为霜脑中一片空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广平王怎会无故送自己这种东西?
“哟,还写了信,”刘舒曳放下雪莲,拿出盒底的纸条,展开来,上面只写了一句诗:
“梦起至戏月,只因落花颜……”刘舒曳缓缓读道,刘景阳的声音像是除夕的爆竹一般,在耳边炸响:
“臣弟就问这一句,元庆三十一年秋,到今日,七年了,你可曾感到过一丝愧疚?”
“呵,戏月楼,落花颜,”刘舒曳笑道:“怎么,你还想说什么?替他求情?”
“陛下,臣妾……”
“还当真是郎情妾意啊!”刘舒曳揉碎了手中的纸,连同那雪莲与锦盒一起狠狠地扔在地上,吓的亭中几人悉数跪下。
“陛下息怒,”安明伏地道:“广平王征战西南数年,霜嫔娘娘有久居深宫,定是不能……”
“闭嘴!”刘舒曳吼着,走上前捏住白为霜的下巴,抬起她的头,看着那泪眼朦胧的双眼,忽的笑了:“白为霜,你们若真是情投意合,那朕便成全你们,把你赐给广平王可好?”刘舒曳甩了甩手,直起身望着脚边的人儿,“不过可惜,朕马上就会给他赐婚,就算进了广平王府,你也只能是个妾!”
“陛下为何不信我?”白为霜慢慢站起来,泪划过脸颊,摇摇晃晃地朝刘舒曳走了两步,看着面前那张自己念了七年的脸,时清时浊,不尽真切,“倘若真如陛下所言,七年前我那一顶花轿进的为何是靖王府?”
刘舒曳望着白为霜,良久,甩袖离去,“霜嫔不知礼节,顶撞天子,即日起禁足于寝殿,没有朕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探望。”
罢了罢了,倘若他们情真意切,成全了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