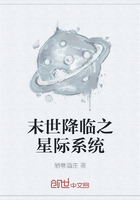小的时候,把能看的都看在眼里,但没有说。我把那些话养在肚子里,等时间一长它们长出细密的牙齿,放出来只怕咬人更狠——不可说。
看着水泥、油漆、涂料,墙纸、墙布,思维一转身就到了蛎灰。
母亲去烧蛎灰时,要穿上尽可能包得住的衣服,再戴上一顶帽子。帽子前有鸭舌,其余三边垂下来长长的,护住脖子。蛎灰碰到汗水是要咬人的。
回来的时候,母亲的脸就云山雾罩,眉目不甚分明,有时竟皑皑起来。
小时候尽量避开烧过蛎灰后的母亲,脸若罩了一层严霜还在其次,主要是她所戴的帽子,下面披下来的部分像极了电影上日本鬼子戴的。看《地道战》《地雷战》长大的孩子,对有关这一切零容忍。
当然我没有任何表示。小的时候,把能看的都看在眼里,但没有说。我把那些话养在肚子里,等时间一长它们长出细密的牙齿,放出来只怕咬人更狠——不可说。
没有几个大人会喜欢这样的孩子,作为孩子他们好像预先老掉,存心让大人们失去做长辈的乐趣。
蛎灰场少儿不宜,我极偶然地去。灰窑建在地上,以前是挖成深的圆桶状,后来改成浅浅的盆状,简直就是地窑。蛎壳下放着一层发火的燃料,一开始是木柴,燃着后往上面一层一层地加蛎壳,蛎壳里混进了窑灰,以后才改成煤。母亲他们推着土制的大风扇往窑里鼓风,一开一合,前进倒退,发出扑扑的声响。灰白色的烟雾,一阵阵冒出来,气味呛人,伴随着嶙峋贝壳被火逼出的密集裂响,场面惨烈。
这些都是贝壳类的外骨骼,种类繁多。这些壳当然不是当时的人吃出来的,那是从海底捞上来的。
海边的岩石上结满了贝壳,它们自生自灭。冬天的时候,一旦过于严寒,岩壁就会结冰,冰过的贝壳大片大片剥落,比铲除还要干净。但是海底的贝壳也不是上面掉下去能堆得起来的,那是潮流带来堆在一起的。潮流是很奇怪的东西,会选一个地方堆石子儿,一个地方堆沙子,剩下的地方堆成泥涂。它当然也会选一个地方堆起贝壳,主要是有洄水的地方,海流从各处捎带来的贝壳都在此沉积,附近的铜瓦门就有个大壳场。
采壳船停在预先相准的地方,成堆往上捞。什么货色都会有,能认得出的有藤壶、蚶子、牡蛎、蛤蜊、长尾螺、珠贝、海瓜子。碎成残片的已被水流磨得圆光润泽,像古代瓷片。很多模样大体还在,只是缺尾、缺嘴或者腹部洞然,废墟感同样很强。看着这许多空空如也,人以为海底往来许多的年轻海妖,像人间的小女子一样喜爱吃零食,尤其长于嗑瓜子,嗑出一堆一堆的壳儿。人类像清道夫一样来收集它们的盛宴余物,用铁制的抓斗,绑上加长的竹竿,至少有十余米,即使用上绞索滑轮,还是十分费力,控制抓斗的人有时不得不将竹竿往上提提,免得贪心过深,难以扯动。采壳人很苦。
洗壳同样苦,采壳船撑到海岸边,洗壳人立在海水中用大筛子将壳在海水中淘洗,去除海底污泥,所以我们看到的壳总是干干净净。洗过的壳堆在海岸边,像连绵的小山,等待运到窑场,有时来不及,大水潮或者台风雨一来,壳山颓然,各色壳等重回大海,采壳人一场空。
其实面临一场空危险的更有烧蛎灰者。蛎灰红到顶层烧透后,恰到好处的特征是结成了小块,如果没有结块,那是还未透,结成大块那是烧僵了,都得废掉。烧好的灰窑打上一阵冷气,经过一夜的自然冷却,就可以将它扒出来由生化成熟了。这个过程的唯一媒介是水,只要有一滴水滴入生灰,都会冒出一蓬烟,因此除非迫不得已,船一般不会用来载生蛎灰,也有胆大妄为者,遇上雨哪怕不幸船有点漏水,满船沸腾,竟连船也一起化了。可以想见,灰场不可避免地会遇上雨,那将是何等情景,大概像炼狱。
我家当年造房子是在自家前院现挖个窑现烧,天公作美,几日未雨,因此炮制与熟化的过程都很顺利,虽然同样惨烈。我看着冷水浇在蛎灰中间的窝里,温度急剧升高,将水煮得直冒泡,放鸡蛋下去,立刻就熟了。这叫灰蛋。
然而熟化后的蛎灰还得过筛。就算前面加了不少的水,蛎灰还是粉状的,证明水在当时就被烧干了。筛灰的地方粉尘蓬勃,那里走动的人全身一片灰白。筛去杂质后的熟灰开始被人用手臂粗的长木杵使劲地敲打,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啪啪响,粉尘继续四处升腾,混迹其中的人,他们的呼吸都是灰白的,被蛎灰从里到外粉刷了一遍又一遍的同时,也啃蚀了一层又一层。
洒上一点点水,粉状的蛎灰硬是被捶打成了柔韧的一团,黏性很强,完全能将砌墙用的石头或砖块粘合起来,还可以涂布在墙壁上,颜色白得寡淡,又带点灰心。
归类一下,它就是现在所说的装潢材料,用来装饰我们的日子。但看着这种材料长大,看它们长出来,同样活生生的,区别最大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用柔软的血肉将骨头精心包住,一旦意外露出来就要呼天抢地,它们却是用骨头将肉小心包裹起来,它们的骨头才是真正坚硬。
后来掉下水去,又被捞起,洗净,先在火里煅烧,又在水里释放出火热,然后百般捶击,从粉身碎骨再到不分彼此,最后上墙。
那时无甚讲究,因此砖缝里露出的灰浆或是直接涂布在墙面上的都显得不平滑不细致,用手摸,似乎能摸出一把把的骨感来。
坚硬与锋利,让人始终摆脱不了粗糙与黯淡,放不下过程里的焦灼、迷惘,仿佛映照着备受煎熬的人生。
我认为烧蛎灰的人没法好脾气,那是值得原谅的。
问题是,如果世界上有种很不幸的人,既然不能对困苦安之若素,往往也不能对幸福甘之如饴。
所幸蛎灰已经远去,惨烈与悲怆的场景不再重现,现代装潢材料时代,我们的生活周围充满了平滑可喜。
祝福人们从此以后心平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