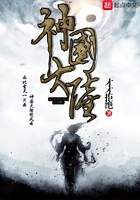“我……”猜的。
李承景话还没说完,就听见产房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刚才那位产婆跑出来报喜:“恭喜老太太,夫人生了位小姐,母女平安!”
老太君闻言神色一松,她身边的嬷嬷思松早就喜气洋洋的去安排打赏了。
气氛一直低落的将军府终于迎来了一件喜事,全府上下都满心欢喜。
更没想到的是,这时候传来了关外的捷报,李怀远和李怀明打了胜仗,此刻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赵谢双手合十,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来,她随手指了一个丫鬟,吩咐道:“你,快去和大夫人说,让她也宽宽心,便也能好好坐月子罢!”
“欸!”那丫鬟正是大夫人沈婧的陪嫁丫鬟谷芹,自小就跟着的,听了老太君的话,忙红着眼睛应了一声,向产房跑去贺喜。
安顿好儿媳,赵谢才稳了稳心神,仿佛又活过来一次。
“国师大人,大恩大德,我们李家,没齿不忘!”她声音微颤,身形却稳如山。
这半年来,她早已做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准备,次子李怀重不堪大任,她甚至都做好了亲自培养长孙成材的准备了,没想到最后竟峰回路转。
她已经年老了,在活着的时候能保住李家子孙,百年之后,也能有脸面去底下见李家祖宗了。
“老太君言重了。”国师微微点头,摸了摸花白的胡须:“李将军和李都尉得胜归来,李家又添贵女,真真是双喜临门,恭喜太君了!”
“这都多亏了国师大人,”赵谢接过重新准备好的佛珠,她虔心向佛,家里的佛珠一直都在菩萨面前供奉着。
丫鬟们早就将刚才洒落的珠子捡起送去了寒山寺重新祭拜。
“厨房已经备好宵夜,粗茶淡饭不成敬意,国师大人不嫌弃的话,就移步偏厅用些吧。”
“不了,老道还有些事要去处理,就不叨扰了。”老国师笑着摇了摇头,他今日来也不仅仅为了李家,只是此事事关重大,他不得不亲自跑一趟方能安心。
“国师留步!”沈媱抱着一名婴孩快步前来,孩子的襁褓上放着的正是玉铃,叮当作响:“姐姐产子体弱,让我前来相还玉铃,李家沈家,定不忘大人恩德。”
沈媱本就是沈婧一母同胞的姐妹,自小感情甚好,如今又一同嫁到李家,更是相互体谅,甚至沈婧生产,她都一直在一旁相陪。
国师从她怀中接过孩子,细细的看了看:“这孩子是有福之人,这也是她的福分,这玉铃,就当是我送给她的见面礼了。”
白瞿如一直安静的站在一边,听到国师的话便上前来取过玉铃,从手腕上解下一条掺着金线,编着金刚结的红绳,穿过玉铃系在她的左脚上。
“瞿如,要不要看看这孩子?”国师笑了笑,微微弯腰,刚出生的孩子皱皱的,小脸通红,似乎是感觉到有人在看她,变睁开眼睛盯了一会儿白瞿如,竟然小嘴一撇,大哭了起来。
白瞿如皱着眉头看着嗷嗷大哭的孩子,略有些嫌弃的退后一步。
身子小小的,声音倒是大。
国师哈哈一笑,将孩子还给沈媱:“她看样子是饿了,快去抱给奶娘吧,老道就先告辞了。”
赵谢知道国师向来来去无踪,不再强留,带着人送到了门口,目送马车走远才回府了。
马车上,玄丘打量着自己这个向来待人冷漠的弟子:“怎么把你的红绳给她了?”
瞿如最不喜别人动他的东西,也不喜别人接触,连他这个师傅也不例外,没想到这次竟亲自给那孩子带了玉铃。
难道他转性了?
白瞿如淡淡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师傅:“那玉铃不是凡物。”
孟槐兽最是高傲,玉铃经它的骨血浸润,便也沾着它的傲气,是以玉铃宁愿玉石俱焚,也不愿被凡间浊物束缚。
若不用这同样灵气十足的红绳,是碰不了它的。
玄丘哪里会不知道,只不过和自己徒弟开个玩笑罢了,哪知道他小小年纪,还是这样古板。
他干咳一声,收起脸上的笑意,正色道:“那孩子出世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了吗?”
“是鸾鸟。”
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
玄丘点头:“不错,是鸾鸟,十年之内,夏后国再无战事。”
他撩开帘子,外面正是十五月圆之夜,满天繁星,东方却已隐约升起红霞,黑夜马上就要过去了。
马车停在国师府前,白瞿如一跃而下,玄丘却仍留在车上。
“师傅?”他敲了敲车壁。
“瞿如,为师有事要进宫一趟,你先回府吧。”
“为了朱厌?”
“你知道?”玄丘惊讶的看着自己的弟子,头不自觉的伸出了窗外:“你如何得知?三年前,你才四岁!”
“所以我当时只看到了影子,”白瞿如踮起脚,放下帘子盖住他的脸:“今日鸾鸟一现世你就要进宫,定是为了三年前的朱厌。”
玄丘被甩了帘子也不生气,摸着胡子笑了起来:“瞿如竟如此天赋异禀,不愧是我玄丘的关门弟子。”
话音刚落,就见马儿嘶吼一声飞奔了出去,瞿如收回抽马的手,淡然然地转身进府。
夏后国历代国师都受到极大的敬重,宫门刚开,他的马车便毫无阻碍的进宫了,皇后早已梳妆整齐等着了。
“皇后娘娘近来可好?”
“托国师大人的福。”嬷嬷弓着腰,恭敬地给玄丘敬茶,他方品了一口茶,皇后便快步进来了,玄丘起身微微颔首,也不行礼。
“国师大人!”皇后丝毫不在意,甚至微微拱手表示敬重,脸上却是一片焦急之色:“国师大人,今日便是三年之期了!”
“正是,所以及今日老道连夜赶来。”玄丘坐回位子,慢条斯理的闻了闻茶香,和皇后的急切截然不同。
皇后到底也是皇后,不管内心如何着急,还是沉住了气,坐在上座:“不知国师还有何吩咐?”
谁不知玄丘脾气古怪,油盐不进,计较起来谁的面子都不给,庆幸的是他还算是个正道人士,为夏后国挡过不少邪祟,也因为这样,连皇帝都要敬他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