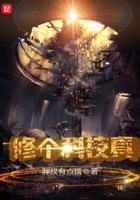天气出奇地好,白云像扯飞了的大团棉絮,天空被铺满了,只从棉絮的缝隙里露出一点点浅蓝。没有雾霾。北方有地方流行“七月八月看巧云”,在北京,却要推后到十月份。美桃见过草原上的云,单是那片一望无际、深浅不一的绿已经让人心旷神怡,阳光又从云缝里照下来,给草原洒下一片亘古不变的金,那是从盘古开天辟地时就存在的颜色,沐浴在这样的阳光下,只觉得人也浑然有了古老永恒的气息,心安、沉静。而同样的云搭配上北京的高楼和车流,又瞬间给人未来科幻世界的错觉,凡是人为的,都是变化莫测的,给不了人多少安全感。
三环上车流汹涌,堵车不分时间——早晚高峰时堵,闲时也堵。美桃在出租车上坐如针毡,想着几公里外的儿子图图正待在医院里受罪,他那么小、那么乖,像一只会说话的小泰迪,除了幼儿园,他从来没有离开美桃单独待过。可是出租车总也开不快,美桃的心在医院的儿子身上,脑海中却像过电影一样闪过无数或者庸常、或者惊心动魄、没有任何意义、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美桃情绪的画面。美桃想起怀上图图那年,常会在睡梦中因为喘不过气而惊醒,一醒来心情就无端地变好。世界太大,人们又太忙,生命的逝去和到来只对最亲爱的人才有意义。美桃开始相信有一个上帝,在平衡着世间的万事万物,他从太过得意的人身上拿走一些东西,补给失意的人。他看见美桃的孤单,于是赐给美桃一个孩子。
隔离带上开满了粉的黄的月季花,开在微凉初秋再加上吸了太多粉尘尾气,灰扑扑的没有光泽和生机。美桃看着觉得扎眼,真像自己刚做好的那件上装,那颜色忽然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回头就换个颜色拆了重做,美桃这样想着。天气好的让人想哭,花却恹恹的让人生气,此情此景像极了煽情电影的情节,主角明明哭到快要窒息,风景却一如既往地美着,美得让人不忍看。
车子终于下了辅路,来到阳光医院门口,开车看病的人很多,路又设计地非常不合理,通往车库的车把道路堵住了,美桃看着明明几千米外的医院门口,车子却开不进又倒不出,堵在那里。美桃连忙付了车费,下车朝医院跑去。
去往医院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商场,商场外面的小广场上有一个大而华丽的旋转木马,图图只在一个月前坐过一次。美桃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图图坐在那匹带了金色马鞍、五彩辔头的白马上做鬼脸的照片,苹果样的小圆脸显得有些苍白,美桃把这张照片传给自己的男闺蜜徐贵儿,“磨皮磨得太过分。”徐贵儿说。天知道,美桃根本没有修图。
“白是遗传了我的基因。”美桃回答,现在回想起来,那白应该就是生病的前兆了。美桃急匆匆地经过那匹静静的木马,她的左眼无端地狂跳起来,那么发生在图图身上的一定是好事,美桃这么安慰着自己,她的步伐却越来越快,从小跑到狂奔,有几次她的高跟鞋蹭到了裤脚,她的白裤子上会留下几条灰印子,管不了那么多了,能让美桃不管不顾地跑的,只有图图。
医院门口大堵车,天天如此。美桃拨通了王老师的电话,王老师告诉她:图图已经醒了,医生把图图安排在H住院楼,没说几句,通话就断了。图图精神状态好吗?是笑还是哭?所有的消息又都不得而知。美桃收起电话,一路狂奔。
在美桃年轻的生命中,很少有忘掉形象没命地奔跑的时候,十八岁那年夏天有过一次,与其说是奔跑倒不如说是逃避,美桃下了车狂奔向自己家,进家门口的一刹那却又猛地停下。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么他一定会给每人的一生中安排几次这样的时刻,让人忘却自己、全心全意投入到对别的人和事的关心上,经历过以后,人才更接近神,才明白尽人事、听天命的道理。
H住院楼离医院前门太远,美桃恍惚记得有个后门可以走近路,美桃从小路绕过去,阳光儿童医院后面,有一家专业肾病医院,美桃七拐八拐地走到两家医院中间的一条小街,路边开满了林林总总的小店,远看像各种民族服装,走近了才知道这分明是寿衣店和花圈店。天明明是晴朗的,可是美桃总觉得地上有水,湿湿的水先是沾到鞋底上,然后蹭到裤管上,浑身上下都变得粘腻潮湿起来。气氛无端地肃穆,像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拽着美桃的腿,被迫让她放慢脚步。像美桃一样经历过亲人离世的人,她们甚至看过死去亲人的遗容,守过灵、烧过纸钱、上过坟,面对寿衣、花圈这些丧葬的东西,美桃不会感到害怕或者难过。人死以后到底去了哪里?天堂里的亲人在给自己某些启示吗?美桃抬头看看天,絮状的白云慢慢散去,露出蔚蓝的天空,像一望无际的大海,这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给她的暗号。
拐进医院的小门,美桃跑向H病房楼。她白色的裤脚,的确有几道灰印子,但是淡紫色的丝巾一角被微风吹得飘起来,她脚步匆匆,美丽的脸上却透露出干练、镇静,让人联想起朝霞满天的清晨或者云淡风轻的午后,有阳光,有青草,野花在微风中摇曳。
美桃跑进病房楼,从容镇静地问守门的护士,她希望人们看到的是她的镇静,但她的眉头却微微地皱起来。
“请问,林源在哪个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