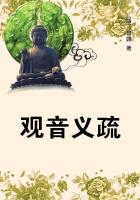JING ZHE
尘烟绮年事
“二十一日,群臣入临,见帝于东序阁,群臣拜舞称万岁,复哭尽哀,退。群臣上表请听政。”
念到这里,伯方低声叮嘱我说:“陛下要推辞两次,等到他们上了三次,然后才可以应允。”
我木然点头。
“二十三日,陈先帝服玩及珠襦、玉匣、含、襚应入梓宫之物于延庆殿,召辅臣通观。二十四日,大敛成服。二十五日,有司设御座,垂帘崇政殿之西庑,帘幕皆缟素,群臣叙班殿门外。”
我转头看窗外,杨柳刚刚发青。
大约是惊蛰天气。
春天就要来了。
与几位宗室见了面,他们的神情都没有什么异常,只是眼睛红红的,好像平白用辣椒水刺激了一样不自然。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眼泪是流出来的,不是哭出来的。
到东序阁的时候,才发现母后坐了大安辇来。
大安辇是咸平年间,父亲为万安太后所制,上设行龙六条。平时皇太后、皇后常出,一般只用副金涂银装白藤舆,覆以棕榈屋,饰以凤凰。母后在父亲刚刚龙驭的时候,就坐大安辇来,想必不是没有深意。
于是我跪下拜见,然后诏皇太后出入所乘,以后都如万安太后舆,上设六行龙,制饰率再加。
母后在辇中微微点头。
万岁万岁万万岁。
群臣呼声山响。
如果真能万岁,我还用坐在这里吗?
我父亲若真的万岁,我就可以一辈子在司天监里看着星宿,永远也不用知道人世间的事情了。
木然地听所有人按礼节哀哭,这感觉真奇怪。
父亲和我见面的时候,大多都是那几句话——
“给父皇请安。”
“起来吧。”
“谢父皇。”
低头无言。
“今天书念了吗?”
“念了。”
“好好用心。”
“是。”
“下去吧。”
“是。”
但是以后连这样的话也不会再有了。
不知不觉我也泪流满面。
回宫后母后褒奖了我:“皇上刚才的举止很合礼节。”
杨淑妃旁边的老奴说:“对啊,那些个宗室,个个哭得那么僵硬,哪有皇上哭得好。”
因为淑妃是把我从小养大的人,那老内侍在我小时候也经常给我逮蛐蛐,大概现在是老糊涂了。所以我假装没听见。
淑妃忙拉老奴跪下,怒喝他磕头。
母后也就不再说什么。她端起茶盏喝了一口,问:“有拟好谁去守陵了吗?”
“还没有。”我低头说。
“那不如封李婉仪为顺容,从守皇陵?”她缓缓地问。
李婉仪,我没有什么印象,大概也是普通的嫔妃吧。
“一切遵母后的懿旨。”
母后着意看了下我,见没有什么异样,想了一想,又说:“让刘美、张怀德访其亲属入朝吧,她是杭州人,据说在杭州还有个弟弟叫用和,不如让他补三班奉职。”
“是。一切听母后的。”
傍晚的时候,我见到了李婉仪。
我依例讲了抚慰她的话,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我,口中只是称“是”。
最后我说:“你既没有孩子,长守父皇身边也算是福分了。”
她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看见她的眼里全是泪水,却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只是泪流满面。
这个人,和我一样的哭法。
她跪下磕了头,然后回去了,头也没回。
据说她是有个女儿的,只是和我的哥哥们一样,都夭折了。
在皇家,能长大的孩子是很少的。
我心里难受,看看天色黑了,又想起昨夜那个奇怪的女子。
胡乱吃了点东西,太白已经出来了。
到司天监的路上全是竹子,夜风中斑驳瘦影在我衣袍上晃动。禁苑的灯全是白色,照在青砖上,一股阴寒从地面卷起,直扑人面。
我要去看她吗?
我一身寒意,呆了半晌,然后回身向伯方说:“回去吧。”
走了几步,回头看一看司天监。
一片寂静。
不知道她来了没有?
我感觉到右颊开始温温地热起来。她手心的温度明明还在我的肤表,那种奇异的温暖却像藤蔓一样蜿蜒地钻入我的心脏。
她身上的香味,是白兰花的味道,青涩而幽暗。
她对我说,我明天再来哦,小弟弟。
她的笑容就像被关在稀疏笼子里的蝴蝶一样,既没有些微威胁,又伸手可及。
我站在离司天监只有百尺的地方,默然地看着那个高高的步天台。
伯方在身后问:“皇上?”
“回延庆殿。”
我已经整整两夜都只是稍微合了下眼,可居然还是睡不着。
起来在殿外看天空。现在天空最亮的那颗星,就是北落师门。
长安城北门叫“北落门”,这颗星星就是以此为名。师,兵动。
北落师门,主非常以候兵。兵,即是兵灾。
太祖皇帝每灭一处割据,就将金银财货分一部分入专库,对臣子说,等库内积存到三五百万时,就可以用来向契丹赎回燕云故土。
从那时开始,对外族就是妥协,而不是用武力。
澶渊城下那一战,局势已经倒向我们这一边,但是父亲始终不相信能真的打败辽人,而且,他后来还对我们兄弟说,不要战争,万一臣子握紧了兵权,五代之祸就是前车之鉴。
他最后对我说的善待天下,何尝不就是要我安定局势,避让战争?
宁愿屈辱,也不要颠覆;宁愿苟延残喘,也不要失去权力。
这就是我们的国策。
其实这与我又有何关系?
我其实什么力量都没有。我甚至也不想当这个皇帝。
我排行第六,是父皇最小的孩子,没有贤能,加上年纪太小,也没有公开支持自己的势力,现在能做的,只有乖乖听母后的话而已。
母后现在已经在替我物色皇后,据说是应州金城人,平卢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为了防止前朝后戚干政,她也不是什么显赫出身。
心里正烦躁,伯方突然在后面问:“皇上该安歇了?”
我点头。
伯方伺候我睡下。
周围空荡荡的,仿佛连我的呼吸都隐隐有回声。
宫灯点得又这样明亮,越发映得周围冷清,清清楚楚地看到,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人躺在蒙着缟素的房间里,睁着眼,看一室的死寂。
那些宫女在外殿也睡安静了,母后挑选过的人,睡相都是极好的,没有一丝声音。
周围空气也一片凝固。
因为这安静,我害怕极了,手指不自觉就痉挛地抓着被子。那些丝绣的龙,像蛇一样缠绕在我的身上。
我喘不过气来,我看见母后大安辇上的六条龙,从外面钻进来,冷气咝咝地吐着信子。
信子血红,却像父亲的唇,在他大去的时候,异样血红的唇。
他的双唇不停颤抖,里面吐出的字却清晰无比——善待天下啊,受益。
……受益,受益。
杨淑妃在我很小的时候,跟在我身后追我,笑着叫我。
我回头看她,突然前面一空,坠入悬崖,在最高的地方一下子摔了下来。
梦魇。
我挣扎着坐起来,大口喘气良久,才爬起来走到窗口。
北落师门明亮而冷淡地挂在天边。
这宫里,还有我唯一喜欢的地方——步天台。
还有那个奇怪的女孩子,约我今天在那里见面。
那贴在我右颊的掌心,又再次温热地在我的肌肤上燃烧起来。她手心的温度,已经在我的心脏里,生根发芽。
她身上的香味,好似白兰花的气息,青涩而幽暗。
她对我说,我明天再来哦,小弟弟。
这个幽深的宫廷之中,唯有她的笑容,像被关在笼中的蝴蝶,美丽温柔,不带任何危险。
我从偏门跑了出去。狂奔过无数惨白的宫灯,奔过无数枯瘦的竹子,风像刀子一样从我身上一掠而过,二月,几乎冻到皮开肉绽。
子时还没有到。我在高台上等待她。
这样冷,我好想要一点点温暖的东西,就像她手心的那些夏天的温度。
还有,像笼子里的蝴蝶,安全,又贴近。
银汉迢迢。
在高处看,最是清楚,可也最不胜寒。
似乎全天下的风都聚在这里,我穿着薄薄的单衣,从被窝里跑出来,等待她的到来。
可也许我并不是在等待她的到来,我也许只是厌恶延庆殿太过窒闷的空气,也许只是不想看见那些龙蛇。
也许,只是想摆脱那即将从最高处坠落的恐惧感。
抱着自己的膝,我坐在步天台的乱风中。
整个天空缓慢地斗转星移,所有的星宿都冷淡地在我头顶上旋转。
冷得连发抖也停止了,只是觉得那寒意从四肢百骸钻进去,像在里面扎根一样,一层一层深到骨髓里面去。到最后那些寒冷挤满了全部的血肉,就不觉得寒冷了,只觉得融融一片。
直到子时过去,长河渐落,天边幽蓝。
她没有出现。
她明明说要来的。
原来她也在骗我。
好像她的膝盖狠狠撞到我的时候那样,疼痛至极。但这次却不是右肋,而是心脉那一块。
天色大亮。
我想要起来,手脚却僵硬了,一时跌在地上。
身后有人默默把我抱起来,给我包上锦被。
原来是伯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的。
他已经准备好热水。我僵直的手指触到温水的瞬间,血液像从凝固中融化一般,开始在我的全身流动起来。
意识清醒过来,我这才明明白白知道,那个笑得温暖的女孩子骗了我。她没有来。
听到外面的宫女在偷偷议论,太后赐了壶酒给淑妃身边的老内侍。
我甚至连眼睛都没有抬。
好像已经冻麻木了,甚至连他小时候给我掏蛐蛐时,那些粘在他下巴上的泥都已经忘记了。
那年三月庚寅,我初御崇德殿,母后设幄次于承明殿,垂帘以见辅臣。
八月乙巳,母后同御承明殿垂帘决事。
十月己酉,安葬先皇于永定陵。诏中外避皇太后父讳。
十月己未,祔父皇神主于太庙,庙号为真宗皇帝。
就是在那个月,众人口中出现已久的郭青宜正式进宫了。
她比我大四个月,即使在低着头向我走来时,也有一种抬着下巴看人的感觉。
我向她看了一眼,看到她头上冠饰为九翚、四凤,就放了心。这是妃子之制,看来母后没有现在就立她为后的打算。至于她的脸,我没有瞧清楚就把眼睛转回来了。
向太庙里的祖先行礼时,我暗暗庆幸。
我朝帝王每月在皇后宫中时间若太少,身边内侍客使就会提醒着去皇后宫中。我才不要每个月用那么多时间在这样一个陌生女人那里睡觉。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我以为再也不会看见那个奇怪的女子,我也没想再看见她。
我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习惯了任何事情都往右一看。
仿佛母后随时垂着帘幕在我的右边。
我以为自己的人生顺理成章就会延续,再没有任何突兀的事情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