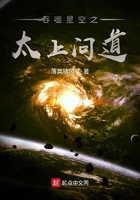宗政康在峡州并没干多久,便被李庭芝将军调入了两湖。
再之后由于宗政康出身将门,文采斐然且交游广阔,又被陈宜中调到了临安,做了他的幕僚。他亲眼目睹了家国沦丧,奸佞当道,外族入侵,哀鸿遍野。
十四岁投身军旅,十几年的四处飘零,终于在他弱冠之年心灰意冷,进了青城山,拜了青城派著名的宗师陈希泰为师,修道练剑,不问世事。
直到听说赵丹青意外被捕,淮南义军惨遭偷袭,隐居多年的他终于不能坐视不理。引剑出山,踏进了纷扰的江湖仇杀之中。
任飞云等人当天夜里便出了河间府,在一处马驿中抢了马,飞速逃入穷乡僻壤,余不问为人机警,事先还让一队人带着同等数量的马匹,往相反方向跑出脚印,生拍于括苍带着援兵前来复仇。
口衔核,蹄裹布,一行人在东阳县黑石岭弃马走路,避开官道,专挑人迹罕至的小路走。终于在一环境清幽的小山坳处寻得一处可避风雪的破庙。此地离东阳县还有半天的脚程,马氏兄弟带着几个好汉四处查验了一番,并在周围设下了可随时触发的机关。
众人累了一天,早就疲惫不堪,宗政康命几名弟子轮番守护,再用周边的枯木削尖做成厉害禁制。如此一来,整个破庙前前后后十几处独门机关,再加上暗桩暗哨,这些人的防范意识还真不弱。
快至清晨,破庙之中鼾声如雷,众人围成一个圈,中心升着一个暖烘烘的火堆,随着雪越下越大,庙内却温暖如春,说不出的舒服。
任飞云看着宝相庄严的释迦摩尼,心中升起一种平和的感觉,背后被粗布包裹的祭兵此时也不再胡闹,安安稳稳的没发出一丝响动。
他倦意全无,与马氏兄弟有一搭没一搭的喝酒聊天,他走南闯北阅历丰富,说起一些奇闻异事更是手到擒来,尤其是他当云阳管事这段期间,缠着邵良辰恶补江湖掌故,虽然曾经在下五门听人说过一些,但有必要加深了解。他骨子里对江湖套路早已摸得透彻,再加上孔秀,若浪峰,袁无义等人的介绍,阅历更是无人能比。
尤其是袁无义,他的消息可谓可是千金难买。那是中州杀手团和他手底下数十家帮会牺牲了多少人换来的一线情报,袁无义都要在每天清晨的时候草草看一遍。
有了这些情报,任飞云算得上富可敌国了。可他宁愿拿出来作为喝酒聊天的谈资。
至少他现在还活着,活着就要讲话,活着就要喝酒,没什么比说话喝酒爆粗口还要让人兴奋的事情了。
任飞云说了一些江湖隐秘,其中有肖辨机伙同金宗全力打压丐帮的内幕,也有湘北七星帮的老帮主精尽人亡的闹剧,说得马氏兄弟一惊一乍,完全难以置信。但仔细一听,任飞云说得有条有理,有证有据,你不信都不行。
“怪不得庐山派这些年的消息来源这么可靠,和金宗两家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壮大,控制了丐帮,就相当于控制了半个天下的情报来源。”马二说道。
任飞云道:“丐帮的可怕在于根深蒂固,不是想撼就能撼的动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衣衫褴褛的乞儿究竟有多么可怕的力量,这些人组织严密,行动迅捷,条理清晰,防不胜防,真正的根系藏在大地的土壤中,那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所以,任凭孙见霞与肖辨机怎样折腾,都是徒劳无功。”
马达笑道:“最可笑的还算是七星帮万老头的死,什么白莲报复说,兄弟相残说,门派倾轧说,原来根本是谣传。亏难了司徒盟主还专门到场吊唁,说那些什么报仇雪恨,天妒英才这样肉麻的悼词。原来万老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色鬼。哈哈,笑死我了。”
黑影中有人“哼”了一声,好像显得极为不满。
任飞云听出来是余不问,不理他,继续聊天。
“云兄弟,那你说于括苍此次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可能在沧州的修龙丹会上与我们为难么?”马大听了任飞云对于括苍伤势的评价,心想少了这么个厉害人物,这次捣乱元人的鸟丹会算是十拿九稳的事了。
马二做事把稳,摇了摇头,表示怀疑,“苏勒德到了战无极手里之后完全就变了样子,想当年苏勒德只是成吉思汗编制的情报斥候,专门监督各地官员的动向,是否有叛逆的行动。由成吉思汗手底下智囊者勒蔑一手负责。”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将兴安岭一地赐给了他信任的木华黎,漠北呼伦贝尔一地赐给了他弟弟哈撒尔,他的一些部将多少都分得了不小领地。领地很大,谁知道谁有异心,谁暗自集结兵力企图反叛?尤其他对自己的弟弟别里古台和哈撒尔多少有些不信任,更大程度上是对这些刚归顺自己的部族具有很深的疑心。统一初始,蒙古人中有很多都是相互敌对后被征服的,泰赤乌和乃蛮部,统一的部族很有可能再次分裂。为此,就必须有一支情报收集单位。
苏勒德就是成吉思汗号令全军的战旗,是他权利的象征。
“此后蒙古东征西讨,势力越来越大,许多奇人异士纷纷投靠,者勒蔑便将他们安排在苏勒德编制之中,直到战无极接管。他上台后大肆改革,将苏勒德彻底从军方划分开来,成为皇帝直属下的机构,不属于各部各司的独立存在。他们便是忽必烈管辖北方武林帮派的爪牙。”
宗政康不知什么时候加进来,拿起马二面前的酒,咕噜咕噜的灌了一口,笑道:“不仅如此,由于战无极和吐蕃藏密的关系,还将苏勒德设置为宣政院的一部分,有人说战无极的势力不只是九天二十八宿,没有人清楚这股力量有多么强大。”
马二道:“战无极势力这么大,岂不是连皇帝也管不着了么?”
魏惊天在旁边睡不下去,探出头来,也照例喝了一口酒,笑道:“皇帝也怕的很啊,曾经我有一位小偷的朋友进大都皇宫顺些东西出来,无意中听见忽必烈和他手下心腹,一个叫耶律希亮的小白脸讨论这件事。”
“哦?”
“忽必烈对耶律希亮说:‘国师的势力越来越大,怕底下的人会很有意见。你说这么办?’耶律希亮说:‘依臣下之见,不如准了那张弘范的请求,让拓剑门进京,授予皇家剑派的称号,培植心腹安插其中,再挑些人员加入却薛军,用以制衡国师的苏勒德。’忽必烈说:‘你说的很对,只不过若让一个汉人担任这样重要的职位,怕有人不服。’耶律希亮笑道;‘那不要紧,我听说伯颜将军有个义子,小小年纪武功了得,天资聪慧,无论什么样精深的武学,一学就会,连龟九灵,真鼎也说着孩子是旷世的练武奇才,我想不如让这孩子拜张弘范为师,学全拓剑门的武功,替陛下效力。’忽必烈一听很高兴,问起那孩子的姓名,耶律希亮道;‘此子蒙古名字叫揭必那儿兀失,蒙哥汗赐了他一个汉名,盖天蛟。’忽必烈当场赞道;‘好个盖天蛟。’”
宗政康道:“哼哼,如此这般,这名震天下,杀死我义军无数高手的‘万象神罗’算是出世了。”言语中略带讥讽,随后叹了口气,“当日在烟霞关中,这盖天蛟武艺绝伦,二个人战我们几十人,而且不落下风。当真令青城蒙羞。瞧!”
说罢卷起袖子,露出一条深可见骨的伤口,任飞云一见,惊为天人。这剑痕劈出的轨迹很怪,但说不出的流畅,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任飞云惊呆了,闭着眼睛,摸着剑痕,陷入忘我的境界,如痴如醉,好像见到了剑法中从未窥测的东西。流畅,细腻,赏心悦目,就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余不问全身颤抖,额角流出豆大的汗水,即使在阴影中,他的背还是在轻微的震动着。
这种感觉任飞云在鬼塔中似曾相识,在一副不经雕琢的水墨画上,鬼十三说这幅画是天剑门一代宗师凌怀部以剑上的墨汁滴成的,蕴含着契合天道的真理。
任飞云自从接触剑道以来,之所以进步飞快,就是对剑的领悟力超越凡人。剑在真正的使用者手中不是一件利器,而是一件创作的工具,像书生的笔,木匠手中的刻刀,石匠手中的锤子。这道剑痕,只有最敏锐的感觉和极具天才的用剑者才能劈出来,狂傲不羁,盛气凌人。
这是一个怎样的对手?真值得期待。他比我到底强多少?至少光凭这道剑痕,我与他实在差得太远。
宗政康道:“实在看不出这人还这么年轻,在我的记忆中,能在瞬间接下我,傅辨城傅少掌门,关山鹰关大侠,方姑娘四个人的杀招者,屈指可数。你们可知道这道伤口是怎么弄出来的?”
任飞云不吭不响,道:“剑气!”
宗政康惊呆了,“你,你怎么知道?”
任飞云笑道:“伤口骨肉分离,剑痕曲折不定,既然他是用剑,只有用剑气,否则我想不出其他的招式。”
“正是!云兄弟观察细致入微,实在令人钦佩。正是剑气。”
魏惊天下巴都快吓掉了,他练玄牝剑法也有一段时间,对剑理说不上精通,好坏也能看得出来,道:“这样的剑痕用剑气打出,这完全不是人能做出来的。”
“这是什么剑法?”任飞云问道。
余不问发言了,惊了马氏兄弟一跳,他的声音很颓废,很失落,但语气中又有说不出的敬畏:“能剑术!”
当君王最怕的是什么?忽必烈能告诉你,这个身形魁梧,近来食欲不振的帝王现如今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他用深邃的口吻对身旁站立的侍从说:“将他们带进来见我。”
成为了这个浩大疆土的帝王,数不清的当世名儒要他效仿前朝的君主制度,沿用“朕”“钦此”之类的朝堂礼仪性称谓,以显得“君臣有别”,但忽必烈却深深厌恶这种浮夸无用的东西,相比之下,他更喜欢与有知识的人交谈,谈论古往今来的圣贤明君,名相名将,而不是拘束在一些礼仪之类形式的称谓。
西北的战报连日来是他食不知味的来由之一,对海都频繁的军事调动,他那敏锐的军事嗅觉感到了现下时局的紧迫。海都他自小认识,同穿一条开裆裤,在一个火堆边喝酒吃肉。他有着孛儿只斤黄金家族优秀的血统,一个天生的军事天才,这与他的爷爷窝阔台,忽必烈的亲叔叔很像,但独独没有太宗皇帝的亲和与仁慈,多了一些暴戾与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