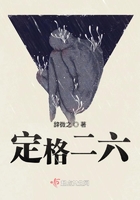王宇轩迷迷糊糊间听到有人在叫自己,他揉了揉眼睛不太利索的撑起身子,瞅向那声音所在的位置。
直到看清来人是谁后,王宇轩脸上方有了点喜色,”玉儿?是你来了?可是王爷他查明了真相,洗脱了我身上的冤屈,让你来带我出去的?”
白柔玉都觉得王宇轩这话问的可笑,人家一个堂堂在上的王爷,就算图谋着王家的东西,但也三番两次的帮衬搭救过王宇轩,你王宇轩不感恩戴德,尽心尽力的报答恩情,反还为了一己私利串通自己的妹妹,企图混杂铭王府的血脉纯正。
这样以怨报德,狼心狗肺的人,岂能再有活命的机会?
白柔玉敛淡了眸中的轻蔑,换上了一副平常对待王宇轩时的贤惠模样,“都怪玉儿来晚了,让轩哥受苦了。”
王宇轩激动的忙站起身,疾步奔至白柔玉身边,“一定是王爷下达了要无罪释放我的命令,对不对?不然这地牢重地怎能让你说来就来。”
白柔玉真不知道该说这王宇轩是真傻还是假傻,这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一心幻想着能活着从地牢走出去。
“轩哥,王爷他...并未下令要放你出去,是我苦苦哀求他,才有机会来看你一眼。”白柔玉抬头对上王宇轩的双眼,果不其然看到了他眼神里的满满失望。
王宇轩颓败的吹丧着头,沉默不语,但白柔玉可不会任由他这么耗费时间,耽误她的大事。
“公道自在人心,轩哥莫要难过丧气,只要你是清白的,我相信王爷他也必然不会让你蒙冤,就算眼下皆是对你不利的证据,那玉儿大不了就豁出去性命去告御状。”
这一席话多少都触动了王宇轩几分,在他意气风发时,因为娶了白柔玉而跌入人生的谷底,可如今他锒铛入狱了,肯同他患难与共的却是让他痛恨到牙痒痒的女子。
王宇轩心情复杂的长叹了口气,紧接着伸手拉起了白柔玉的手,“这些日子苦了你了,如果我这次能逃过一劫,等出去了咱们就好好过日子。”
白柔玉点头一笑,不着痕迹的推开了王宇轩,揭开胳膊上挎着的食盒盖子,“玉儿听身边的婆子说,轩哥走时匆忙,冬儿那丫头又是个粗心大意的,都没能你披件像样的衣服,我担心你身体会受不住牢房的寒凉,便带了几件过来给你换上。”
“还是玉儿周到细心,冬儿的出身太低,欠缺正经的规矩调教,以后还需你多担待些,省的她不懂礼数让人笑话。”王宇轩态度客气道。
自己都是一个活不过明天的人了,居然还有心思护着冬儿那贱丫头,白柔玉方才故意提及王宇轩人押走时的窘态,更祸水东引把原因全都推到了冬儿身上。
虽然白柔玉还没本事处置了冬儿,至少此刻能在嘴上多抹黑她几句,心里也算痛快不少,但王宇轩对冬儿的新鲜劲还没过去,自然会偏心多维护一番。
白柔玉使劲攥着手中的衣物,不停暗示着自己要忍下心里的怒火,“轩哥说的是哪的话,不管冬儿出身如何,她能让轩哥看中还收进房里做了通房,那就是个有福气的。我身为正妻教导自己夫君的妾室,实属应该,什么担待不担待这样的话,轩哥万不可再说了,否则真是太见外了。”
服侍完王宇轩更衣后,白柔玉用食盒内的隔层为垫,将两盘家常的下酒小菜摆到地上,“牢房里的牢饭大都是酸馊的剩饭,我思量着轩哥大概还没用过晚膳,便自己下厨炒了两道小炒,轩哥快来吃吧。”
一闻到饭菜的香味,王宇轩的肚子立马咕噜噜的叫了起来,他俯下身子盘膝而坐,执起一旁的筷子便大口大口的送入嘴中。
白柔玉见王宇轩动了筷,就势又自食盒里拿出那壶毒酒,不慌不忙的斟满了一杯,轻轻放到王宇轩的眼前。
“光有吃食没有好酒可是不行的,玉儿想着陈年老酒最是暖人身子,便花了点银钱让人帮着从外面的酒肆里买了一壶,轩哥不妨饮上一杯暖身驱寒。”
王宇轩感念白柔玉的越发贤惠,正准备端起那杯酒水一饮而尽之时,无意瞥到白柔又放回食盒内的酒壶,仅是以一瞬的功夫,王宇轩便对白柔玉又起了疑心。
“那酒壶看着好生金贵,貌似是西南瓷镇进贡的彩釉瓷,只有皇亲贵胄才有享用的资格,过去我以商贾之子的身份,都不得触及此物。现在我沦为低贱籍人,更加不可能使用这彩釉瓷制品。嫡庶尊卑,制度有别,所以王爷每每下发恩赏与我,管家都不会逾越过这个规矩,你手中又为何会有这把酒壶?”
白柔玉突如其来的探视,加之手边又出现了非她阶级所有的名贵器皿,王宇轩不得不怀疑她是否早已背着他投靠了黎南瑾,兴许他和王瑞仪筹谋的计划,也是她传出去的风声。
“轩哥此言差矣,难道你忘了瑞仪妹妹嫁的是谁了?虽说她在铭王府里的位份是个妾室,但若以民间的称呼来算,王爷还是你的妹夫呢,他看中你的才识,偶尔破格赏下个稀罕的物件,哪会至于遭人深究啊?何况早前瑞仪妹妹有孕,她院中成箱成箱的赏赐,没少往咱们这送,即便这把酒壶不是王爷赐给你的,也八成是瑞仪妹妹送来的,不然想寻个盛酒的东西时,怎么会在房中的宝箱里找到它?”
亏的白柔玉够机灵,及时想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她同王宇轩相处的时日不断,当然晓得王宇轩最在意,最引以为傲的是何物。
王宇轩此人一向自视甚高,总爱觊觎与他而言遥不可及的一切,白柔玉以一句他王爷妹夫,被王爷看中才识的吹捧说辞,成功的打消了王宇轩对她的猜忌。
王宇轩觉得白柔玉此言相当顺耳,他自以为是的拂了下袖口,“那是自然,王爷对我的器重,乃是人尽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