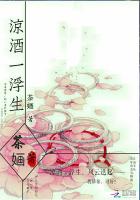北狄的马场乃王室挑选战骥的重要屯马之地,位于北狄王庭之南,近千亩的草场沃土肥美,骏马奔腾,而如今阿执跟着宁宣的近卫来到这里只觉得一片死寂,遍地都是口吐白沫死不瞑目的血骢尸体,半空里还有漫天的绿头苍蝇没有方向的乱窜着,空气中的尸体腐臭味夹杂着粪便浓郁的恶臭熏得人睁不开眼睛。
阿执一边扯着袖口紧紧捂着口鼻生怕被臭晕过去,一边步伐紧跟着侍卫来到一个营帐内。宁宣坐在营帐中央的金座上,浓黑的眉头扭曲在一起,紧闭着双眼,向下撇着的嘴角像是随时都会大放怒言。金座周围还跪着几个粗衣奴才,应该是马场的领头,各个将头埋在地上,战战兢兢地等候着宁宣发话,可越是这样默默的等待越是会等来血腥的结局。
“大王子,人带来了。”
带阿执进来的侍卫上前禀告。
宁宣抬了抬眼,那侍卫转身便朝着营帐外走去了,留下阿执独自面对这一屋子的诡异氛围。
“把你刚才跟我说的,在说一遍。”
宁宣指着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老奴才冷声道。
那老奴才抬头看了眼宁宣,顿时整个眼神都溃散开来,对于王权的恐惧在这个普通人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嗯......是大约两三天前的夜里,轮到我值夜,于是我便按照每日血骢固定的粮草份量放进马厩中,可不知怎的,到了第二日晌午,其中就有几个血骢浑然倒地,口中还流着白沫子,四条腿不停的抽搐,我吓坏了.......我......我......”
那老奴才吱吱呜呜大概说了这些血骢是怎么发病的,正想为自己开脱,却被宁宣厉声打住。
“够了,你可听清楚了?”
宁宣回眸瞥向阿执。
阿执换手抱胸摆着思考的姿态正等着宁宣开口,可是做戏总是要演的逼真些,阿执摸了摸下巴,思衬了片刻,从容道。
“大王子,我即便懂些医术,你怎能就知晓我会医治马匹?更何况,就算我能医治,你就这么放心将你们北狄的宝贝交到我的手上?你也太相信我了吧!”
“若不是那些庸医治了两日都没有成效,反而死的血骢更多,你以为本王会去请你?”
宁宣不改往日口气,对着阿执像是解释,又像是训话的说道。
阿执心下嘲讽,看来北狄的庸医还真不少,治不了宁璃也就算了,连个毒都不会解。
“既然大王子都说是请我了,总要有些求人的姿态啊!”
阿执手中拿捏着宁宣乃至整个北狄最硬的把柄,别说语气,就连表情都是一副‘你能耐我何’的模样。
四下跪着的几个奴才骤然冷汗,只觉得这个小丫头怕是个“憨的”,也不瞧瞧这上面坐着的是谁!
宁宣更是冷脸,目中布满了血丝,这几日因为马场的事情他夜不能寐,如今还要被一个丫头片子教唆,思及到这些,他真恨不得现在就要了她的命。
“......说,这次你又想要做什么?”
轻轻的一句话,宁宣心里不知忍耐着多少怒火,短短几个字近乎是咬着舌头说出来的。
“非也,我一介布衣,能要何物啊。”
阿执抬眉朝宁宣细细打量了一番,这一看其实也没有什么,但在宁宣眼中这就是蔑视。宁宣挥了挥手,那几个奴才陡然意会,争先恐后往营帐外跑去。
“说!”
宁宣背过身忍着最后的耐心,沉声吼道。
“冯落扬!我!要!冯!落!扬!”
一边不够清楚,阿执又一字一顿的重复了一边。
可想而知宁宣此时的表情,惊讶,震怒,不可置信......
“你......到底是何人?”
宁宣近乎颤抖的问道,他不是没有想过阿执的意图,可还是太小瞧这年纪小小的丫头了。
“大王子,孰轻孰重,还望细细斟酌,毕竟这极品血骢是北狄独有......”
此刻的阿执依旧环手抱胸,可是与先前相比总是哪里不大一样,每一句话都像是告诉宁宣,你已经拿我没法子了,乖乖给我放了冯落扬。
“你到底是谁!你来到北狄,来到王庭,来到朝云殿,就是为了冯落扬?哈哈哈哈,我早该想到,斗兽场里我原以为你是南国派来的戏作,没成想啊,你竟是冯易玄派来的!”
宁宣的这些猜忌倒是让阿执更加明确了一点,大齐皇帝果然薄情寡义,就连北狄人都知晓冯落扬被俘大齐是根本不会派人来救的。
“那岂不是更划算。我帮你留住你的血骢,你放了冯落扬,我保证宁璃不会再有任何闪失。”
“璃儿?你又对她做了什么?”
从阿执口中不过听到了宁璃这两个字,宁宣便愤然抓住阿执肩膀追问道。
“成与不成,全凭大王子一句话。”
阿执的两个肩膀被宁宣掐的生疼,可依然淡定道。
“哦对了,与先前一样,冯落扬一日不出王庭,你就一日也别想让我救你的血骢。”
宁宣面色铁青,曾经的高高在上,傲然凌霜,在这女子面前皆视若无睹。
当日雪山下冯落扬率领的那支队伍已经大难当头,再继续下去也不过苟延残喘,宁宣只好下令捉拿冯落扬,以此为之后收复北疆而留下一手。可这冯落扬被俘虏了这么些年,别说大齐皇帝派特使来谈判,就连寄信询问都未曾有过,俘虏冯落扬这一步棋也就这样摆在了这里。
宁宣思虑了很久,血骢必然要救,可这冯落扬是否该放他却不敢轻易下定论,就在这时,翎奇冒然闯进营帐。
“殿下,君上已经在来马场的路上了,这可如何是好?”
翎奇语气慌乱,神色却甚是凝肃。
“慌什么,恭候。”
宁宣沉声道。
宁圳身材魁梧,走起路来左右摇晃却不失王者雄威,此时他进到营帐面露苦涩,想来他听闻自己的极品血骢突然暴毙心中定是万般愤懑,但身为北狄的王,要止于颜色。宁宣和阿执一前一后立在营帐内俯身行礼,宁圳挥手让太监宫女都出去候着,这才开口道。
“可知是和缘由?”
宁圳此时神情与方才宁宣如出一辙,轻声问道。
“回父王,是粮草出了岔子,儿臣已经找人来给剩下的血骢医治了......”
“可是她?”
宁圳抬眼朝阿执看去,目中怒色不觉而起。
“......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