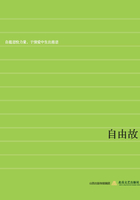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颠簸,老朱来到了学校。辅导员没有直接带他去见既成,反而找了个便利贴写了个地址给他,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老朱笑了笑谢过老师,便出了办公室的门。低头仔细一瞅,好熟悉的医院。这不,这不是阿芬……老朱,不想再继续往下想了,希望这都是假的。“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嘛,怎么可能?”老朱在心里努力的自我安慰。刚出校门,天空霎时乌云密布,才一会的工夫雨点就积极的飘了下来。老朱耸起衣领子上了一辆出租车,向医院驶去。
老朱像刚刚一样,只是有了心理准备,动作温柔了许多。是继成,面色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像极了阿芬走时的模样。谁会真正惋惜眼前躺着的这个花季少年呢。老朱颤巍巍的把手指放到既成的鼻子前,没有呼吸,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老朱无法接受这么戏剧又悲惨的现实,只感觉像是一场梦,一瞬间身体像是被人拿走了骨头,失去了支撑,所有的能量在某一刻消耗殆尽,以另一种方式去参加能量循环。老朱一屁股拍在了地上,眼泪和清水鼻涕仿佛在赛跑谁会先落下,天花板是冰冷的白色,地板的凉渐渐刺穿骨头,整个人像是坐在冰面上似的,这种感觉正慢慢向腰部蔓延。老朱这次彻彻底底对生活失去信心了,彻底的对现实绝望了,他什么也没有,赚钱了路子被堵上了,至亲也撒手人寰,心底的那朵希望的火苗渐渐熄灭。谁也没有预想到会发生这样事,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天竟是如此的突然毫无征兆。老朱站了起来肩膀发麻,心里一紧一紧的,他只想在看既成一眼,死亡证明就是一张纸,它凭什么判定一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人死亡。出于人道主义,医生早已知道这一切,并隐瞒了一些事实,是一个善意的举动。老朱缓了一会,扶着床站了起来,只感觉整个人被从侧面劈成了两半,另一半把热量毫不吝啬的传递给了冰冷的地板,老朱埋头沉思了一会,心里依然是阵阵绞痛。老朱觉得这就是一场梦,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老朱将手伸进被单里。一下就触摸到继成冰冷的躯体,那种冰凉的感觉通过指尖传到大脑,老朱可算有点清醒了;他只想拉住继成的手,哪怕是最后一次。摸到了,是那么的稚嫩细腻,自己粗糙的双手对这种感觉有点模糊,可能是因为温度。老朱感觉到了异样,这又让老朱清醒了些,医生本想上前制止,还是忍住了;老朱轻轻的将继成的手抽出来,呆滞的目光落在了继承手心,明显的勒痕,是浮肿,又消了下去,被水浸泡后,勒痕连成一道血印,老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恐的擦干自己的泪水,迫不及待掀开被单,艰难的给继承翻了个身,背上了伤痕映入眼帘,该怎么描述烙在视网膜上的血痕呢?这是四五道人为虐待的铁证,不是血痕,在老朱眼里就是血沟,为什么要对孩子下那么狠的毒手呢,接着视线自然的移到上面,既成脖子上的一道血痕格外扎眼。
这个时候的老朱已经说不出话,只是两片嘴唇在无力的颤抖着,医生目睹了这一切,也只是在在心里独自惋惜着,同情这个家庭,更多的是对这个青年的遭遇感到痛心。医生在自己的脑海里惋惜,想着这一切,忽然被一双冰冷的手拉回了现实,在这种环境下的确被吓了一跳;映入眼帘的是老朱,和他满脸的凌乱,医生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当下医患关系那么紧张,他不会找我麻烦把?“医生,大哥,求你了,这是怎么回事能给我一个说法吗?我就这一个儿子,我就这一个儿子啊!你肯定知道的,对不对?”医生被剧烈的摇晃着,思绪一片混乱,“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先冷静下,对,先冷静下。”老朱仍没有放松的意思。“患者刚被送来时,我们也很惊讶,但我们只负责抢救治疗,他身上的伤痕是警察的事。”“真的,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去挽回去救治了,可是,内脏大规模受损,伤势太严重了,加上溺水,我们也很绝望,痛心。”老朱听到这番话后算是冷静清醒了些,眼前的恍惚如一场梦。“你先缓一下,这个案子警察已经在处理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的那伙人迟早被绳之以法。”老朱听不进去了,眼前床上躺着的既成才是真真切切的。老朱恍惚着,缓慢地走出了房间,点了一支烟在走廊里的长椅上坐着。